野馬倏忽掃塵埃(代序)
柴劍虹
承蒙馮玉雷先生眷顧,得以先睹他的百萬字長篇新作《野馬,塵埃》。因種種原因,多年來我極少閱讀現(xiàn)當(dāng)代的長篇小說;但是這部長篇主要取材于敦煌藏經(jīng)洞、吐魯番等地出土的文獻(xiàn)資料與相關(guān)歷史典籍,作為一部歷時七年創(chuàng)作的以絲綢之路文化為題材的重要文學(xué)作品,當(dāng)然會引起我的興趣。然而,作者精心設(shè)計的獨具匠心的篇章結(jié)構(gòu),時空交織的敘事方式,歷史大背景下真實人物與與虛擬場景、奇幻心理的描述,乃至紛繁交錯的矛盾糾葛,廣闊而豐富的社會生活畫面,還有當(dāng)代網(wǎng)絡(luò)語言的穿插使用,使閱讀習(xí)慣單一、對現(xiàn)當(dāng)代小說創(chuàng)作所知甚少,又脫離“時尚”的我讀得相當(dāng)艱巨。因此,當(dāng)作者囑我為之撰寫書序之時,竟不知該如何下筆。好在我對敦煌的歷史文化尚略有所知,對作者多年來從事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意圖也比較清楚,欽羨、惶惑之余,談些心得,聊充“代序”,請玉雷及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我國的敦煌與西域地區(qū),是世界上幾大古老文明集中(或曰唯一)的交匯之地。而文明的交融,往往伴隨著人口遷徙、經(jīng)貿(mào)往來、政治爭斗、宗教傳播、戰(zhàn)爭較量而進(jìn)行,成為人類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文明的交流與互鑒也成為推動歷史進(jìn)步的強大動力。可以說,自古以來,我國敦煌與西域地區(qū)的文明交匯,無論對中國各民族文化的發(fā)展、變革、繁榮,還是對域外各國各民族文化的發(fā)展、變革、繁榮,都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文明交匯,正是小說《野馬,塵埃》的主題。
“野馬,塵埃”之說,當(dāng)源自我國先秦名著《莊子》中的“逍遙游”篇:“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后世注釋家對此有種種解讀,其中最能給我們以啟發(fā)的是“四生雜沓,萬物參差”“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這十六個字,因為道出了人類的社會生活與自然環(huán)境之間的本質(zhì)聯(lián)系。當(dāng)然,小說作者應(yīng)該還有更深層的用意。據(jù)史籍記載,敦煌的渥洼池是出天馬之地。盡管這里帶有濃烈的民間傳說色彩,卻印證了西漢王朝西求天馬這一個追求文明交流的歷史事實。我以為這部小說里的“野馬”是帶有明顯的象征意義和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的(請注意其“青木部·金牛座卷”中對“野馬”一詞的多種注釋)。小說從頭至尾散發(fā)出“野性”和“神秘色彩”——如果我們能細(xì)細(xì)品味兩千多年前孔子所言“禮失而求諸野”,那么對“野”的內(nèi)涵,當(dāng)有一番新的感受。主人公尚修羅出生之時,便能用西域地區(qū)流行的多種民族語言,滔滔不絕地講述如夢如幻的神秘故事(統(tǒng)名《寧布桑瓦》,亦稱“野馬”),使人們感覺到如同降生了一匹不同尋常的充滿了野性的天馬。誠如小說中言:“《寧布桑瓦》多處文字如野馬狂奔,塵埃飛揚,荒誕不經(jīng),類于《山海經(jīng)》《占夢書》,時見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當(dāng)然,其中也不乏崢嶸高論,浩蕩奇言,且最大程度體現(xiàn)客觀真實。”看似天馬行空,光怪陸離,卻在紛繁的故事情節(jié)中開啟了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文明交匯的大幕。
文明交匯的主體是“人”,是在大的歷史人文背景下社會生活中的各色人等。請注意作者自撰的小說“引言”里的一段話:
小說以安史之亂前后的中國唐朝為歷史大背景,以青藏高原、西域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區(qū)為人物活動大舞臺,以人文關(guān)懷視角審視在社會動蕩時期人們心理受到重創(chuàng)后痛苦的生活狀態(tài),以多種藝術(shù)手法表現(xiàn)社會各階層、各民族人們在動蕩歲月中的尷尬歷程,及追求真善美的執(zhí)著決心。
小說描述的盛中唐之際正是中國歷史上最敞開胸懷進(jìn)行經(jīng)濟貿(mào)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時代,也是因安史之亂造成戰(zhàn)亂頻仍、社會動蕩、經(jīng)濟衰落的時期。但是,這個時期的文化卻得益于碰撞、交流、融合而持續(xù)了大發(fā)展的態(tài)勢,呈現(xiàn)出空前的豐富多彩。一方面是“動蕩歲月中的尷尬歷程”,同時另一方面則是“追求真善美的執(zhí)著決心”,兩者看似矛盾沖突,實則相輔相成。這部小說涉筆的人物數(shù)以百計,上至帝王將相、部族首領(lǐng)、高僧大德,下到叛臣逆子、巫婆駝夫、歌妓舞女,都成為承載文化的鮮明符號;涉及的歷史事件錯綜復(fù)雜,無論是遣使通好、設(shè)防羈縻,還是攻城略地、招降納叛,抑或僧諍辯理、修文經(jīng)商,其間充滿了真善美與假惡丑的搏擊。小說結(jié)尾前,“前河西觀察判官、散朝大夫、殿中侍御史、舍人王錫奏表”頗值得細(xì)讀,其中說道:“我風(fēng)燭殘年,唯有一念,使吐蕃與唐朝永遠(yuǎn)交好。”又說:“不管梵語還是吐火羅語,不管突厥語還是粟特語,都是承載教義的工具,如同虛幻的野馬,飄揚的塵埃。其實,您所謂的‘野馬’應(yīng)該準(zhǔn)確地描述為‘像野馬一樣升騰的云氣’,與我所說的野馬迥然不同。云氣在太陽照射下很快就會消失,而野馬不管在沼澤、冰面、雪山還是草灘、戈壁、沙漠,都能夠像唐語那樣穩(wěn)定地保持和諧緊湊的形態(tài)和秀麗多姿的時態(tài)。”全書一直以多種民族語言來象征不同文化,而這里的“野馬”“塵埃”并非虛幻的云氣,而是穩(wěn)定、和諧的實際存在。不管是吐蕃貴族之子尚修羅“倏”、后突厥小王子磨延泣“忽”,還是那個安祿山的同母兄弟、侏儒阿嗜尼,他們在書中的所作所為,他們的“命運”或者說是“使命”,就是在紛繁復(fù)雜的政治、軍事斗爭與經(jīng)濟、宗教活動中承擔(dān)文明沖突與交融的任務(wù)。
小說最后,吐蕃贊普命頓悟派高僧摩訶衍與漸悟派高僧蓮花戒展開辯論,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僧諍大會”(其具體內(nèi)容也有幸保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所出的寫卷中)。論辯的結(jié)果是漸悟派占了上風(fēng),頓悟派須退出藏區(qū)。但實際上,這場論辯的結(jié)果并無輸家,兩派之間取長補短,不僅對佛教的進(jìn)一步中國化起了推動作用,也為包括佛教文化在內(nèi)的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形成、發(fā)展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小說結(jié)尾,摩訶衍將傳承文化的文字全部鐫刻到十二只‘羲和’與十只‘混沌’之上,又將“羲和”安裝到月角位置,將“混沌”安裝到日角位置,日月交輝,光耀世間,正喻示著文明的進(jìn)步。野馬倏忽掃塵埃,天翻地覆慷而慨。我以為,這就是玉雷這部長篇所要宣示的主旨。
至于小說在結(jié)構(gòu)、章法、情節(jié)展示等方面的特色,在語言風(fēng)格、人物塑造等方面的藝術(shù)手法,則要請廣大讀者去自行鑒賞和品味了。我的粗淺感受似可擬為一聯(lián):運斤有方,一顆匠心獨具;變幻莫測,萬變不離其宗。不知馮君以為如何?
2014年7月初稿于北京
2020年定稿
柴劍虹 原中華書局編審、中國敦煌吐魯番學(xué)會顧問,主要研究敦煌學(xué)。
本文轉(zhuǎn)自《大西北文學(xué)與文化》集刊(2020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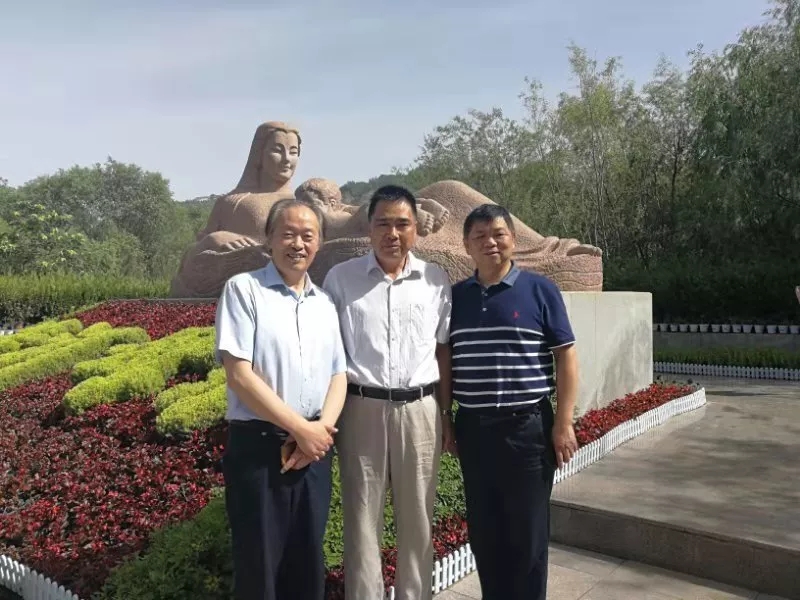
相關(guān)新聞
- 2020-12-29《野馬,塵埃》:讓敦煌文化馳騁、飛翔
- 2020-01-17甘肅省作家馮玉雷榮登《大家》封面人物
- 2019-04-16第15次玉帛之路考察活動|馮玉雷:君子比德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