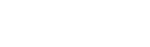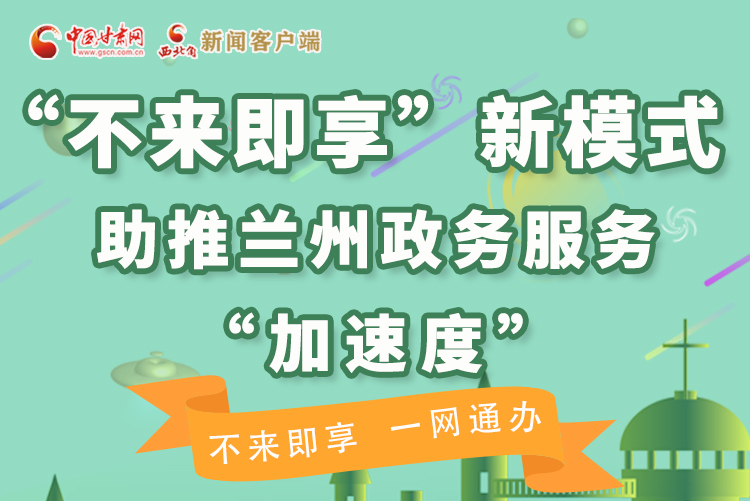原標題:胡楊地帶
瓜州人有時也把胡楊叫“梧桐樹”,我想大概有兩個原因:其一,胡楊又名“胡桐”,也許是梧桐樹的一個變種;其二,稱呼其為“梧桐樹”是追求美好事物的一種情感寄托,畢竟,“栽下梧桐樹,引來金鳳凰”,金鳳凰可是神奇的吉祥之物。
二十年前的我,身背簡單的行李,帶著年輕人的血氣方剛和夢想,一頭扎進了西部這片荒涼而神秘的高原,做了一名“傳道、授業、解惑”的人民教師。
學校在鄉下。閑暇之余,單位總會組織一些活動。有一次野炊的目的地,就是吳家沙窩的梧桐林子。
兩輪摩托車組成的車隊,大約經過二十分鐘的車程,便齊聚于一座巨大而連綿的沙丘下面。土黃色的沙粒,粒粒可數,極其干凈,雙手捧起來,緩緩地,就在指縫間全部漏光了,不留一絲灰塵。在沙丘的外圍,生長著零星的綠色——駱駝刺、紅柳、野麻。不遠處,安靜流淌的疏勒河在閃光。
沙丘上有漠風走過的紋路。沿這些紋路,目光抬升,可見沙丘高處離地面竟有二三十米。胡楊,老鄉口中的梧桐樹,便散布在金黃色的沙丘上,高低錯落,自然而然,形成一種別樣的景致。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胡楊,驚奇于它們竟能在干燥的沙丘上悠閑生長。胡楊樹的軀干幾乎都不是豎直的,為了汲取到沙粒深處的水分,它們扭曲著身子,仿佛要攢足全身的氣力。樹冠有的像一把傘,有的卻像一個老嫗頂著一頭亂發。所有的枝丫上都有銅錢大小的葉片,葉皮肥厚,綠中帶黃。
在戈壁生存久了,對胡楊的了解也漸漸多起來。胡楊是荒漠地區特有的珍貴森林資源,它耐寒、耐旱、耐鹽堿、抗風沙,有很強的生命力,曾經廣泛分布于新疆、內蒙古、甘肅西部的流沙地帶。千百年來,不管人類歷史如何變遷,野蠻還是文明,胡楊始終以堅強的軀體,阻擋著侵襲邊關、城瞿、綠洲的風沙,并用扎在數米、數十米的地下深處的根脈,為人類提取大漠深處的綠蔭和濕潤。
《后漢書·西域傳》和《水經注》都有過關于胡楊的記載。西漢時期,神秘的樓蘭古國胡楊覆蓋率至少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人們的吃、住、行都得靠胡楊。清人宋伯魯《胡桐行》的詩歌中也有“君不見額林之北古道旁,胡桐萬樹連天長”的詩句。
可見,沒有胡楊寬闊的臂膀,幾乎就沒有曾經輝煌的西域文明。
2018年夏天,我到敦煌監考。
從敦煌中學的教學樓不經意間向南舉目張望,整個鳴沙山橫亙眼前,難以計數的沙粒安靜地攏聚在一起,閃爍著金色而柔和的光芒。近處,胡楊樹零星地分布于山腳,卻又形成一個綠色的集體,像是佛國衣袖撫動的舞蹈仙子,又像是閉目趺坐聆聽梵語的圣哲。
我曾為時間緊迫,不能親臨莫高窟和鳴沙山而懊惱;但當我站立窗前,面對如此和諧而自然景觀,又激動不已。
敦煌是佛教藝術的殿堂,佛教的目的就是挽救世間人心,給眾生提供一個心安的環境。
在這里,在此時,我感覺到了這樣的心境。
我的內心漸漸趨于平和,如一枚微風中含羞的胡楊樹葉子。
人類總是野心勃勃。
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對此保持沉默:我分不清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已不再年輕而沖動。
讀書。讀到西部詩人林染的《敦煌的變奏》。
“我的農墾團場所在的那片胡楊林是中國最完整的野生胡楊林,沿著疏勒河鋪展一百多里路。到了夏天,林中的布谷鳥叫得直想翻跟頭。”
林染曾經勞動過的農場,就在瓜州小城的附近,我為此還親自去參觀過他們居住過的房子。
房屋破敗不堪,還在。
但鋪展一百多里路的野生胡楊林,幾乎已難尋蹤跡。
□宗海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