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銜山遙對九州臺,古史今韻一脈相承
——致敬敦煌學家李正宇先生
馮玉雷
2024年4月19日,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主辦、國家社科基金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項目“敦煌多元文化交融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批準號:22VRC025)支持的“敦煌讀書班李正宇先生學術專號暨學術研討會”在敦煌研究院蘭州院部舉辦。

我與德高望重的敦煌學家李正宇先生交情深厚,在創作《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敦煌遺書》《野馬,塵埃》等敦煌題材長篇小說時,自己建立的敦煌文獻資料庫中,囊括了先生所有的研究成果,并且經常到先生在廣武門的寓所聆聽教誨,或者通過電子信箱、電話請教有關問題。敦煌學界在一些問題的研究中觀點不盡一致,如吐蕃占領敦煌城的時間,敦煌得名問題,等等,我在小說創作中建立歷史時空坐標,基本上都采用李正宇、鄭炳林等先生的觀點。

近期,由甘肅文化發展研究院、中國甘肅網、上海交通大學神話學研究院、中共臨洮縣委宣傳部聯合主辦的“巡禮馬銜山:玉文化與文學融合發展考察活動”拉開序幕,馬銜山是齊家文化重要中心之一,李正宇先生在馬銜山之北、九州臺之南、黃河之濱傳承古代圣王大禹精神,著書立說,也成就了自己的偉大品格和學術大山,應該與段文杰、史葦湘等敦煌學家一起,成為蘭州底蘊深厚的文化名片。這個活動在李先生鮐背之年舉辦,意義重大。

我在座談會發言中說,黃河從蘭州穿城而過,南有馬銜山,北有九州臺。馬銜山作為隴中高原最高峰和齊家文化重要玉礦資源地,是史前西北文明高地的重要文化名片,九州臺因傳說古代圣王大禹在此劃分九州而得名。在南北兩山之間、黃河之濱,躬耕敦煌學四十多年、成就卓著的李正宇先生就生活在這里。敦煌學誕生于甘肅,已經成為國際顯學,影響日隆。如果說馬銜山是史前時期的西北重要文化名片,那么,“敦煌學”就是中國古代歷史中的重要文化名片之一,更是甘肅省底蘊深厚、光芒四射的珍貴名片,而使這張名片煥發生命力的正是一代代敦煌學家。李正宇先生就是煌學家的重要代表之一,先生厚德載物,學識淵博,不但著作等身,還以高尚品格和春風雅量支持、幫助、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學者及文化工作者。我作為一名文學創作者,在從事敦煌文化題材小說創作過程中也得到李正宇等敦煌學家學術成果和精神品格的滋養。新近出版的玉文化長篇小說《禹王書》,我曾以為這種長年累月坐冷板凳打磨出的小說可能會很冷,沒想到,付梓出版剛剛一個月就售罄,目前已經在印制第二版。這幾天我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讀者?可能是我在小說創作中傾注了對山河風物的熱愛,傾注了史前文化、古代文化的精神活力!傾注了古圣今賢的博大情懷和仁義慈悲!
我特別摘取隨筆散記的《關于敦煌名稱來源的通信》,期望從一個側面窺測先生的學術品格。

關于敦煌名稱來源的通信
《山海經》之《山經》第三卷《北山經》記載:“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枬,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原。其中多赤鮭,其獸多兕、旄牛,其鳥多柝鳩。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窺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雁門之水。其中多魳魳之魚。食之殺人。”
徐客《圖解山海經》認為敦薨山為今河西走廊北端之馬鬃山;李正宇先生《“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論“敦薨”即“敦煌”》(《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認為《山海經》所載“敦薨之山”即黨河發源之黨河南山,而“西流注于泑澤”的“杠水”、“匠韓之水”及“敦薨之水”是疏勒河干流及其兩條重要支流榆林河、黨河。“敦薨之水”即黨河。關于黨河名稱之演變,李先生在文中說:
乾隆皇帝《陽關考》及常鈞《敦煌雜錄》與《清一統志》等皆以為黨河即高居誨《使于闐記》之都鄉河;王國維先生進一步釋黨河之“黨”為“都鄉”之合音。蓋不知“都鄉河”本是黨河在敦煌城西分出的一條灌溉干渠;又不悟“黨河”為蒙語“黨金郭勒”之省音漢譯,從而將黨河誤釋為“都鄉河”。
李先生考證“敦煌”應是大月氏語舊名;又據音韻學知識考證“敦薨”與“敦煌”同音異字:
《唐韻》《廣韻》《集韻》《類篇》《五音集韻》及《韻補》等書皆載“煌”字一音“胡光切”,音huāng(煌);一音“呼肱切”,音hōng(薨)。
表明“煌”字確有huāng(煌)hōng(薨)二音,為“煌”“薨”二字音通提供了直接的證據,進一步證明“敦煌”即“敦薨”。文中又考證:
清康熙年代地理學者儲大文就曾指出“漢敦煌郡,因敦薨山名。”(見儲大文《存研樓文集》卷8《取道》),近年,學者繼有探討,或謂“敦煌”語源為“桃花石(Taugas)”的對音,或謂“吐火羅”的對音,或謂羌語“朵航”(義為“誦經地”或“誦經處”)的對音,或謂即《禹貢》之“惇物”。王宗維先生亦嘗疑“敦煌”為“敦薨”之變音,惜未進一步揭示“敦薨”與“敦煌”同音互通之理,卻推測“敦煌是族名”,即“敦薨族”。“敦薨族”之稱,史所不載,據張騫之言,知其族實為“月支”,“敦薨”應屬月支語。至于“敦薨”一詞含義若何,尚有待后之達詁。
《山海經》之《山經》第三卷《北山經》記載:“(松山)又北百二十里,曰敦與之山,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泜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彭水。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泜澤。”徐客《圖解山海經》:“依據山川里程推測,此山應在今河北西部。”
敦煌馬圈灣出土漢簡,提到敦煌,寫法與今同。筆者曾看到有寫作“燉煌”的。是不是進入東漢或玉門關東移后才加了偏旁“火”?為什么要加?
1752年,《漢燉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銘》被征西大將軍岳鐘琪在巴里坤屯墾時發現。《后漢書》未記裴岑公元93年擊呼衍王事。裴岑時任敦煌太守,不可能無緣無故在“敦”邊加一偏旁“火”字,可見當時“敦煌”都寫作“燉煌”,據此,敦煌當為少數民族(羌?)語音譯。至于后來應劭記作“敦煌”,可能是取諧音而略改;之所以改“燉”為“敦”,在于書寫簡便,字形、寓意均好。
反證之,正因為“dunhuang”寫法不同,證明音譯時借用了同音不同形的字?這真是個有趣的話題,以后留心一下,收集些資料,探討。

2016年12月12日晚上8:36分,李正宇先生發來郵件:
玉雷先生:
1994年以來我與多識都曾是省政協委員,因而相識,也多有往來。曾討論過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敦煌“悉董薩部落”問題,但未討論過“敦煌名義”問題。至于認為“敦煌”出自羌語,李得賢《敦煌與莫高窟釋名及其它》曾有此說,以為是羌語“朵航”的對音,義為“誦經地”或“誦經處”(李得賢文刊于《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5期)。您說多識以為敦煌乃羌語之“音譯”,義為“北部”、“上部”。我不懂羌語,不知羌語敦煌之“音譯”讀作何音。“敦煌”古音讀作tun huang,李得賢所說“朵航”,顯然是“敦煌”的近現代讀音,與漢代“敦煌”古音不同,故不可取信。今多識教授所說羌語敦煌讀音若何?可與“敦煌”的漢代古音相合否?換句話說,多識所說的“羌語”,是什么時代的,可與漢代讀音相通否?須請多識先生釋惑。
李正宇謹復
2016-12-12

我于12月13日上午回復:
李老師好!2013年9月我在天堂寺拜會多識活佛,他說了很多個古羌語(與古藏語有關)的漢譯音詞;因為不懂音韻學,因此,未敢深入研究。今年6月考察黨河源頭,鹽池灣,寫文章涉及到這些問題,多了些探索;關于《山海經》所記“敦薨”,之所以一直未觸及,也是不懂音韻;偶然發現先生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論“敦薨”即“敦煌”》(《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非常興奮:可惜我收藏的《敦煌研究》正好沒有2011年,就沒讀到先生大文。看到您的文章,才知道樊錦詩在演講中引用的就是您的觀點。
我與先生目前觀點相異處,惟在“敦煌”源于月氏語還是羌語。不知道月氏語與羌語有什么關系?
下面是我文章中的部分,發給您,請指教!(此處略)
馮玉雷 上
2016-12-13
12月12日晚上,敦煌作家夏惠發來微信說:“馮老師,看到您最近很關注‘敦煌’二字之起源,謝謝您!我也一直在想,不過,我想的是學者岑仲勉的看法:他認為敦煌的詞源是‘桃花石’(Taugas),也就是拓跋氏,這還需要深入。網上還有篇文章,看能否給您參考下。”
接著,他發來張博泉《“桃花石”的名義與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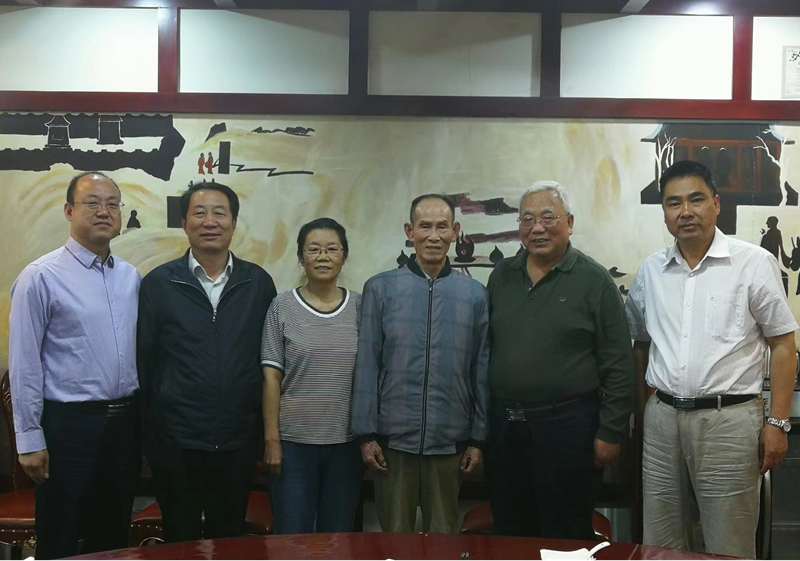
2016年12月13日晚上、李正宇先生來信:
玉雷先生:
1.“當”、“黨”、“當金”、“黨金”、“丹增”與“敦煌”讀音互不對應。敦煌古音“屯黃”。
2.況且羌、蒙藏語之“當金”、“黨金”、“丹增”,早不過唐代(“丹增”)甚至晚到明清(“當金”、“黨金”),而戰國及西漢時已有“敦煌”之名。不可拿后世詞語比附古詞語。
3.“敦煌”之敦作“燉”,并不始于東漢(如裴岑、應劭)。司馬遷《史記》中已有之。如《史記·匈奴列傳》:“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后,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又《史記·大宛列傳》“燉煌”出現四次。
李正宇
2016-12-13
我于12月14日早晨回信。
尊敬的李老師:
您好!認真拜讀來信,非常感謝百忙中不吝賜教!
您的所有觀點我都沒有疑議,而且覺得這是目前最客觀、最接近事實的論點。
這個問題主要涉及到音韻學,而我對此一竅不通,故而對相關問題無法深入研究;也不具備對所有觀點進行甄別的能力。之所以涉獵這個話題,主要推測“敦煌”可能是民族語言音譯。對您的復信,我謹解釋如下:
1.多識教授2013年9月所說,“敦煌”是古羌語演變、轉音結果,但不可能是直接對音。這個問題,如果您有機會與多識教授見面探討,或能更有收獲。毫無疑問,用音韻學專業知識記錄古音(或者推測的古音)要遠遠比現代漢語來代替要準確。但是,我沒有能力用專業記錄方法來記錄,大概是我記錄方面的問題;多識教授說法應該比較可信。多識教授另外一種身份是活佛,佛教講“不妄語”;他這樣說應該有證據,是慎重思考的結果。正因為如此,在我不具備判別能力的情況下引用此觀點并撰《敦煌六章》在《絲綢之路》(2016年16期)文化版發表;
2.“當”、“黨”、“宕”或許都是古羌語同一轉音。這是我個人推測。
3.“黨金”、“丹增”屬于藏蒙語言合成詞,即“黨”、“丹”為藏語,而“金”(果勒)是蒙古語,后來又有藏、蒙、漢三種語言合成詞的現象。這方面的知識是請教了新疆社會科學院才吾加甫研究員——他是土爾扈特人,懂蒙古語。
4.月氏語與羌語或其他相關民族語言中是否也存在類似混雜現象?例如現代詞“吉普”之對譯英語“jeep”,還要加上車,叫“吉普車”。
5.漢朝文獻中經常提到的燒當羌及當煎、當闐、封養、鐘存等羌族諸部落是否與多識教授所說古羌族“黨”部相關?
6.關于馬圈灣漢簡和裴岑碑所記“敦煌”、“燉煌”問題,之所以沒顧及《史記》或相關文獻,是考慮到出自敦煌本土(或相當于本土,例如裴岑碑雖然不在敦煌,但裴是敦煌太守)的文獻——第一手資料最可靠;而內地學者在引用材料時有可能會出現以訛傳訛的情況。先生所列證據表明,兩漢時期“敦煌”、“燉煌”可能都在使用,后來才逐漸統一使用“敦煌”。
7.我可能沒有表述清楚,我打算說明裴岑時期正在使用“燉煌”,而不是說從“敦煌”改為“燉煌”;我僅僅疑惑何以馬圈灣漢簡幾乎全部記作“敦煌”,而后來卻又變成“燉煌”?我要表達的本意是:敦煌作為郡名,無論如何也不會出獻錯誤,就像現在不可能把甘肅寫作“甘蘇”、“干蘇”之類。
8.昨天才看到先生大作,實在遺憾!先生大文,乃是糾謬校偏之力作!可惜,2011年之后還是有學者按照應劭的觀點解釋“敦煌”,人云亦云。
先生積淀深厚,廣學多聞,不勝景仰!對玉門關、河倉城等問題糾謬校偏,功德無量!關于敦煌名稱問題,我感覺您之大作已經說清楚了,惟一一點,“敦煌”最早究竟是“月氏語”音譯還是“古羌語”音譯,原義是什么,不管有無確鑿證據最終能厘清,其實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類似語言、文字消失或變為死文字的現象也不少。
非常感謝先生多次賜教!真誠感謝!
順頌
文祺,健康!
晚輩后學 馮玉雷 敬上
2016-12-14
2016年12月31日早晨8點10分,到西北民族大學參加“絲綢之路民族與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暨甘肅省歷史學會第25屆年會”。去了才知道被安排發言,便打車回單位,充實并改成《有關敦煌文化的兩個關鍵詞:玉石(玉門關)、敦煌》,大會宣講。本來寄希望求教于專家,引起爭論,因為會議時間緊張,取消討論環節。茶歇時,李并成先生介紹譚世寶、王宗維兩位先生的文章。他認為漢朝要向西開拓,如同“武威”之類取名模式,取“敦煌”者,就是“要將漢朝盛大輝煌的經濟文化氣象照亮西方愚昧的天空”;這也能解釋通。但能解釋通的未必就是歷史事實。存疑。
2017年3月16日,我們籌劃“絲綢之路甘肅段語言文化調查活動”,擬邀請李正宇先生參加,特發去郵件:
尊敬的李老師,您好!
我們4月2——8日將舉行一次短暫的文化考察活動,您能否通行?
考察中,我計劃將去年與您關于敦煌名稱問題通信記錄以考察記形式發出來,目的是引起學界注意。因為您的大文已經說清了敦煌名稱來源,但有些學者還是以訛傳訛。我是贊同您的觀點的,如果此前看到先生在《敦煌研究》上發的大文,就不可能有我后面推測性的文章。
順頌
康安!
馮玉雷 謹呈
2017-3-16
23日,先生再次回復:
玉雷先生:
收到《關于敦煌名稱來源的通信》。讀后,覺得很有意義。一方面反映人們對敦煌問題的關注;另一方面反映人們對敦煌地名語源及語義的探討,涉及敦煌古代居民種族問題。關于敦煌一名的來源及含義,可能還要討論下去,真理愈辨愈明嘛!
李正宇
2017-3-22
李正宇先生德高望重,才學深厚,碩果累累。我非常尊重他!這次關于敦煌名稱的來源問題連續幾次通信,更見先生嚴謹之學風!
(作者系甘肅文化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一級作家)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編號:6212006002 | ICP備案:隴ICP備17001500號 | 經營許可證編號:甘B2-20060006 | 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許可證編號:(甘)字第079號增值電信業務許可證編號:甘B2__20120010
食品藥品監管總局投訴舉報電話:12331 | 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電話:12377
主辦:甘肅中甘網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 本網常年法律顧問團:甘肅和諧律師事務所(0931-8580115)甘肅天旺律師事務所(0931-8864528)
Copyright © 2006 - 2024 中國甘肅網(GSCN.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網站簡介 | 人才招聘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電話: 0931-8960109 0931-8960307(傳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