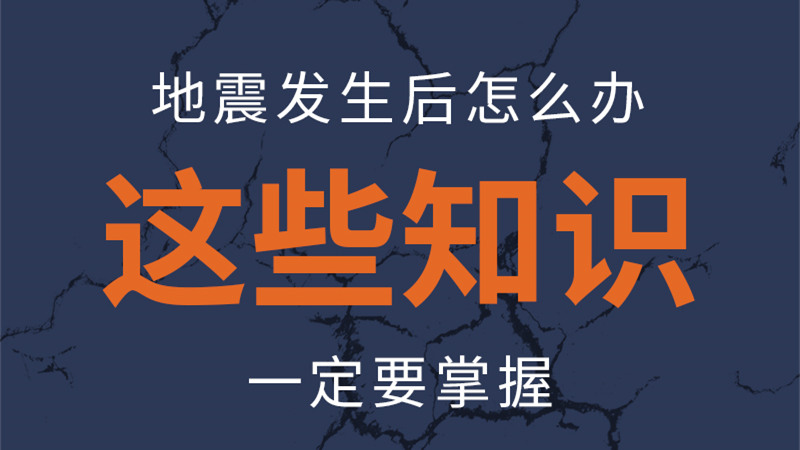本報特約撰稿人 林茂森
臨松(今張掖市肅南縣臨近松林的馬蹄山區)薤谷(即生長馬蓮或馬蘭的一條幽深山谷),位于張掖市區南60公里。這里溪流淙淙秘谷幽境,曾是避世修身的世外仙境,兩晉時期的大儒郭荷及郭瑀、宋纖、劉昞等文人名士在此隱居,聚徒傳道,鑿窟造像,因此臨松薤谷成為中原與西域國學文化傳播的中轉站和石窟藝術創作的發端地。
時勢造英雄 板蕩識忠臣
西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青年將軍霍去病“攻祁連山,揚武乎觻得”(《漢書·霍去病傳》),西漢攻打匈奴河西之戰大捷,漢武帝設“河西四郡”、“張國臂掖,以通西域”(《漢書》),張掖由此而得名。在長達400多年的兩漢統治時期,得益于祁連山冰雪和黑河豐沛水源滋養,河西走廊綠洲農牧業、商業貿易發達,張掖戈壁呈現出半城濕地、半城蘆葦的獨特風貌,因此享有“塞上江南”的美譽。
西漢末年,從王莽攝政簒權更始帝劉玄亡西漢,到光武帝劉秀洛陽建東漢時期,一個世祖三輩曾做過張掖太守、武威太守和護羌都尉的顯赫世家后嗣,在戰亂頻起的中原亂世里出道了,他就是張掖屬國都尉、河西五郡大將軍竇融。
竇融,今陜西咸陽人,由忠誠謀士班彪輔佐,赦放囚徒效力邊防、懷柔胡羌鼓勵農桑、官辦市場活躍商貿,經略河西13年歸順東漢,《后漢書》載:“竇融據河西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兇饑者,歸之不絕”。那時內地曾有多位達官顯貴、飽學之士,以及戰亂流民前來張掖躲避戰亂,竇融號令各郡妥善安置,歸之麾下為我所用,以充實河西邊陲空曠之所。一時間河西出現了“蕃人舊日不作犁,相學如今種禾黍”“城市街坊時見異商,館肆茶舍南腔北調”的興旺景象。從而使張掖成為河西政治軍事統治中心。
俊鳥棲佳木 高士隱幽境
西晉末年(公元301年),護羌校尉張軌出任涼州刺史,州治武威郡姑臧縣。張軌世家以專攻經學著稱,他采取中原“重教化”與“拔賢才”之策,招收河西學子500人,聘知名學士開辦官學,從而使河西儒學蓬勃興起。
正是因為兩晉時期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又因為河西走廊中段的東大山、張掖南山和酒泉南山一帶實為世外仙境,更是一個避禍修行潛心治學的好地方,因此一代大儒秦州略陽(今甘肅秦安縣)高士郭荷,與內地投奔者一路向西,在河西走廊扎下根脈,后來成為“河西望族”。隨郭荷而來的不僅有門生弟子,還有汗牛充棟的家傳經史典籍。郭荷在河西悟道授儒,結廬講學,為儒學傳承開枝散葉奠定基石。
郭荷出身于經學世家,其家族以儒學為尊。郭荷師徒來張掖尋得傳說中老子騎青牛避世,著《道德經》的東大山結廬講學。郭荷隱居東大山聲名遠播,河西學子們紛紛前來求學,敦煌人郭瑀就是飛來的一只俊鳥,也是郭荷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同時代和后來卓有成就的河西名士,還有宋纖、索靖、宋繇、劉昞等人,其成就對后世儒家漢學傳承產生了深遠影響。
郭荷的聲望使前涼王張祚竊喜,張祚雖承襲曾祖張軌崇文衣缽,但骨子里卻假借儒士裝點門面。郭荷身處亂世,秉承不為官祖訓,潛心修身傳道授業做學問,但終究抵擋不住“三顧茅廬”的“請求”,使者請其出山做張祚主管官學的博士祭酒,為光大弘儒大業,郭荷興沖沖拜會張祚,禮遇他的卻是涼王宮內太子陪讀的閑差。而此時受同樣冷遇的還有儒學高士敦煌效谷(今甘肅瓜州縣西南)人宋纖。年事已高的宋纖被逼,走出隱居30余年的酒泉南山,被婉囿于涼州前涼王宮,一生才華難以施展,郁郁憤懣,絕食自盡,終年82歲,身亡后獲得解脫,留下儒學雅士的高潔清名。時敦煌太守楊宣為其畫像并賦詞:“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表達對宋纖的仰慕和緬懷之情。張祚的昏聵狡詐與宋纖的可悲遭遇,令耄耋之年的郭荷對官場心灰意冷,他向張祚請辭得到應允,由入室弟子郭瑀陪伴,隱居于臨松薤谷。
傳道著述之 根脈得承傳
秦安人郭荷與敦煌人宋纖應該是儒家同時代中人,且郭荷親眼目睹、親耳聆聽過宋纖的人生經歷,對宋纖聚徒講學和被迫出山遭冷落感同身受。宋纖少有大志,天資聰穎,一心向學,不慕榮利(《晉書·隱逸傳》)。東晉前涼張駿在位時,宋纖尋“穆王會西王母觀黃帝之宮”(《穆天子傳》)之瑞象游學,隱居于距酒泉南30里處的昆侖山支脈酒泉南山悉心著述,為《論語》作注,依崖鑿窟,靜心修身養性,終日聚徒講學,受業弟子3000余,堪比先賢孔圣,成為名震河西的一方大儒。
這一時期同是敦煌儒生的郭瑀也游學張掖,拜在著名大儒郭荷門下,潛心攻讀儒學,精通經義道法,成為郭荷門生中最有成就和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自郭荷從姑臧返回臨松薤谷,官場失意,身心交瘁,不久便與世長辭,終年84歲。郭荷離世,郭瑀為老師的不公遭遇惋嘆,師生之情如同再造,師生之誼重如昆侖,郭瑀遠離塵世紛擾,為恩師守孝三年,儒家的哲學思想早已浸入郭瑀骨髓,老師修身傳道的終身大業銘刻于胸,郭瑀率領弟子們走向臨松薤谷深處,開鑿石窟,設館講學,著書立說,弟子千余,著有《春秋墨說》《孝經綜緯》等巨作。
郭瑀講學著作期間,不斷有年輕學子慕名求學,在傳道授業解惑之余,為解決弟子安身之所,帶領學子在馬蹄山開鑿石窟。在他的千余門生中,卓爾不群的劉昞是出類拔萃者之一。劉昞天資聰穎,博聞強記,十四歲時來臨松薤谷隱居,拜郭瑀成為入門弟子,他勤奮好學,深得郭瑀器重。
其時,前涼統治繼任者張天錫,遣使召郭瑀,遭嚴詞拒絕。涼使抓捕郭瑀弟子要挾,郭瑀正色道:“吾逃祿,非避罪。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東晉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前秦滅前涼,秦文昭帝苻堅饋以厚祿,請郭瑀出山規制朝廷禮制,郭瑀因為父親治喪守孝,回敦煌聚弟子300講學。淝水之戰后前秦長史王穆起兵,對抗反叛前秦的后涼主呂光,郭瑀不顧劉昞勸阻,毅然辭別弟子出山,聯合敦煌旺族太守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約定于張掖相機而動策應王穆,時官拜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后王穆聽信讒言殺索嘏,郭瑀苦諫無果,悲憤中棄王穆而去。回到酒泉南山,郭瑀嘆息:“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旋“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與疾而歸,旦夕祈死”,即面壁赤崖閣飲氣而卒。
郭瑀去世后,劉昞吸取前車之鑒,隱居于酒泉南山繼承師業,聚徒講學,門生五百余,專事學術研究與著述,著有《三史略記》《敦煌實錄》《涼書》等百余卷并行于世,成為蜚聲河西的一方大儒。前秦、后涼政權多次征召,劉昞均婉言謝辭拒赴命。李暠割據河西建立西涼后,劉昞應征拜儒林祭酒和從事郎中,以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主持國學教學及典籍校勘。李暠曾把自己得到劉昞,比作劉備得到諸葛亮而欣喜若狂。沮渠蒙遜滅西涼后,任命劉昞為秘書郎專管教育。北魏一統北方之后,涼州樂平王拓跋丕拜劉昞從事郎中,主持教育。后北魏令河西儒士歸國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劉昞因年邁告老而留在姑臧。臨松薤谷風景秀美,山嵐間云纏霧繞,是隱居修身、聚徒講學的寶地。劉昞對臨松薤谷情有獨鐘,晚年離開姑臧在這里安居。公元440年,劉昞在返回敦煌途中病逝,一顆儒壇巨星隕落,但他的文壇地位和卓越貢獻將彪炳史冊,永遠昭彰后世。
依窟造佛像 文藪留圣跡
在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河西史上,沮渠蒙遜是一位卓有建樹的歷史人物,為河西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尊崇儒學,創辦學館,校撰典籍,使北涼國內禮法盡依漢制;還篤信佛教,優厚高僧,開鑿石窟,興建塔寺,校譯經卷,普及佛學。這些開明之舉不僅使北涼出現了文化繁榮的景象,也有力地推進了多民族間的大融合。
沮渠蒙遜征伐西涼,攻克酒泉,在宋繇家中得書數千卷。他興奮地感嘆:“孤不喜克李歆,愿得宋繇耳。”時宋鷂雖為西涼重臣,卻也是一位學界大儒,北涼遂拜宋繇尚書吏部郎中。北涼從張掖遷都姑臧后,“起游林堂于內苑,圖列古圣賢之像”,蒙遜常與群臣說論儒家經傳,令兒子沮渠牧健尊劉昞為國師。蒙遜曾給闞骃“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余卷”(《魏書·列傳·闞骃傳》),其數量遠超整個北涼所譯的佛教經典,為中華文化遺產的傳承作出貢獻。
蒙遜于公元429年冬“復遣使至宋入貢”,除“獻青雀頭黛百斤”外,“并求周易子集諸書,詔并給之合七十五卷。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集》弘與之。”蒙遜求書尚若斯,可見其學儒之心切。他不惟推崇儒學,禮敬仕賢重用人才,亦對佛教頂禮膜拜,普及佛學,鑿窟造像,推廣佛教繪畫藝術,對北涼政治文化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北涼時期,河西儒學圣地張掖南山、酒泉南山,在經學先賢們率弟子開鑿講學石窟的基礎上,后人皆陸續擴而廣之,增塑佛像,壁施繪畫,并逐步形成規模宏大的施道寺廟。
蒙遜遷都武威,廣召天下工匠開鑿石窟,有涼州天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北涼三窟(第268、272、275窟),玉門昌馬石窟下窯第4窟,酒泉南山(文殊山)石窟千佛、萬佛二洞,張掖南山(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東西二窟等。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是世界上現存規模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酒泉南山文殊山千佛洞內的北涼壁畫運用西域凹凸邊暈染法,將四壁繪滿千佛;張掖南山金塔寺東西二窟保存有北涼以來的彩塑260余身,懸空于壁間的立體飛天高肉懸雕,將圓雕和浮雕完美結合,要比敦煌飛天早300年,為彩塑藝術精品中的精品。
十六國時期的佛教石窟開鑿,不僅培養了大批開鑿石窟、精于塑繪的技藝人才,繁榮了燦爛的文化藝術,記錄下寶貴的歷史故事,保留下珍貴的文化遺產,而且對當時安定社會,緩和民族矛盾,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發展,發揮了積極的助推作用。
藝術發端地 國學中轉站
五涼時期佛教自河西盛行于內地,薈萃于河西儒學文壇的大家們,以深邃敏銳的目光和兼收并蓄的胸懷,為這個來自恒河兩岸的異域宗教文化提供了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必要條件。張掖馬蹄寺石窟群、文殊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劉昞率領弟子,為研習經史講學讀書而開鑿,最終發展成了佛教圣地,河西儒家文化的源頭地位,也逐漸為佛教文化所取代。
在涼州天梯山石窟開鑿的同一時期,祁連山西線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相繼造像,接下來這種“涼州模式”的石窟造像藝術風格,又由姑臧高僧曇曜和內遷的工匠們帶到了中原,從天水的麥積山北朝石窟和隴東的北石窟寺,到山西平城的云岡石窟,再到洛陽的龍門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藝術所取得的成就,無不閃耀著河西石窟藝術的熠熠光彩。
郭荷、郭瑀、劉昞三代師徒,是五涼時期河西儒壇的典型代表,當年郭瑀在臨松薤谷結廬鑿窟,設帳講學著述,因為他們的帶動和影響,河西公學、私學興起,民間求學之風盛行。盡管中原地區的中華文明和國學文化遭戰亂破壞,但因為五涼統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河西學者皆堅守儒學傳承使命,呈現出官學私學相輔相成,教學著述繁榮發展的景象。
五涼時期,劉昞是學術著作最多的學者,在他的《敦煌實錄》和《涼書》中,記錄下河西走廊百年風云史,被北魏孝文帝譽為“德冠前世,蔚為儒宗”的河西大儒。漢文化在河西得到保護傳承和延續創新,反過來又倒逼中原國學文化慘遭破壞后的復興。《宋書》記載:北涼后期河西向東晉朝廷進獻典籍154卷,其中有失傳已久的西晉以前的古籍,也有劉昞等河西本土學者的著作。較為典型的是十六國時期在中原和江南已失傳的魏晉時期名著《人墓志》,就是由于劉昞為其作注被保存下來并返還江南。這部分古籍著作,是河西走廊對中原王朝厚重的回饋,更是為整個中華民族國學文化傳承作出的獨特貢獻。
- 2025-01-07甘肅省舉辦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直通車進校園活
- 2025-01-07甘肅10名師生獲高校畢業生基層就業卓越獎
- 2025-01-06暖心護航 助學子圓夢——2024年省委省政府為民實事困難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學資助工作取得實效
- 2025-01-06閱讀點亮生活 書香浸潤金城 “書香蘭州”建設推動全民閱讀走深走實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