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走索橋堡
□王復庫文/圖

初冬的一天,我們沿著古絲綢之路北線前行。穿過平川區水泉堡大峽谷,翻越裴家堡峴口,進入哈思山原始森林地帶。大雪紛飛,汽車在彎彎曲曲的砂硌山路上艱難爬行。
快要和索橋古渡見面了,我們激動不已,思緒似窗外的雪花,在哈思深林中飄舞。
到達靖遠縣石門鄉哈思吉堡,天完全放晴了。哈思吉堡離索橋古渡東岸15公里,我們棄車步行繼續向目的地挺進。
一個70多歲的祁輝老師,一個60多歲的祁有榮老師,為我和兒子帶路做向導。
談起索橋古渡,祁輝老師有說不完的話題。祁輝老師在當地中學教書,研究索橋古渡50年,曾站在哈思海拔最高的山頂看黃河落日,感受張騫翻越哈思山,沿索橋古渡過黃河的傳說故事。
索橋渡口東岸的哈思吉堡,蒙語意為“玉也”。《康熙志》載:明隆慶六年(1572年)建,憑勢筑堡,三面陡峻,是稱天險。寇或入犯,迄不得逞,誠戰守重地也。哈思吉堡先是管轄和護衛古索橋渡口、保障絲綢之路安全暢通防御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堡寨,后又有防御兼驛站功能,明末開始成為一個大型商貿交易市場,陜商、晉商絡繹不絕。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兩省7府30個縣商人捐資修路時立于索橋橋東的《山西修路碑》載,索橋古渡東岸的哈思堡當年有大車店18家,是商旅過境休息和貨物交易之處,有店費“日收斗金”之說,可見其當時的繁榮程度。
山路彎曲,我們先沿溝壑前行,再翻過數座山梁,再沿溝穿行。我不知道古代軍旅、商旅們是怎么走這條道路的。行走的意志力被摧垮了,我想回頭。兩位祁老師說:“現在回去的路比去索橋的路還要遠”。我們只能跟著兩位老人慢步前行。
太陽已爬上山頂,我們才來到索橋堡東岸。兩位祁老師要趕著返回,留下我和兒子拍攝索橋堡遺址。遺憾的是,索橋堡溝谷深邃、陰山太大,索橋古堡遺址沒有了光影。
站在東岸堡寨的石碣門上隔河相望,河對岸的古堡遺址黑沉沉的,峽谷陰影里的殘垣斷壁如同一支支軍隊在布陣練兵,暮色中的索橋堡古建筑群遺址靜謐而神秘。
環顧四周,山巒峽谷溝壑里連一個人影也看不見,仿佛連自己也不存在了,只有孤寂的黃水在空曠的峽谷中回吟。
我的心一下空曠起來,拍攝晚霞輝映下千年古堡的美好愿望,從夢中消失了。
沒有拍到日落,我們對拍攝日出更加向往,毅然決定夜宿索橋堡。
天黑麻的時候,我們在黃河岸邊一片野棗林里發現了一個小石頭房子,破舊的木門,塌陷的土炕,屋頂的一半是露天的,這便是我們今晚的宿營地了。
深秋的夜晚,風大,星空格外明朗,星星漫延在蘆葦蕩中,灑在暗淡的河里。窎窎坡傳來貓頭鷹的叫聲,聲音在峽谷中飄渺,遙遠得好像從千年漢墓中發出的呼救聲。
風不停地在叫,河水在石屋后流淌著,呼嘯著。
很累很困,卻怎么也睡不著。迷迷糊糊,仿佛有人敲門,聲音很清晰,張騫騎著黑紅色的馬來了,幾十輛馬車擁到索橋堡橋頭,要從索橋過黃河。不幸的是,車馬行人全被匈奴擋在了索橋堡西橋頭。雙方對峙了半夜,索橋起火了,連索的24艘木船全被點燃了……風很大,火直往我身上撲,把我從夢中驚醒,拍拍身上沒有火,靜聽是外面河水的聲音。
由于一夜的夢中驚嚇,我活動了一下,腿不聽使喚了,撐著胳膊起身,身上全是土。
扒開蓬草堆,我和兒子背上相機拼命地向山邊跑。太陽已曬到索橋堡西岸,拍日出的事被昨夜的惡夢給攪和掉了。
從石崖上艱難地攀爬了半個小時,才來到東岸堡寨的石碣門上。太陽光已跑過點了,我們趕緊架起相機,準備拍攝。這當兒,一朵黑云擋住了太陽,索橋堡遺址沒光了,河面沒光了。我們唯有坐在堡墻上嘆氣,只能等云去光回,太陽再露出臉。
索橋堡渡口是漢武帝時期開通的黃河官渡渡口,是古絲綢之路北線古渡群中最主要的渡口。漢武帝破匈奴收復景泰,為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開辟了西進通道,而距索橋古渡15公里的媼圍縣城(今景泰縣蘆陽鎮吊溝)的建立,又保障了絲綢之路北線西渡黃河各渡口的暢通。
索橋古渡橫跨靖遠、景泰兩縣。黃河東岸的索橋堡在今靖遠縣石門鄉哈思吉堡西北15公里處,堡墻、石棧道、石臺階和石碣門遺址尚存。黃河西岸的索橋堡在漢置媼圍縣城西北15公里處(今景泰縣蘆陽鎮境內),堡寨遺址尚存。
由于甘肅黃河北出口段屬中原王朝與匈奴、吐蕃等西域民族長期爭奪地帶,在明朝以前,索橋古渡因戰亂和朝代更替,權主歷經頻繁變更。索橋古渡曾是漢渡、唐渡、明渡的官渡渡口,也曾是匈奴渡、吐蕃渡、西夏渡。
索橋古渡一直是船渡或筏渡渡口。“索橋,名橋而實無之……索橋不過鼓棹浮舟,往來津渡而已……”。(《秦邊紀略》)。明隆慶元年(1567年),古渡兩岸間修建索橋墩柱基,用蓆子編制成碗口粗的繩索系在兩岸四根“將軍柱”上,再將24艘木船固定排列掛于繩索之上成為浮橋,索橋由此得名。
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重修被河水沖毀的索橋,并在河東岸修筑堡寨鐵鎖關(堡址尚存),門上有碣,額曰“索橋堡”,駐兵防守,以確保渡口的安全暢通。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在河西岸的小坪上建索橋堡,堡內居民曾達300戶。直到清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南大道西(安)蘭(州)公路開通之前,索橋古渡一直是絲綢之路北線進入河西走廊的必經渡口。清代乾隆后期,索橋古渡逐漸沉寂,北線商旅通過烏蘭關、北卜渡西渡黃河。
現存黃河西岸的索橋堡遺址還能辨認出街道、院落、店鋪、門樓等。堡城外的瞭望哨所、廟宇、烽燧、五座旗墩,渡口處“將軍柱”臺基和堡內石街石樓上的殘垣斷壁,愴然訴說著當年索橋商旅云集、古渡繁忙的輝煌景象。
歷史是游走的。望著索橋堡石碣門上的雕刻,隱隱約約還能聽見吐番、匈奴在索橋堡殘垣斷壁的小巷穿行的腳步聲。他們從不同歷史時期走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或者被貶謫,或者被殺戮……那時沒人拍照,司馬遷也未來這里采過風,索橋古渡沒能進入《史記》,任憑恢弘的歷史在河水和暮風中飄流。
河水是有記憶的。兩千多年,歲月滄桑,朝代更迭,寨主頻易……殘缺的索橋堡就是歷史上無數個輝煌的永恒,多少風云人物從古索橋這個歷史舞臺上走過,來去匆匆,人們來不急看清他們的容顏,就消失在濤濤黃河哀嘆的回聲里。
黃河與索橋堡又有著怎樣的美麗錯過?我們無法解開和還原張騫西渡黃河的歷史密碼。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張騫奉命第一次出使大月氏。傳說張騫一行用了三天時間在哈思群峰中找尋最佳渡口,張騫登上松山極頂遠眺,在諸多河灣峽谷中踩點,只有窎窎坡對岸有河谷溝壑,可通往西域,且哈思山松林繁茂隱蔽性強,滿山遍野的油松,質輕利水易造船渡河。最終選擇了窎窎坡上峽口為索橋渡口,西渡黃河。
夕陽西下,彩霞滿天,索橋堡的殘垣斷壁上閃耀著魅惑而神秘的光芒,黃河像一幅金燦燦的油畫掛在東西索橋堡之間,讓人流連忘返。
只顧拍照,忘了身處無人區,忘了回家的路。
突然想起小口子村的友人石貴清先生,他會開三馬子,拿起手機,沒信號。我們想抄近道返回哈思吉堡。走到峽口時,兩邊萬丈石崖,中間像刀切的一個石縫,峽谷險峻,無法逾越。
退回的時候,迷路了,走進一大片古墳地。暮色中,從遠山峽谷中走出了一群綿羊,步子很輕,好像飄在云朵之上。羊群后面慢悠悠飄隨著一個滿頭銀發的牧人,遠遠看去像一只老山羊在暮色幻影中直立行走。
我們激動不已,聲音放到最大分貝急切地喊到:“老大爺,走哈思吉堡有捷徑嗎?”
牧人搖搖頭,恍惚間和羊群一起消失在遠山的背后。
暮色漸濃,四野空曠,沒有行人,沒有歸鳥,唯有西岸堡寨的那些殘垣斷壁在相互低語、凝視、交談……
兩千多年,索橋古渡褪盡了喧器與繁華,孤獨和迷茫牽絆著它的靈魂,任何高端的攝影器材都無法拍攝它的內心世界,只有濤濤黃河日夜不停地守護著它的初衷,而我和沉重的相機只是索橋堡的過客。
風還在吹,手機還是沒信號,天已黑盡了。
今夜,我們還得再宿索橋堡。









 中國舞劇《孔子》亮相莫斯科
中國舞劇《孔子》亮相莫斯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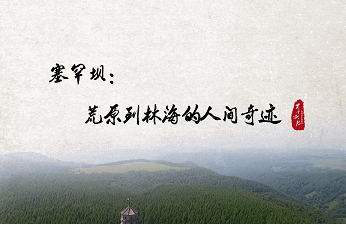 電影《那時風華》展現塞罕壩精神
電影《那時風華》展現塞罕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