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爛漫綻放時
□韓德年
四月芳菲,在料峭春寒仍然纏綿難舍的高原絕對是一個奢侈的愿景。裸露了一冬的原野依舊蕭索荒蕪,只有蹲下身子,撥開干枯的蓬草,才會發現頑強的冰草芽從枯根中抽出的綠尖,怯怯地泛一抹春的羞澀。被剛剛播下麥種的田地,捂住自己貧瘠的胸,想把蘊藏了半年之久的不多的乳汁哺乳給冰冷的種子。一群紅嘴鴉似一片油亮的黑云泛著紅光鋪到地里,啄食剛剛探出嫩尖的草芽,也啄食剛播下不久的種子;才出蟄不久的阿拉善黃鼠,用兩只后腿人立在田埂山坡盡情地鳴叫——“啾啾啾啾”,那聲音就像鐵釘快速地來回劃過玻璃一般的撕裂耳膜,卻也給闃寂的山野傳遞了些許生機;遠處山巔的山雞不滿黃鼠的嘶鳴,也不服氣地“嘎達嘎達”絮叨不已;尖銳與圓潤兩道高音在空曠山野間絞纏碰撞,終于惹怒了空間的霸主,一只“黃健子”(隼的一種)似一頁風箏,撲棱棱定在碧藍的天幕,一串機關槍似的尖銳急促的鳴叫,似鋒芒萬丈的劍氣掠過虛空,冰冷的肅殺讓整個山谷霎間入定——山谷就這般喧鬧在寂寥的春困里,慵懶中裹挾著躁動,閑適里暗藏著刀光。奮力生長的冰草大膽地吐了吐嫩綠的巧舌,仿佛在嘲笑動物們無謂的爭鋒。
我的入侵,打破了山間微妙的平衡。各種的鳴叫聲戛然而止,靜的瘆人的鴉群,驀然爆發出一團裂帛般的嘎呀聲。我翻過一道道嶺,越過一道道溝,已到了山溝的最深處,不過只找到了幾株鎖陽根(這是我此行的目的)。當再次爬上一道平緩的峴口時,我忽然被眼前的景象擊懵了,一瞬間腦子一片空白,變成了一張立體的相片。我看見了一棵樹,一棵杏樹,一棵被緋紅的煙霏籠罩的杏樹!我蒼白的語言無法形容她璀璨綻放的妖冶俏麗。宋人有“紅杏枝頭春意鬧”的名句,卻覺這詩句里的杏花宛然是一個爛漫天真又調皮的豆蔻少女;而宋徽宗趙佶眼里的杏花:“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又像是一位端莊嫻淑眉鎖愁云的宮娥。若是非要以人譬花,那眼前這夭夭灼灼婀娜似妖的滿樹杏花,更像是一位濃妝出閣的新娘。眼眸中盈盈洋溢著綺麗的憧憬,面頰上氤氳著妖魅的誘惑,云鬟低垂燃燒著青黛的情思。“仿佛兮若輕云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靜謐山阿、明麗春陽、赤裸田野,全都沉醉窒息于她驚世駭俗的顧盼流眄間。沒有嘉賓良媒,沒有華堂云車,沒有瓊樓玉閣,沒有禮贊喝彩,沒有曼舞清歌,只有蒼涼山隅,童禿垅畝,無垠之碧空,輕寒之東風。而她依然沉湎于似有還無的柔情幽思中,依然流光溢彩于瑰艷綽約的風韻里。寂寞中透著超凡的睿智,孤傲里盡是脫俗的赤忱,率意里詮釋著生命自在的真諦,若水的柔美里卻是一往無前無羈無絆的無畏。她收集了山野所有春光里的柔軟煙靄,她涂抹了山野間所有的瑰麗華彩,她芬芳了山野中所有的馥郁幽香。她是行走在蒼茫高原的寂寞劍客,她是舞蹈在天幕地臺上的孤獨舞者,她是荒原暮春里僅存的赤子。原野的春情因她的踟躕山隅而一瀉汪洋……
多少年過去,無情的時光湮滅了幾多世道的丘壑,但那山隅里邂逅的翩若驚鴻的倩影非但未被磨滅,反而被歲月醞釀的更加靈動、活潑。我曾經幾次再去山間,眾里尋他千百度,而見到的不是一樹蔥蘢,即是虬枝如鐵,那如真似幻的綽約風姿卻再也無緣得見。
找尋中,我在小區的院子看到了一棵楸子樹,初冬的凜冽剝去了他一身的葉子,裸露的枝條上出現了一串串只有仔細看才能發現的楸子,僅有豌豆大小,剛看見時他呈殷紅色,幾天后顏色加深,到后來變得絳紅。仿佛只有嚴寒才會加速他的成長。他們個頭太小,味道酸澀,連院子里上天入地的熊孩子都懶得理他。但他依然一絲不茍的成熟著自己,盡情地在小雪季節里綻放專屬自己的靚麗。我還找尋到了許多平凡的人,他們不以物喜,不因他悲,只在乎自己生命里的璀璨綻放,只專注自己內心天空的那片明媚陽光。他們都和山坳里絢麗的杏花擁有相同的徽章。
我忽然頓悟,既然他們是行走天地間的獨行者,是隱身山阿只為順應自然而自然的精靈,是純粹因生命絢爛而絢爛的純粹者,又怎能茍同于凡夫俗子的淺陋粗鄙?又豈會因為我的仰慕而迎合出被仰慕的模樣?又豈會因為他人的漠視而因之輕賤自己?
你若爛漫綻放時,任憑他荒郊野嶺抑或冷淡漠視!









 中國舞劇《孔子》亮相莫斯科
中國舞劇《孔子》亮相莫斯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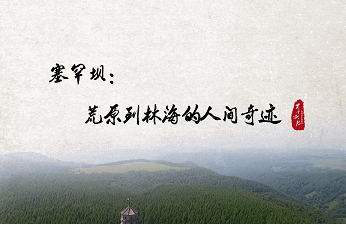 電影《那時風華》展現塞罕壩精神
電影《那時風華》展現塞罕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