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澈通透的白
“下雪了。天明了。”母親說。我驚喜異常,揉揉惺忪的睡眼,抬頭朝糊著白色油光紙的木格子窗戶往外看。咦!真個是白花花一片。抽門閂開門看瑞雪,是十分有趣的事兒。這雪不知啥時候落下的,此時繼續悄無聲息地飄著,地面已落有半尺厚的纖塵不染的白雪了。這白,白過小麥面粉,白過白砂糖,白得直晃眼。院墻南面的柴火垛上,院中部雞籠頂端三四個花木已枯萎的盆子上,院北低矮的兩間廚房上,幾棵椿樹枝杈間吊著的沒剝苞皮的玉米上,成捆的紅薯秧上,一人多高的拐尺形墻頭上,無不被雪花簇擁覆蓋。站在院子里賞雪,我瞬間成了雪孩子。
走出用槐樹枝條編織的籬笆大門,眼前,是誰從銀白色的雪地上掃出了一條條靜謐的小路,通往牛棚、驢屋、井口、池塘,又連接到一家一戶的大門口。本以為我起了個大早,孰料更有早起人。他是勤快的丁姓大叔,還是喂牛的赤姓大伯……我一一猜想著,雖沒人告訴我是何人所為,但我知道,雪中的故鄉肯定記得。
那年月,村莊里數百戶人家的建筑,大多是低矮的草房,家境好一點兒的磚瓦房屈指可數。下雪了,除了村中的水井、喂牛的池塘,雪一落上去就融化得不見蹤影外,環繞村子的土大路、磨坊、羊圈、牛棚、驢屋、柴草垛等,全都頂著厚厚的松軟的白雪,身上仿佛披著既潔凈素淡又雍容華貴的盛裝。偶遇兩三條白色或黑白毛相間的土狗在雪地里追逐撒歡,犬吠聲很富于質感。雪不誤人,人不誤事。頭頂一藍底白花蠟染方巾,身穿碎花花紅布棉襖的村姑,胳膊挎一笆簍筐糧食,行走在彎彎曲曲的雪道上,到磨坊里去磨面。雪花追隨著她的碎步兒飛舞,她扭腰轉身送給雪花以歡笑和靚麗。老漢小心翼翼地從冬暖夏涼的水井口往上提水,站在滑溜溜的井臺條石上,用力搖動“吱嘎吱嘎”響的轆轤把柄。肩膀上擔著兩桶冒著“熱氣騰騰”的清水,舀半瓢喝下,溫溫的,頓有蕩氣回腸之感。這雪天仿佛不屬于寒冷,而屬于溫潤。抓一把雪面搓手搓臉,起先涼冰冰的,一眨眼周身便熱辣辣舒服極了。整個村莊端坐在澄澈通透的活潑潑的雪的世界里,一點兒都不感到寂寥單調。
村外,雪兀自飄落得紛紛揚揚,熱熱鬧鬧。天地皆白,銀裝素裹,一派妖嬈。無垠無痕的雪野,靜悄悄地消融了遠山起舞的綽影和遼遠空曠的地平線。天和地,相連相接,團抱成一個不容分開的整體。
雪天里,孩子們是閑不住的,他們有自己特有的樂趣。結伴在雪地里玩耍的群體中就有我。打雪仗堆雪人是不可或缺的游戲項目。好像不與雪親昵,就會愧對從天而降的圣潔似的,盡管一雙雙小手凍得像紅蘿卜。我們有時還將泥土大路上融化了的雪水又結成的薄冰踩得啪啪響。懸空的大小窩窩里的薄冰,踩出來的聲音是不一樣的,如同音符巧妙的組合,抑揚有序,張弛有度。瘋夠了,穿著濕漉漉的棉靴回家,免不了被手中線密密縫的母親呵斥一頓。自知理虧,剛一邁進門檻,便縮頭縮腦溜進里間。
做了“錯事”,也有彌補表現的機會。雪止了,碧空如洗,更顯清冷。喜鵲、麻雀等鳥兒,爭相從草垛間、屋檐下飛出來覓食,嘰嘰喳喳,招呼同伴。我們則學著大人的舉動,清掃院落里和臨近自家大路上的積雪。先將雪掃成堆,再用鐵锨拍牢,端到樹根周圍,讓樹木過足雪水癮,來年枝繁葉茂,果實累累。我家院中20多棵椿樹、棗樹、梨樹,每到雪天都會受到如此特殊待遇。剩下的雪,還要端到糞坑內,同土末子、草木灰等廢棄物混合漚成農家肥上地。村外鏟雪的人群中,時常有我們的身影。風勢作用,部分雪被刮到溜腰深的大路溝里。小小年紀的我們,扛著鐵锨跟隨大人一起勞作,將溝內積雪一锨锨甩到溝沿上方的麥田里,讓正做酣夢的麥苗多加一床雪被。我們之所以興致盎然,因那雪被下有我們望眼欲穿的顆粒飽滿的麥穗,隨風翻滾的麥浪,金黃燦然的麥囤……
夕陽西下,順著田間小路回家。當看到雪后初晴的村莊里,從高低錯落的煙囪中飄出的裊裊炊煙,向天空書寫著平安和睦時,心中頓生愜意。雪中的村莊傍晚,閃耀著賞心悅目的藝術光芒,神圣而美麗。(劉傳俊)









 中國舞劇《孔子》亮相莫斯科
中國舞劇《孔子》亮相莫斯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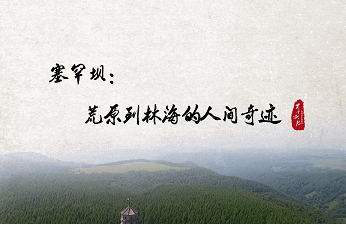 電影《那時風華》展現塞罕壩精神
電影《那時風華》展現塞罕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