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寫本書手及其書寫價值——以敦煌唐代寫本書跡為例
【讀史札記】
20世紀(jì)以來,敦煌寫本書跡打開了從普通書手角度考察唐代寫本的窗口,雖然創(chuàng)造這批寶藏的書寫者史籍無名,他們的作品卻是書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唐代作為我國書法史上的巔峰時期,亦是寫本史上的極盛時期,這些默默無聞的書手對唐代書法時代特征的形成起著推助作用,他們是唐代書法最普通的實踐者,也是唐代文化發(fā)展的有力參與者。
一
前輩學(xué)者對于唐代書手的身份、組織及書寫制度等問題已有深入探討,但在官府書手的職事、數(shù)量等具體問題上仍存在著分歧甚或訛誤之處。唐代敦煌寫本的書手構(gòu)成十分龐雜,大致分為官府書手和民間書手兩大類。需要強調(diào)的是,民間與官府的分類并不是絕對對立或有明確界限劃分的,而是隨著服務(wù)的場所和角色的轉(zhuǎn)變發(fā)生變化。
唐代官府書手設(shè)置比隋朝更加齊全,有“楷書”“楷書手”“御書手”“寫國史楷書”“群書手”“令史書手”“書直”等多種稱謂。門下省、中書省書手稱“楷書”時多從事公文的抄寫,而從事圖書經(jīng)籍抄寫的則稱為“群書手”。秘書省“楷書手”“楷書令史”則負(fù)責(zé)經(jīng)籍圖書的抄寫、校勘;著作局“楷書手”主要撰寫碑志、祭文、祝文等。而“能書”“書直”是其中比較特殊的一類。《唐六典·尚書吏部》載門下省設(shè)能書直,意在使國家大事記的制敕由書法優(yōu)秀的能書負(fù)責(zé)。另集賢殿書院有書直及寫御書一百人,書直由前資、常選、三衛(wèi)、散官以及五品以上子孫“各有年限,依資甄敘”充當(dāng)。《唐故汝州魯山縣丞司馬府君墓志銘并序》末題“文林郎前恒王府參軍直集賢院張文哲書”,張文哲以文林郎(散官從九品上)、前恒王府參軍的身份入職集賢院,與《唐六典》卷九所云“至(開元)十九年敕有官為直院也”正好吻合。
官府書手職事的明確和細(xì)化反映出唐代職官制度的完善。不同稱謂的書手所任職的機構(gòu)和職事各有差異,不能簡單以抄寫文書概言之,他們的工作還包括碑志、典籍、經(jīng)文的抄寫、校對等等,書手各司其職。獲得出身途徑后,才有做官的資格,在流外任職,屬流外行署,積勞累考后經(jīng)過由吏部等主持的銓選入流。唐后期,選官制度、文官結(jié)構(gòu)都有巨大變動,一方面流外入流呈現(xiàn)泛濫之勢;另一方面政府大量裁撤流外人員,這些變化對書手的入仕以及政治經(jīng)濟(jì)狀況具有重大影響。
二
傳統(tǒng)書法史的研究視角多聚焦于名家名作,對于普通書手雖有關(guān)注,但僅僅作為研究對象的附屬看待。從書手角度來看,寫本的實用性書寫體現(xiàn)了唐代書法傳播、消化、應(yīng)用的過程,普通的書手群體在促動書法變革的過程中,潛在地成為各種書風(fēng)的延續(xù)者、融合者和探索者。正如黃庭堅所評價的“觀唐人斷紙余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在歐、虞、褚、薛也”。時代風(fēng)格的形成顯然不是僅靠少數(shù)的書法家,無數(shù)不知名的書手在其中起著不容忽視的推介作用。此外,宋代以降直至晚清的千余年間,世人大都憑借碑帖、刻本推究唐代楷書的筆法,而豐富多彩的書手寫本墨跡,是銘刻楷書之外的另一種書法范式,更能體現(xiàn)唐代書法的特點,有利于全面了解唐代書法的真實狀況。
唐寫本書法與“二王”系統(tǒng)一脈相承,大都以虞世南、褚遂良以及顏真卿為范本,三家之中褚字的影響最廣最久。歐陽詢雖為“初唐四家”之一,但歐體風(fēng)格在官方寫經(jīng)里幾乎不見,反而多見于民間文學(xué)寫經(jīng)及其他實用文書中。上述書法面貌與當(dāng)時的政治背景和藝文風(fēng)尚密切相關(guān)。“南朝化”早已被視為唐代歷史演進(jìn)中普遍性的發(fā)展趨勢,可以說上至唐代帝王為代表的關(guān)隴貴族,下至普通書手的書法審美、書法實踐,以敦煌寫本為媒介全面展現(xiàn)了始于北朝并延續(xù)至隋唐的文化藝術(shù)領(lǐng)域內(nèi)的南朝化傾向。從規(guī)整純熟的經(jīng)籍抄寫到奇趣多樣的日常應(yīng)用,無不體現(xiàn)南北書風(fēng)的融合,這種融合是建立在以南朝書風(fēng)為主、以“二王”書法為宗的基礎(chǔ)之上,書法取法對象、范本選擇、書體應(yīng)用、風(fēng)格形成之于每個書手來說,都會折射出時代性的具體影響。
三
從字體的角度來看,唐代寫本字體粲然大備,包括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篆書在內(nèi)的所有形式,此外還有篆楷、隸楷、隸草等雜糅書體。寫本字體的選擇,因書寫功用、場合和服務(wù)對象的不同而有較為明顯的區(qū)別。譬如官寫本字體要求較為嚴(yán)格,文獻(xiàn)典籍、宗教經(jīng)文寫本作為“官樣”和“定版”,字體多以虞、褚風(fēng)貌的“官楷”為主;政府公文尤其是御制公文,則多以懷仁《集王圣教序》為范本的行楷字體為主。民間寫本在字體選擇上較為自由,佛經(jīng)寫本中供養(yǎng)經(jīng)以楷書居多,大量的日常用經(jīng)以及文學(xué)寫本、契卷、書信等字體多樣,行草書居多。
以楷書為例,唐楷的成熟除體現(xiàn)在史上熟知的大家巨匠名品以外,大量寫本墨跡尤其是官方寫本更能從細(xì)微處逐步體現(xiàn)出其發(fā)展脈絡(luò)。唐代書法承襲隋制,全面開啟南北融合之勢,唐代前期的官方楷書寫本較前朝寫本字形變扁為方,筆法由擺動向提按頓挫轉(zhuǎn)變得更加明顯,捺畫、勾畫由平出改為頓出。唐中后期寫本明顯字形方正且寬博、結(jié)體穩(wěn)定、筆畫的起收及轉(zhuǎn)折處隸意全無,加入較多修飾性動作,體現(xiàn)出成熟的楷書筆法。不同時期的書寫變化反映出楷書的基本面貌及其演進(jìn)大勢。一方面隋唐書家自身較前代更加注重對楷書結(jié)字規(guī)律的研究和總結(jié),從智果《心成頌》到傳為歐陽詢的《三十六法》將結(jié)字法進(jìn)行了分析并且歸類;另一方面唐政府加強了文字的整理規(guī)范,顏元孫《干祿字書》、張參《五經(jīng)文字》、唐玄度《新加九經(jīng)字樣》等以刊正經(jīng)籍、讎校楷書為目的,直接影響到書手的抄寫,因此唐后期寫本的俗字、異體字明顯少于唐前期。上述因素與唐代的書學(xué)銓選制度、書學(xué)教育等因素共同促進(jìn)了楷書筆法的規(guī)律化與法度化,推動唐代楷書成為書法史上難以逾越的巔峰。
四
時代的鑒定是寫本學(xué)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從書法角度開展的字體、書體、筆畫、結(jié)體等研究,亦為寫本的綴合提供了主要的判斷依據(jù)。唐代官寫本在某一階段內(nèi)的字體、用筆、結(jié)體以及審美趣味方面顯現(xiàn)出的共性,使書法的階段性特征比較凸顯;民間寫本在風(fēng)格的階段性方面則比官寫本更加自由和模糊。因此甄選不同時期、不同書體的官文書作為取樣標(biāo)準(zhǔn),挑選具有代表性的筆畫作為符號單元,按照時間先后進(jìn)行比對并建構(gòu)出一系列的模型,在此基礎(chǔ)上結(jié)合書法風(fēng)格、紙張、文本內(nèi)容等因素作為判斷時代的標(biāo)準(zhǔn)將更加合理和科學(xué)。如敦煌寫本《優(yōu)婆塞戒經(jīng)》北圖083號、斯4162號、斯4570號、法2276號四寫本,從紙張和書法風(fēng)格上看應(yīng)屬于同一種抄本。筆畫多為尖起重收,結(jié)體偏扁,呈現(xiàn)濃郁的隸意,皆非隋代寫經(jīng)書法,與寫經(jīng)題記所載仁壽四年(604年)的時間明顯不符。啟功先生鑒定為六朝寫本,應(yīng)為書寫者利用舊有寫經(jīng)的補經(jīng)修經(jīng)之作。經(jīng)過改裝而成以修補舊的寫經(jīng)來做功德,在敦煌唐寫本中非常盛行,這類寫本僅從題記來做判斷,難免失之偏頗,而通過書法的筆墨特征進(jìn)行校對比勘非常必要。再如對敦煌殘卷的綴合研究中,同一內(nèi)容的不同寫本,也會因受用人、書手等產(chǎn)生諸多差異。如唐寫本中由古人修補卷首經(jīng)文的《大般若經(jīng)》北敦6460號A、斯5334號A和北敦6777號A三紙,其中斯5334號A和北敦6777號A兩紙筆畫的“S”線條、橫畫末端收筆處的上翻上挑動作、結(jié)體的靈動之感基本一致,很可能為同一書手所寫,而北敦6460號A的書寫技藝和成熟度明顯劣于后兩者,結(jié)體略顯生硬拘謹(jǐn),橫畫仍然是尖起入筆,缺少變化,與前兩紙并非一人所書。以上通過具體的筆畫以及筆法特征的分析也是當(dāng)下進(jìn)行綴合研究需要考慮的因素。又如敦煌寫本較易出現(xiàn)經(jīng)文折損、缺落的現(xiàn)象,故官方和民間修補文書時或?qū)iT摹寫脫落或磨損的經(jīng)文,或割裂一批經(jīng)文進(jìn)行修補。要區(qū)分兩者,首先得依靠寫本文字相互間書風(fēng)和書跡的細(xì)致比對,然后從中厘選出相應(yīng)類型的文書進(jìn)行綴合,在津藝208號B和斯2257號B綴合時,應(yīng)先排除摹寫脫落或磨損經(jīng)文的可能,利用書法墨跡的精準(zhǔn)比較肯定二者最初出自同一個寫本。總之,對寫本的性質(zhì)面貌和制作書寫過程的相關(guān)問題給予書法角度的判斷梳理和解答,是寫本斷代以及具體的殘片綴合工作行之有效的方法。
綜上所述,敦煌唐代寫本書跡顯示出書手群體內(nèi)在的共通性、穩(wěn)定性和個體差異性,這些“原生態(tài)”的記錄抄寫以墨跡的形式較碑刻銘石更加直觀地反映出唐代書法的原生狀態(tài)和暗含的時代藝文脈絡(luò)。尋流溯源,思昔啟今,唐代書手研究亦可為當(dāng)下書法實踐、書法理論以及寫本學(xué)等相關(guān)研究提供有益啟示。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代實用書跡書寫群體研究”〔17BF117〕的階段性成果)
相關(guān)新聞
- 2020-01-07圖書館里“充電”忙
- 2020-01-06第十七屆中國文化產(chǎn)業(yè)新年論壇聚焦“大國文創(chuàng)與文化小康
- 2020-01-06親朋北京追思史鐵生:為人為文都是一面鏡子
- 2020-01-06《敦煌小畫師》入選中宣部2019年“優(yōu)秀兒童文學(xué)出版工程”優(yōu)秀作品









 中國舞劇《孔子》亮相莫斯科
中國舞劇《孔子》亮相莫斯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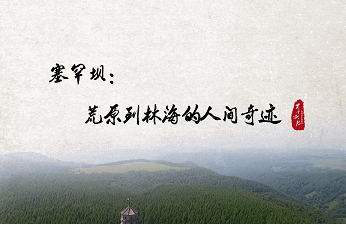 電影《那時風(fēng)華》展現(xiàn)塞罕壩精神
電影《那時風(fēng)華》展現(xiàn)塞罕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