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韻: 寫作本身就是對抗遺忘
□本報記者 郝天韻

一個黑羊皮筆記本失蹤40年后物歸原主,帶回了遲到40年的真相與原諒……《你好,安娜》是魯迅文學獎得主、著名作家蔣韻的最新作品,故事縱橫40年,以一段青春戀情、兩個少女的生命悲劇,探入3個家庭12位身份不同、靈魂各異的女性的沉浮命運。
“寫作最大的功能就是對抗遺忘。”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采訪時,蔣韻坦陳,《你好,安娜》的寫作初衷,源自母親患阿爾茨海默癥失去了記憶。母親的一生多難卻豐富,在人生接近終點的時候,疾病使她成了漆黑的、沒有記憶的人。在陪伴母親的日子里,蔣韻感受到,母親曾經多么努力地想打撈她的記憶,挽留它。“我從母親身上感受到一種對記憶逐漸流逝的緊迫感,可能對很多人來說,記憶其實會比生命先死亡,這個特別可怕。所以我要趁自己有記憶的時候,將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歷史烙印與人性最本真的東西寫出來。”蔣韻說。
在很多人眼里,蔣韻的小說辨識度很高。這種辨識度源自她作品中一以貫之的一個母題——罪與罰。這也源自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長篇小說《罪與罰》。憶及青春時代的經典讀物,蔣韻表示,俄蘇文學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影響無可取代,其中對她影響最深的便是《罪與罰》。“在我的那個年代,俄蘇文學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很多方面。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類苦難與絕境的刻畫、對人性深度的理解,都深深影響著我的文學創作,流淌在我每一部作品的血液之中,根深蒂固,無法取代。”蔣韻告訴記者,由此奠定了她一以貫之的寫作風格與敘事手法,《你好,安娜》也是以凌厲、觸人心底的筆鋒書寫了一個時代,以及時代中的人們如何面對他們的命運。故事含量、覆蓋面極大,對人性的挖掘極深,可以說,《你好,安娜》中每個人物都有一個自己的史詩。
關于蔣韻《你好,安娜》對時代的記錄與精神的書寫,著名文學評論家賀紹俊解讀道,20世紀5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即“50后”,那個時候人們主要是讀蘇聯和俄羅斯的文學作品,也有西方18、19世紀經典作品。這些經典文學對那一代人精神成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很多“50后”的人相對來說很天真,他們的心好像更加單純,甚至有時候不知道怎么應付當下的復雜現實,從這個角度來說,蔣韻的小說是非常有價值的,她提供了這樣一代人的人物形象圖譜。蔣韻關于“50后”的精神成長、精神境界的小說在當代文學當中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故事情節雖然是杜撰,但我把《你好,安娜》給很多我當年的朋友看,小說中極端的故事和結局雖然沒有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但他們都能或多或少地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蔣韻說。
“因為我寫的都是最本真的人,而不是神。”蔣韻表示,是人就會有弱點,《你好,安娜》告訴讀者的,就是直面這些人性的弱點,而不是逃避,這樣才能最終發自心底產生對善與美永恒的敬畏與追求,這也是蔣韻想表達的終極價值觀。
相較于大多作家,蔣韻比較低產,尤其近年來,父母、丈夫的生病,讓她忙碌奔波于各大醫院之間,一度讓她覺得和文學隔得很遠。然而在丈夫病情得到緩解之后,有了少許空閑時間,心緒也得到緩釋,蔣韻開始了《你好,安娜》的創作。寫作中,她感覺找回了自己最本真的樣子,用蔣韻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又成了我”。
在蔣韻看來,寫作帶給她極大的樂趣與力量,這部小說在蔣韻的創作生涯中也是為數不多的高產作品。寫作《你好,安娜》,僅用了3個多月的時間完成初稿,照顧病人和小外孫女之余,蔣韻每天上午抽出3個小時來專心寫作,那是她最快樂的時光,抽離于生活的瑣碎與忙碌之外,蔣韻在寫作時感到格外幸福和珍貴。
采訪最后,對于《你好,安娜》從構思到完成初稿,蔣韻也有個有趣的比喻,她認為創作是場“探險”,“我寫作從來不提前擬好提綱,因為在我看來,創作前心里有一個方向,沿著這個方向上路,路上遇到的一切人和事、一切驚喜和悲傷,都是‘探險’之旅,越走越奇妙,越走越精彩”。由此,一切的文思泉涌,都水到渠成。
相關新聞
- 2020-01-15劉海棲: 對青蔥歲月的趣味書寫
- 2020-01-15《中國歷代瓷器鑒定》新書發布
- 2020-01-15“南京現象”:讓文學深入城市生活
- 2020-01-14陳思思新作《思情話憶》在京首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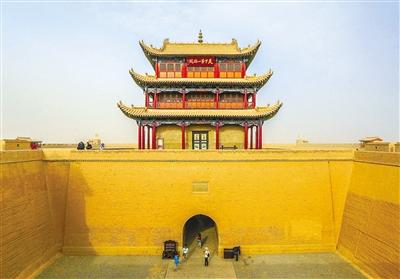





 2019年中國電影:如何把主流大片送達更多觀眾
2019年中國電影:如何把主流大片送達更多觀眾 《星球大戰》系列電影觀影馬拉松活動
《星球大戰》系列電影觀影馬拉松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