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一縷見史入心 ——在《文人相重》中找尋文學所的點滴過往
作者:張大明《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12日 16版)

何其芳(1912.2.5—1977.7.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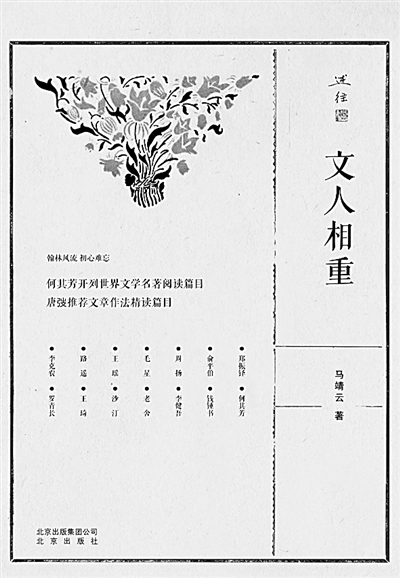
《文人相重》馬靖云 著 北京出版社
【述往】
對于享譽中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對于何其芳、俞平伯、錢鍾書等著名專家、學者,在過往的幾十年間,人們從文學的視角寫過不少文章,進行過許多研究,但是像《文人相重》的作者馬靖云這樣,以回憶錄的形式,從一個學術建構和科研管理者的層面,回憶文學研究所的歷史移位,以及在學人治學方面的親身經歷,非常難得。所以讀到《文人相重》一書,我既覺得獨特又感到親切。
本書作者馬靖云長期在何其芳身邊做秘書工作,除了完成科研管理的具體事務,還有送往迎來的外事活動。說得具體點,就是科研規劃、課題設置、外事交流、文獻整理、會議籌備等等一系列工作。但這些工作也使她見多識廣,她養成了重視觀察、重視歷史檔案,講究實事求是,少說話、多用心、善思維的工作習慣。這也決定了她的文章有親見感和紀實感,親聞性和在場性。《文人相重》沒有聲嘶力竭的叫喊,沒有耳提面命的說教,書中的語言娓娓道來,就像淡淡的一抹白云,輕輕的一縷清風,卻能沁人心脾,撼人心靈。這就是《文人相重》的魅力。應當說,作者馬靖云畫出了文學所這樣一個中國最高的文學研究機構的魂魄所在,一點一橫、一閃一耀貫注到書中的字里行間。這魂是什么?就是大家能夠各自按照國家需要,根據個人專長,確定研究課題,專心致志做學問,一做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畢其一生。在這里,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在漸漸地得以延續,學術的基業不斷地鑄造著輝煌。
人畢竟是決定成敗的主體,是統領千軍的關鍵。《文人相重》對整個文學所的書寫,還原了歷史,還原了生活,寫活了人物,突顯了精神。本書不是高頭典章,皇皇大論,而是娓娓道來,綿綿敘述,如爐邊絮語,路旁閑話,其中卻寄予著半個多世紀沉沉的思忖與深深的懷想。馬靖云寫文章很會剪裁,會運用手中的史料,心中的故事。點點滴滴,披沙瀝金。從題目上看,她的寫作是在懷人、憶舊。其實,書中還寫了一個國家頂級研究所的創立和發展,還原了這個中國現代“翰林院”的活生生的歷史。她不是為文學所寫史,也不是為所領導、專家學者寫傳,但若將其書寫的點滴匯總,全書體現了總體的宏放,更有生動的細節,文學所的總體風貌就在這兩極的呼應之中,浩浩乎文哉。
我嘆服作者通過在鄭振鐸、何其芳等人身邊工作,耳濡目染,言傳身教,并且通過大量檔案材料,感知、體驗這兩位所長的親力親為,了解他們為建構文學所這座學術的大廈所付出個人的歷史。他們把文學研究管理上升為一門科學,在科學的層面加以規范,提煉出管理學、研究學的宏大構想。本書作者用鮮活的材料,活靈活現地還原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所的籌建、創立以及發展過程。何其芳把研究所的管理作為一門學問,一種科學,常說“管理是需要鉆研的”。他和鄭振鐸在50年代初白手起家,建立文學研究所。把文學研究變為一種學科,一種事業。在人員調配、學科設置、課題落實、圖書征集和購置設備等等方面,篳路藍縷,辛勤耕耘,既是領導者,又是拓荒者,既是規劃者,又是踐行者。反觀歷史,何其芳的《論〈紅樓夢〉》《論阿Q》在學術史上固然了不起,可以劃出一個時代的學術標志,但在文學研究學科的建立和完善機制上,他的貢獻更值得大書特書。他們在前無古人的基地上,從奠基開始,顛顛簸簸,一路走來,最終建構成一座參天大廈。對這個歷史功績的銘記,我們終于在《文人相重》這本書中找到了共鳴。
一個最高學府所屬的科研單位,最要緊的是人才的調集和科研隊伍的建設。這是事業成功的基礎和起點。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組建到60年代文學所的第一次輝煌,鄭、何兩位創始人,能將國內文學(含外國文學)專家幾乎全部召集到旗下,實實在在是驚天動地的偉業,是創造歷史的大手筆。這一支隊伍在《文人相重》一書中多次出現。他們是鄭振鐸、何其芳、俞平伯、錢鍾書、孫楷第、王伯祥、余冠英、吳世昌、吳曉鈴、陳涌、蔡儀、唐弢、馮至、卞之琳、羅念生、羅大岡、李健吾、潘家洵、戈寶權、繆朗山、沙汀、陳荒煤、許覺民,以及由他們培養出來的一支中青年學者隊伍。文學所為這些專家、學者提供了縱橫馳騁的廣闊天地,反過來,兩代學人以其經典著述建構了文學所這座學術的殿堂。如果說本書有一種貫穿始終的人文觀念,那就是在一些看似軼聞瑣事與經典歷史的細節中,反映出了這種相得益彰的辯證關系。其中至關重要的是,在文學所里面人與人之間所建立的那種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相互砥礪的學者風范,也許就是本書所言說的文人相重吧。
本書的五大附件——鄭振鐸的《最后一次講話》、何其芳的《關于科研干部培養問題》,及何其芳開列的《世界文學名著閱讀篇目》、唐弢推薦的《文章做法精讀篇目》、文學所80年代初推薦的《文藝研究學習書目》,件件是硬通貨,無不具有真知灼見。尤其是三個書目,不是誰都開得出來的,沒有大學問大胸懷墊底,沒有理論的眼光,不能燭照探幽,沒有視野的宏闊,不能橫掃三軍,氣貫長虹。后生學者,照此閱讀,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就囊括于胸,清晰在握。20世紀60年代初,我還是在校大學生,見到何其芳開的書目,竟至驚得發呆!何其芳能夠開出那樣的書目,說明他有學識,有眼光。從行文中不難揣度,這個書目,馬靖云也讀過,至少是其中大部分。學海泛舟,近朱者赤。這使她的工作有深度、厚度、廣度,有思想,有美學成分。作者多次提到,何其芳對讀過的書,都有批注。如有好事之人將何注編為《何其芳批注集》,除了它本身的學術價值而外,更有啟發意義:可見詩人讀書之廣,之勤,之多。不停地讀,反復讀,讀名家名著,記下自己讀書的味道。這是求學之道,寫詩之本,是游弋學海,與前賢對話,與人類的智者交心。
本書涉及的學者、名流一大串,書的封面列有的與記述的包括鄭振鐸、何其芳、俞平伯、錢鍾書、周揚、李健吾、毛星、老舍、王瑤、沙汀、路遙、王琦、李克農、羅青長等,書中捎帶寫到的著名人物更多。回憶文章少不了的是細節,它們是不能刪夷的枝葉,是帶露折花的晶瑩剔透的珠子。如作者說何其芳“書”多,裝書有書架、書櫥、書柜之別,由何其芳的“書”,旁及孫楷第、王伯祥、俞平伯、唐弢、吳世昌、吳曉玲的藏書之差異,更及大學問家錢鍾書卻室內“無書”。在此,我首先佩服作者觀察之細,從這細分之中,真實反映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個人生活水平提高(變化)的歷史,兼及個人性格、興趣之迥然。全書雖未專門論述,僅偶有涉筆,卻盡顯情趣,且無不發人深思。
《文人相重》也有筆墨凝重之處,如《永不停止轉動的齒輪》一文寫何其芳做實事、重效率、忌空談。《荒煤重返文壇》一文寫陳荒煤筆墨瀟灑,一個曾經的副部長,而今指揮書籍的裝車、卸車,重顯當年本色。他力挺解放思想的新作,為一個時代的代表作及其作者唱贊歌。他筆立潮頭,保護新生力量,奮然前行。文字不多,但為時代留下了影像。他的《阿詩瑪,你在哪里?》,吶喊之聲,從云貴高原奪腔而起,回蕩太空,鑲嵌于歷史的天際。
就本書作者馬靖云的潛質和文筆來說,她不應該只提供136千字的《文人相重》就戛然而止,她還應該有續篇。而今,她雖然年過九旬,卻還思維敏捷,記憶鑿鑿,筆力遒勁。就文學所而言,依然以科研為視角,至少還有兩方面的人可書寫,而且有價值、有市場。一是從延安來的、從解放區來的老革命,如王平凡、唐棣華、朱寨、賈芝、力揚,他們或當領導,或為學者,稍加發掘,均可能得富礦;二是一大群中青年學者的涌現,如曹道衡、胡念貽、劉世德、陳毓羆、蔣和森、錢中文、樊駿、袁可嘉、陳冰夷、柳鳴九、陳燊、董衡巽,等等,無不學有專攻,有故事,記錄下來,就精彩,甚至就是詩。
(作者:張大明,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前主任,研究員)
相關新聞
- 2020-03-17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
- 2020-03-13對“京味兒”寫作的再詮釋——評《老舍評傳》
- 2020-03-13《寧靜無價》:寧靜是尋求自我本真的過程
- 2020-03-12《中國的紅星》:一部值得關注的紅色傳記






 《我不是購物狂》
《我不是購物狂》 2020埃及中國春節晚會在開羅舉行
2020埃及中國春節晚會在開羅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