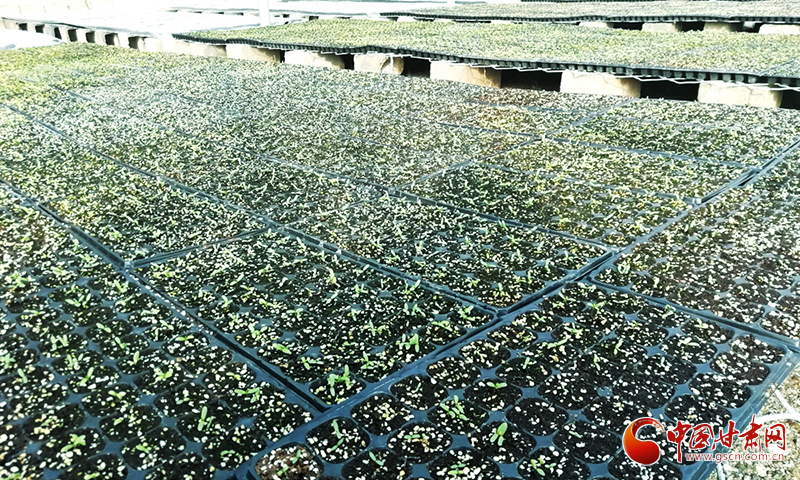中國近代文體嬗變
近代文體嬗變
文學文體也是有其“生命”的,總體看也在發展變化,需要不斷吐故納新、磨合再造。不過,文體發展會經歷不同的時期,有時以守成平穩為主,有時卻以創新求變為主。當歷史來到通常所說的“近代”,即鴉片戰爭(1840)至“五四”運動(1919)期間,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古今交合”并逐步走向“現代”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里,文學也和社會一樣發生了許多變化,文學思潮和文學創作都出現了新的動向,并且在文體的理論與實踐上體現了出來。
文體作為一種文化存在方式,是指一定的話語系統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是由敘述話語、結構模式、作品類型等因素構成的文學審美風范。文體不但是一種表現形式,而且是作家精神特性的表現。在文體理論層面,近代意義上的“文學革命論”非常引人注目,彰顯著近代文人對文體創新的強烈渴望與自覺追求。其中,緊扣詩歌、散文、小說和戲曲四大文體,近代文學先驅提出了著名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曲改良”等主張,切實推動了幾大文體的創新與嬗變,并呈現出較為鮮明的中介特征。
“詩界革命”的提倡,開啟了近代詩歌變革尤其是詩體變革的旅程。在這一詩歌改革思潮中,近代許多優秀的感時憂國的詩人都參與了“詩界革命”,并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黃遵憲在《雜感》(1868)中就提出了“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詩歌改革主張,并且在詩歌形式上進行了相當自覺的創作實踐。夏曾佑、譚嗣同和梁啟超等也積極跟進,在近代詩歌變革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善于思考和表達的梁啟超更是竭力推動,在《夏威夷游記》《飲冰室詩話》《亡友夏穗卿先生》等著述中,進一步提倡和彰顯著帶有理想色彩的“詩界革命”;不僅要創作“新詩”以開通民智,而且在嘗試近代詩歌文體探索方面也付出了很大努力。他主張詩歌要融入“新意境”“新語詞”,并化入“古人之風格”。其他詩人如丘逢甲、馬君武、蘇曼殊、寧調元等也聞風而動,以“詩界革新”的言說與實踐呼應著“詩界革命”。柳亞子、高旭、秋瑾與周實等也都努力嘗試新體詩歌創作,具體呈現彼時的新思想、新意境。但整體看來,近代詩歌在詩歌體式方面仍只是有限度的革新,筆者曾在《中國近代詩歌史論》(1995)中指出:近代詩歌多呈現“舊瓶裝新酒”的形態和體式,由此表明近代詩體的變革還只是過渡性的“中介”形式的,與“五四”時期白話詩、自由體詩相比還不夠“革命”,卻是后起的白話詩、自由體詩的先導與基礎。
“文界革命”的提倡主要來自于梁啟超。梁氏具有整體性質的文體革新意識,他在19世紀末就提出了一系列文體創新主張,其中就包括了他明確提出的“文界革命”主張。他認為,散文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都應該進行一次亙古未有的改革。認為新體散文創作應該沖決傳統古文諸多文法的桎梏,依循“文界革命”提出的理論進行廣泛的文體創新。他個人在改革散文的實踐方面也非常積極。眾所周知,梁啟超是近代非常重視媒體作用的文化名人,他的言論通過近代傳播媒介(主要是報刊)確實產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他的新文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適應報刊媒體的產物。他主張要積極借鑒“歐西文思”,會通古今中外,同時對散文的文體形式提出了更為前衛的主張。如在散文語言改革方面,竭力主張言文合一,倡導俗語文學,要求語言表達要通俗曉暢,這對后來白話文學熱潮的形成有著最為直接的影響。他自己在散文創作實踐上也努力踐行“文界革命”的主張,并形成了雄放雋快、激情洋溢、廣有影響的文風,被時人視為“新文體”的范文。梁啟超的新文體觀念與散文創作在近代散文發展轉型中無疑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有力促進了各體文章的寫作向現代散文創作的嬗變和轉型。
“小說界革命”的提出和實踐,在近現代文學史上特別引人注目,也最具有“革命”的意味。梁啟超在這方面也有倡導之功。他在《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等文中,相當充分地闡述了他的小說界革命觀。尤其是他在1902年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被學界普遍視為正式開啟“小說界革命”的標志性論文,對變革小說文體以及內容表達有著經典性的闡述。梁啟超在許多方面都是名副其實的“改良派”,但在小說理論表達上卻是相當徹底的革命者。在當時依然普遍輕視小說文體的時代語境中,是他竭力高抬小說這一傳統意義上的低賤文體,使之由“小說”變為“大說”,從而逐漸擺脫鄙俗乃至惡俗之弊,登上了大雅之堂,變為文壇令人矚目的文體,甚至被視為“文學之最上乘”。這種文體革命性的成果直到今天乃至很久以后的未來都會被珍視,并有無數小說作家積極地承傳和弘揚,創作了具有嶄新面貌的“新小說”。
“戲曲改良”在近代也浮出地表,并呈現出新的風貌。史料顯示,梁啟超在倡導“小說界革命”時業已兼顧了戲曲,認為小說戲曲的改良勢在必行,戲曲具有自己的特色和優越性。他在《劫灰夢》傳奇中說福祿特爾(即伏爾泰)編劇本以求振興民族精神,就借此闡明了戲曲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小說叢話》中則指出戲曲的“唱歌與科白相間”,可淋漓盡致地展示人物的性格與行動,通過各種戲曲表現方式包括“任意綴合諸調”亦可表達“自由之樂”。近代許多熱衷于“戲改”的倡導者們大都非常看重戲曲的教育功能,強調戲曲在啟蒙開智、興邦建國中可以發揮很大的社會影響作用。如梁啟超、陳去病、天修生、陳獨秀等都強調戲曲的社會功能,認為戲曲作為一種舞臺藝術,具有更加直觀的形象化的特點,有形有聲有色,“雖聾得見,雖盲可聞”,有現場感,能夠感染觀眾,故應大力提倡。陳獨秀在《論戲曲》中甚至空前強化了戲曲的宣傳功能,特別提出“采用西法”“戲中有演說”等觀點,雖然有倡導概念化之弊,客觀上卻也有推動戲曲變革,并進一步走向民眾的作用。
總體看,近代文學文體確實出現了比較全面的嬗變,四大文體都有一些“革命性”的變化,且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取得了可觀的進展;同時也都體現了承前啟后的中介特征,在文體的古今演變過程中發揮了“橋梁”作用。近代文體的“中介特征”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是歷史性的“承上”,即對古代文體自然而然的繼承,前述詩歌、散文、小說與戲曲四大文體都是依托既有的古代文體進行實質性改良的,根本做不到另起爐灶,這大概也是學術界習慣上仍將近代文學納入“古代文學”大格局的內在原因。其二是過渡性的“啟下”。近代文學發展包括文體嬗變的意義是指向現代的,具有指向當下、開啟未來的價值取向。有學者稱“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這話語既有思想史的“現代性”意義,其實也有文體史的“現代性”意義。比如詩歌的近代化,無論在內涵還是形式方面都帶有過渡性的特征,各種詩體有限度的嘗試包括口語化、新語句的采用,啟發了后來者可以進行更多的詩歌藝術探索。其三是與時俱進的“載道”。古代文學的“文以載道”作為一種強大的傳統或“文心文道”,到了近代也只是在體式上有所嬗變更新,在“載道”功能上依然受到重視,四大文體甚至被賦予更多的教育功能和社會使命。文體所載的“古道”可以被置換為“新道”,但仍是“舊瓶裝新酒”,新舊交合或雜糅的形態也別具魅力,也可以沁人心脾。其四是古今中外的“磨合”。文學發展和文體嬗變都與特定時代以及文化環境密切相關。中國近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被動性開放”,在中西文化沖突交融、古今文化嬗變會通的背景下,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遭遇促發了“文化磨合”現象,也助成了“文化磨合”思潮的潛滋暗長,對近代文體的創化產生了非常直接的影響。比如在散文、小說和戲曲的變革過程中,外國文藝的譯介和西方媒介(報刊)傳入的影響就極為明顯,在眾多文學文本中都可以“析出”古今中外的文化元素,都可以看到具有近代特征的“文化配方”以及具有磨合痕跡的文句和故事。
總之,中國近代文體畢竟發生了明顯變化,客觀上也推進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并開啟了中國文學進入“大現代”建構的旅程,而這個旅程最引人注目也最耐人尋味的則是近代文人上下求索的“文體革命”訴求和難能可貴的創作實踐。
(作者:李繼凱,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相關新聞
- 2020-03-23繁體字的文化承載不應被過度放大
- 2020-03-23感受戰疫中語言的力量
- 2020-03-20不直播的書店不是好書店?
- 2020-03-20彩色墨水屏閱讀器來了,黑白閱讀器就該換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