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與敦煌藝術(修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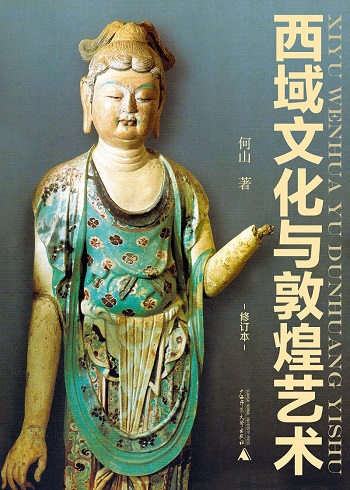
【基本信息】
書名:西域文化與敦煌藝術(修訂本)
著者:何山
書號:978-7-5598-2324-3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4月
定價:298.00元
【內容簡介】
本書從世界美術史的角度,從文化比較學、藝術哲學與美學的角度,對敦煌藝術的源流、題材、表現形式和風格等作了詳細的描述和論證;同時對敦煌藝術的分期、發展、演變,以及各時期的藝術風格與時代特征作了詳細的分析。書中附有大量的古希臘、古波斯、古印度藝術作品,以及敦煌各時期藝術的經典之作,供讀者參閱和比對,以期作出自己正確的思考與判斷。敦煌藝術通過絲綢之路使古代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文化藝術相碰撞、相交融、相汲取,凝結成人類文化藝術史上的璀璨明珠,產生了獨一無二的、綜合性的藝術群體和新型的文化藝術形態。
【作者簡介】
何山,1941年生,湖南湘陰人,著名書畫家。1964年畢業于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現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壁畫專業。同年就職于敦煌文物研究所,從事壁畫的臨摹、研究與創作工作。曾受教于龐薰琹、張仃、吳冠中諸先生,深受他們融古參今、博采眾長、轉益多思、構建新型文化形態的治學精神與美學思想的影響,對中國傳統藝術有深刻的理解,對西方藝術亦了然于心,強調藝術家的生命全在于作品。創作壁畫作品《黃河之水天上來》《楚魂》等;岀版著作《中國當代名家畫集——何山卷》《何山作品選集》《百體篆書千字文全解》《西域文化與敦煌藝術》等。
【精選書摘】
張錫坤序
時光荏苒,轉眼之間何山先生的《西域文化與敦煌藝術》出版至今已20年有余。不過令人欣喜的是,這部著作非但未因時間的推移而稍顯陳舊,展讀之下,反倒每覺滿眼生機。
何以這么說呢?
我們知道,自20世紀初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起,敦煌學即迅速成為世界顯學。千載寶藏的重見天日,著實令人目眩心動、意往神馳。1964年,大學甫一畢業的何先生,正是懷著無限的好奇與夢想,毅然決然地進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他畢業于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壁畫專業,專業本行自然是視覺藝術創作和風格學的研究。但敦煌學因牽涉到文獻、歷史、宗教、語言、地理、民族乃至交通、科技等學科紛繁的頭緒,因此關于其中的任何一項研究,若不甘心筑塔于沙,就必須從頭做起。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全球的敦煌學處在一個文獻整理和研究譯介的基礎性工作階段。學界從頭做起的“頭”,一般來說包括一遠一近的兩個。“遠”者為敦煌西域地區的古史地理及其演變,“近”者為藏經洞的發現和緊隨其后的西方探險家劫經、分藏與整理、著錄和研究的概況。直到今天,敦煌學的概述性著作仍采用這樣的背景敘事方式。我想在與諸多相關著述的比照下,來談談何先生研究路徑和方法的獨特性。
這種獨特性,首先表現在舍近求遠、直指本源的手段上。從上古以降西域的古史地理、人群活動、文物遺存及其精神氣質,來牽動北朝以來敦煌石窟藝術的解讀和辨認。就書名來看,論著的內容似乎分為“西域文化”和“敦煌藝術”兩個層次。而實際上,作者恰恰憑借自己的努力,避免了同類著作那種渙散鋪陳和隔靴搔癢式行文的無奈,而是以各種主旨性的意念,把這兩個時間段的問題,打造成一個“互文”的系統,形成一種相互介入、兩相輝映的論說脈絡。讓讀者感覺到,著者是就思考成熟的“問題”——亦即一個充分的理解前提——來組織材料和展開論說的。
例如,關于敦煌壁畫中的虎和鹿,學界或認為出自南印度的風格,或以為受到楚文化長沙馬王堆帛畫造型的影響。何先生則以早期西域烏孫、大月氏尤其是匈奴等游牧民族在西域的活動,再佐以內蒙古陰山、甘肅黑山、新疆天山南北大量動感十足、栩栩如生的巖壁動物畫,斷定這是卡拉蘇克文化藝術的典型,亦即敦煌本土的藝術風格和民族精神的表達。這樣的探求和釋說,避免了那種支離瑣碎、望影向壁的無稽之談,令人深信不疑。
再如何先生借助古史傳說和文獻,討論了關于中原和西域的交流以及河西走廊的開通問題。指出在張騫通西域之前,類似的活動既已出現了三次:一是大禹治水“至于西極”的傳說,二是周穆王西巡的記載,三是公元前6世紀左右由中原經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亞草原,南下伊朗、西去南俄商路的開通。如果再考慮到匈奴對西部游牧民族的早期統一,那么“就不能說張騫是‘鑿通’或開辟了中西要道,確切地說應該是將絲綢之道奪回到漢王朝的手中”。運用神話傳說來探索古史,徐旭生先生曾以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樹立了一個可貴的典范。而和徐氏相比,除了傳世文獻的運用,何先生更借助了考古發現的實物去印證傳說。例如沿途發掘出土的中國絲織品、玉、金、漆、青銅器皿,對古史傳說的印證,起到了無可置疑的支撐作用。
敦煌地屬古雍州,見載于《尚書·禹貢》。何山先生對其地歷史的探求,不僅借助古史傳說,還上推至史前的馬家窯文化,顯示出永不止步、永不滿足的追索精神。這種開闊的視野及其運用的有效性,不禁讓我想到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長時段的特殊價值”的思想。在布氏看來,傳統史學對短時段、個人和事件的關注,造成了一種“急匆匆、戲劇性的短促的敘述節奏”,從而忽略了“構成科學思想自由耕種的全部現實和全部耕種的歷史”,因而很難接近歷史的真實。在他看來,史學研究只有借助上升到闡釋層次的長時段概念,才能獲得與歷史曲線對應的“新的參考點來劃分和解釋歷史”,在這個意義上,“長時段似乎是導向普遍觀察和思考所有社會科學方法最有用的路線”。何山先生對包括莫高窟藝術時期整個西域文化的探討,都顯示了這種長時段的運用意識,克服了為數眾多的論者那急匆匆、戲劇性、近視病和淺嘗輒止式的討論。我想,這種史學研究中的宏觀視野的價值,并非他人所意識不到的,只不過更多的人在其史學研究中,缺乏那種對歷史的誠心和敬意,未肯盡心費力于此罷了。
《西域文化與敦煌藝術》的宏觀感,不僅表現在時間的維度上,更見于其空間上縱橫捭闔的魄力。從而構成了長時段與長距離三維交錯的意義系統。著者通過消解國內研究者普遍持有的中原文化和漢民族的本位觀,將視線聚焦于西域自身,以此為立足點,環顧希臘、印度和中國中原文化在這片土地上的往來匯聚與碰撞交融。在何先生筆下,西域這片亞洲腹地真正成為世界三大古老文明的輻湊中心和歐亞文化的樞紐所在。而敦煌之所以有幸接受三大文明浪潮的洗禮,除了地理位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其本土兼具了“混交型游牧文化”與“開放型商業文化”的精神氣質,這使其“行為動力”與“心理目標”一拍即合,勢所必然地成為華戎所交之一大都會。
在所有的論說中,作者時時不忘圍繞“商業”這一主題。不僅三代時期西域一直承擔著中西物產通流孔道的職責,匈奴民族的游牧活動在其間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而且希臘、羅馬的軍事東征與文化擴張,也本于其自身先天的商業精神。更為別致的是,何先生探討了印度佛教與商業的種種親和性,對教以商立、因商行教的歷史隱秘的發掘,直接指向了敦煌文化藝術之氣質與繁榮的最后根源。我相信,每位讀者都會被何先生那充滿睿識和魄力的材料組織和敘事策略所懾服,對那曾經輝煌而又業已消逝了的西域文明產生無限的想象和神往。
何山先生是以藝術創作為本業的,由此轉入到藝術史的探索。他能在西域文化研究領域做出這樣的成績,既實屬不易,又理所當然。所謂實屬不易,是就他廣泛大量地閱讀、消化和運用中西歷史、考古、民族、交通的學術材料,最終織構成一部綿密且闊大的學術著作而言。所謂理所當然,則是指他的藝術生涯為其學術研究貢獻出的那種與生俱來的想象力!
歷史研究是一項嚴肅的工作,要以嚴格的、經得起檢驗的史實材料來說話,這自不待言。但我更覺得,作為優秀的史家,尤為可貴的是他依據材料去闡釋歷史的想象力。前者為“史學”,后者為“史才”,二者兼具,才能促成真正的“史識”與“史德”。此中道理,正如劉述先所言:“歷史是要通過史家主觀的正確判斷,來重新建構出客觀歷史的真相。既要辛勤地發掘搜集資料,更要把這些資料貫穿起來繪成一幅歷史的圖像,乃是一項富有高度創造性的工作。”因為“歷史的事實和物理的事實不同,它是意義的單元,要通過解釋和再解釋的歷程,才能保持它的意義,當解釋停頓時,意義也就喪失,看不到它對歷史的重要性……再進一步,這些意義單元必須貫穿起來,才能夠給我們一幅比較完整的歷史圖像”。
在何先生這部皇皇巨著中,想象力的火花隨處可見。如他提出這樣一個很少為人所注意的問題:為什么在公元前7世紀至前4世紀,亦即古希臘藝術由古風期到全盛期這個時段里,人物雕塑的服裝,由質地較為粗糙、衣紋轉折單調平直,轉向了半透明質地且明暗變化日益豐富的表現手法?著者明確地回答道:“(一定是)中國透明或半透明的絲織、羅紗啟發了古希臘雕塑家和畫家的靈感,引起了希臘雕刻繪畫表現手法的變革。”此說可謂極為新穎大膽,而諦審其依據,卻毫不荒率突兀。因為早在公元前6世紀,中國的絲綢既已傳到西方并享有盛譽,不僅貴族婦女著以錦繡羅綺,甚至軍隊中亦將中國絲綢制為旌旗。“也正是這個時期,即古希臘藝術全盛時期的雕刻,它的服飾,特別是衣裙的質地,開始變得輕松、柔軟、貼身,呈透明或半透明狀態。對極善于表現人體美的希臘雕刻家而言,中國的絲綢質地,更有利于他們創作理想的發揮,從而創造出更真實、更含蓄、更抒情的藝術作品。”
此外,如何先生由辛店彩陶的器型及紋飾,推斷它或許是西域一支羌族部落的遺存,“羊角紋的普遍運用表明羊角紋有可能是羌人的族徽標記”。注意到西部半山型裝飾中靜態的方格和半靜態棱形,是早期敦煌壁畫中常用的基本紋樣;而馬家窯和半山彩陶運用的土紅和黑色,也是敦煌早期壁畫中常見的基本色……諸如此類聯想性論點的提出,既表現了作者獨立和富于個性化的思考,也予人以啟迪和想象力的再激發。何山先生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我相信俄國繪畫大師列賓的那句話:“靈感不過是頑強的勞動而獲得的獎賞。”
最后,還想說說該書表現出來的著者那精湛的語言教養。作為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西域文化與敦煌藝術》呈現出一種別有風味的敘事格調。筆墨時或洗練典雅,時或婉轉流宕;莊重而不失生趣,綿密且氣韻蓬松。很顯然,作為視覺藝術家的何山先生,同時對語言的色調和氣息有著一種敏銳的體驗。在宏闊的材料綜理和繁復的問題討論中,不僅無一費辭,且不落同時代文本語言那常見的忸怩空洞的俗套。表現出超拔出群、落落大方的氣度。尤其是他對三大文明藝術的描述和分析,能夠去蕪存真,直取要害,正所謂“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何山先生以他藝術家兼學者的優秀素養,以他的真情真性和真知真見,向學界奉獻出了這部可貴的讀物。
向何山先生致敬!
2010年9月18日
張錫坤,著名美學家,吉林省美學學會主席,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相關新聞
- 2020-04-13報章里的中國記憶
- 2020-04-13柳斌杰:英雄與時代同在
- 2020-04-09深入生命本真狀態
- 2020-04-09孤兒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