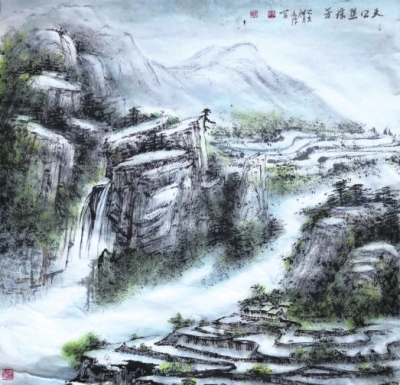書寫“中國式童年”,不能沒有面向世界的眼界

我曾數(shù)次深入農(nóng)家書屋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孩子們最愛讀的是《魯濱遜漂流記》和《平凡的世界》。《魯濱遜漂流記》是英國作家笛福寫于18世紀(jì)的小說,而《平凡的世界》并不是兒童文學(xué)。
這兩部作品緣何能夠跨越時空,打動當(dāng)下孩子的心靈?原因或許是,兩部作品都蘊含著不屈不撓的斗志和迎接生活磨礪的勇氣,這與鄉(xiāng)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兒童渴望走向大千世界、憧憬未來的內(nèi)心是一致的。這說明,經(jīng)典作品的穿透力、前瞻性和未來性,正來自于對人類共通情感的深刻洞察。
站在新世紀(jì)文學(xué)走過20年的時間節(jié)點上回顧,中國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xué)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面對那些感動孩子們的作品,我們是否還應(yīng)該追問一句:這些作品能否感動世界讀者、未來讀者和成年讀者?換句話說,能否深入表現(xiàn)具有普遍性的人類情感,既是檢驗兒童文學(xué)藝術(shù)水準(zhǔn)的有效標(biāo)準(zhǔn),同時也是兒童文學(xué)取得更高成就的有效路徑。
書寫“中國式童年”,不能沒有面向世界的眼界
“書寫‘中國式童年’”的創(chuàng)作主張,為新世紀(jì)中國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xué)提供了豐饒的精神資源,無數(shù)寫作者在中國童年經(jīng)驗的寶庫中勘探,獲得了取之不盡的寫作資源。也許沒有哪個時期能夠像新時代的兒童文學(xué)這樣在如此遼闊的疆域里馳騁:從西部到東部,從高原、沙漠到草原、大海,從鄉(xiāng)村到都市,不同民族不同生活環(huán)境的孩子們,他們的成長故事幾乎都納入了作家的視野,并被訴諸筆端。
時至今日,我們說“中國式”里要加入“世界性”視角,一方面是說立足中國經(jīng)驗的書寫,要有能力去燭照人類共同面對的精神難題;另一方面,作家也要有一種建立于廣博閱讀基礎(chǔ)之上的寬廣眼界,對世界范圍內(nèi)同類主題的杰作了然于心。比如關(guān)于“死亡”這個永恒的文學(xué)母題,在成人文學(xué)中也許不需要有太多禁忌,在兒童文學(xué)寫作中就必須有所寫有所不寫。如何取舍?難度系數(shù)比較高,但也有像《馬提與祖父》《天藍(lán)色的彼岸》等頗為暢銷的外國兒童文學(xué)可資借鑒。新近面世的《童心戰(zhàn)疫大眼睛暖心繪本系列》也在這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這套由張曉玲等年輕作家創(chuàng)作的作品,既勇于直面新冠肺炎給人類帶來的挑戰(zhàn),又能以兒童的視角切入,運用靈活多變的敘事策略,達到“向光成長”的藝術(shù)效果。這套繪本輸出多種外語版本,走向海外小讀者,顯示了中國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xué)與世界兒童文學(xué)接軌的巨大潛能和可能路徑。
立足“兒童本位”,不能沒有“整體性”視野
兒童觀的變革,讓新世紀(jì)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獲得了新的推動力。對“兒童本位”的推崇、對兒童主體性的肯定、對童年游戲精神的張揚,是新世紀(jì)中國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xué)有別于其他時期的特點。尤其是一些發(fā)行量巨大的校園兒童小說以及廣受青睞的作家童年回憶,卸掉說教重負(fù),輕裝上陣,頑皮、幽默、風(fēng)趣、輕松、甜美是這些作品的特點。它們得到讀者的熱烈呼應(yīng),反過來又強化了這一美學(xué)追求的牢固性,吸引更多寫作者追隨。
要讓這類創(chuàng)作走得更深更遠(yuǎn),必然要對“兒童性”進行更為深入透徹的勘探和思考,這就需要具備一定的“整體性”視野。其一,在理解和把握孩子精神世界的特點、刻畫兒童形象時,要避免片面。我們常說,孩子是天生的哲學(xué)家,當(dāng)我們強調(diào)“兒童性”的時候,并不是去簡化兒童精神世界的豐富性,僅僅將其中單純、快樂、無憂無慮的一面展現(xiàn)出來,而忽略成長中遇到的困難、困惑、困境。其二,兒童不是孤立的,他們是在與家庭、社會、成人世界的密切互動中成長起來的。除了孩子間的溝通交流,兒童有沒有能力感知來自社會的更為豐富的信息?答案是肯定的。孩子身上折射著斑斕的時代光影,他們也有能力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感受生活的風(fēng)雨。這一點在《淘氣包埃米爾》《小淘氣尼古拉》以及《城南舊事》《窗邊的小豆豆》等經(jīng)典作品中都可以充分感受到。
強調(diào)“整體性”視野并不是說把成人的思考方式強加于兒童,讓兒童文學(xué)走向“成人化”。始終以兒童的眼睛看世界,是兒童文學(xué)作品最牢靠的立足點。強調(diào)“整體性”視野的目的,意在引發(fā)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的思考:如何處理兒童文學(xué)與時代重大命題間的關(guān)系?
找到重大事件和兒童個體成長之間的契合點,是寫好這類作品的關(guān)鍵。裘山山的《雪山上的達娃》以一只小狗的視角來寫青藏高原雪山哨所士兵們的生活,增強了故事的趣味性,也拉近了孩子們與遙遠(yuǎn)軍旅生活的距離。美國作家勞雷爾·布雷特茲-勞格斯蒂的《寄往月球的信》中,小女孩選擇給登月宇航員柯林斯而不是萬眾矚目的阿姆斯特朗寫信,因為她感受到了前者的“孤獨”。正是這種人類普遍的情感,把登月這個重大事件和一個小女孩的現(xiàn)實生活和內(nèi)心世界奇妙地聯(lián)系在一起。除了紀(jì)實性的正面強攻,兒童文學(xué)介入重大現(xiàn)實題材的角度是多樣的,尋找情感共鳴就是方法之一。
根植當(dāng)下現(xiàn)實,不能沒有凝視未來的目光
當(dāng)下的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現(xiàn)實題材數(shù)量最為龐大。兒童文學(xué)寫作者在現(xiàn)實題材創(chuàng)作上精耕細(xì)作,不斷攀登藝術(shù)高峰的同時,也應(yīng)面向未來敞開無限可能。我們既期待著像《小靈通漫游未來》這樣家喻戶曉的少兒科幻作品的涌現(xiàn),同時也要看到,一些并非是科幻小說的外國兒童文學(xué),也包含了相當(dāng)多的科學(xué)內(nèi)容,甚至可以說是成長文學(xué)與科普作品的跨界融合。這種兼容多種創(chuàng)作元素的寫作,在本土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xué)中還不多見。
對人類未來生存方式的想象,尤其是對科技、生態(tài)等對人類命運產(chǎn)生根本性影響的重大主題的展望,兒童文學(xué)都不應(yīng)該缺席。科技日新月異的發(fā)展已經(jīng)滲透到人類的日常生活,孩子們當(dāng)然也不例外。科技和兒童的精神成長是一種什么關(guān)系?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的興起,又會對孩子們的未來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這些都可以成為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關(guān)注的對象。把科學(xué)溶入文本之中,不但是對文學(xué)的知識傳統(tǒng)的繼承,呼應(yīng)了人類面對未知世界時的普遍的好奇心、求知欲,也緣于人類情感的律動,都不可能離開科技的滲透與投射。
在科技之外,人類與大自然、與野生動物的關(guān)系等,也是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無法回避的命題。可喜的是,我們的兒童文學(xué)作家已經(jīng)在這方面開始默默思考。黑鶴的《馴鹿六季》就是把一個男孩子成長的關(guān)鍵時刻置放在鄂溫克人生活的大興安嶺深山密林中,通過顯微鏡般的文字細(xì)致精確地呈現(xiàn)人的情感成長和大自然的關(guān)系。這些探索也許因為樣本不夠多,還構(gòu)不成一種文學(xué)現(xiàn)象,卻也為兒童文學(xué)如何深入地發(fā)掘人類的普遍情感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文/李東華 作者為魯迅文學(xué)院副院長)
相關(guān)新聞
- 2020-07-14文藝創(chuàng)作要有文化傳統(tǒng)“打底子”
- 2020-07-08多一個“埃德加·斯諾” 少一分隔膜與猜測
- 2020-07-08坐讀與走讀
- 2020-07-08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乘風(fēng)破浪正當(dāng)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