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謙:陽光照在群山上
作者:閆磊《光明日報》( 2019年08月09日 13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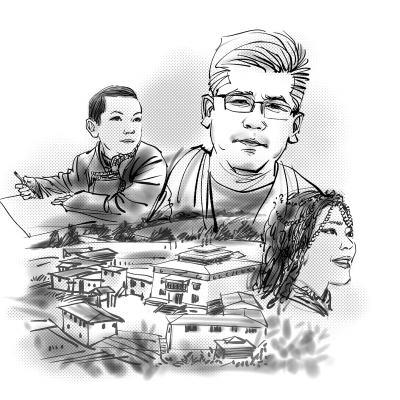
插圖:郭紅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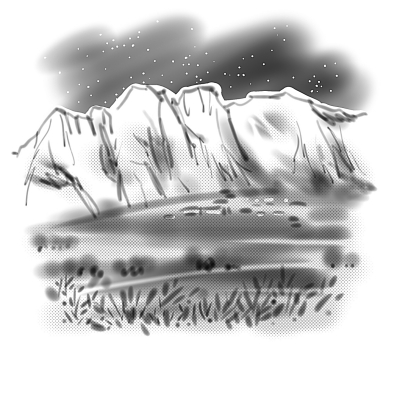
插圖:郭紅松
一
抵達玉樹巴塘機場時,下著細雨。目光所及,灰色和棕紅色巖體間雜著薄薄的綠色植被,形成交錯、連綿的一道道山脈,呈舒緩的環抱之勢。一條柏油公路穿越其間。透過群山的一處空隙,隱約看見一座云層和白雪覆蓋的山峰,薄暮般懸浮在天際,轉瞬又縹緲不知所終。我隨單位工作組鉆進一輛面包車,向玉樹藏族自治州下轄的囊謙縣行進。
“現在從玉樹這邊坐車,兩個半小時就到了,”單位常駐青海的萬瑪加老師笑道,“以前我跑趟囊謙可難了,得從西寧坐車,一坐十幾個小時,一路翻山越嶺,幾乎不見人煙。”
萬瑪加是藏族人,面龐黝黑而飽滿,在一頭白發的映襯下,透出一股高原的純凈和活力。他說,這條路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沿“唐蕃古道”興建的,與后來沿“茶馬古道”興建的滇藏公路連接,定名“214國道”,近年又進行了升級改造。
經過一個埡口,路牌上寫著“尕拉尕埡口,海拔4493米”。近旁山坡上,遍布一堆堆涂著顏色、寫有字符的石頭,還有一條條連結成塔形、迎風舞動的五彩經幡。萬瑪加說,埡口是山頂或山與山的連接處,翻越了埡口,就意味著翻過了一座山。在藏民心中,每個埡口都是神圣之地,會在此放置瑪尼石、瑪尼旗,用來感恩、祈福。
我們繼續前行,在高海拔地帶的微微眩暈中,經過了甲黑Y合、4118米,尕日拉、4324米,然代拉、4322米,俄亞拉、4499米,謝尕拉、4496米等另5個埡口,那些一閃而過的金屬路牌,與車窗外緩緩蠕動的群山、河流,黑色的牦牛,車窗上時疏時密的雨水,車內發動機的轟鳴,交織成一條通往囊謙的時空管道。
二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單位與囊謙建立了定點扶貧關系。2015年初,我從同事口中得知單位派蔣新軍同志前往囊謙掛職多昌村第一書記。此后,我對囊謙迅速熟悉起來:我遇見過許多次囊謙來的干部和孩子們——很容易從單位的人群中認出他們經高原光線和塵土浸染的紫褐色臉龐;參加幾乎動員了單位全體職工的“一對一”幫扶囊謙貧困學生活動;持續關注著單位選派扶貧干部、派出工作組的消息,直到此次我也成為工作組的一員。
然而,只有當我到達海拔3660米的囊謙縣城,住進縣委招待所,注視房間里經幡式花紋裝飾,并連上WIFI、發送地圖定位,才真正感受到置身其中——這片位于青藏高原東部、面積12741平方公里、人口12萬、遍布山川寺院的藏區土地。
接下來的兩天,我隨工作組到縣委縣政府各部門交換工作意見、進村入戶走訪。
在縣政府大樓,胡副縣長帶我們順路參觀了他推動單位出資援建的縣檔案室。“囊謙目前累計識別建檔立卡貧困人口35000多人,全縣每3人中就有1人。要實現絕對貧困人口‘清零’目標,首先要對建檔立卡數據重新核查、逐條整理、實時更新,檔案管理任務繁瑣艱巨,”他一邊演示檔案柜的自動開啟、歸位操作,一邊說,“不打無準備之仗,咱們能幫著升級一下裝備也好……”空降兵出身、有會計專長的小胡是單位2016年派來繼續掛職的,當時小蔣掛職一年期滿。從小胡開始,掛職期延長為兩到三年。
查閱多昌村貧困戶資料卡,我們選定達吉等3個家庭作為入戶走訪對象。每家的資料卡上都貼著一張合成“全家福”——把每個家庭成員照片PS在一起的合照。
曾拍攝并發表眾多囊謙人物和風景照片的小蔣,回單位后卻不無遺憾地寫到,自己原想掛職期間為村里每一戶家庭都拍一張全家福,可是邊走邊拍下來,人總湊不齊,總有人在外學習、打工、奔波,幾乎沒拍到一張完整的全家福,有的甚至拍成了個人照。對于合成全家福照片,他感慨,我們有意無意忽視了其中原本蘊含的情感力量。
三
香達鎮的多昌村座落在扎曲河邊,與縣城隔水相望。柏油公路沿河蜿蜒向前,穿過一片片青稞地,穿過整個村莊。
村口附近坐落一大一小兩座房屋。一座是高大的藏式平頂白色四方形建筑,里面人頭攢動,像是座大禮堂。另一座是普通平房,位于大禮堂側前方,像是一間隨意搭建的“門房”。
村第一書記小蘇帶我們進“門房”參觀,這是一個約100平米大小、綠色墻灰已有些剝落的房間。空軍轉業、懂信息技術的小蘇是單位去年增派來掛職的,他說,要把這個屋子用起來,打造成多昌村的電商物流中心。
村民房屋沿公路一側松散分布,有的院墻幾乎被路邊的雜草掩蓋,路面不時出現大大小小的水坑。“要想富,先修路,”小蘇說,“之前咱們討論的,就是村里這段路,看怎么能修一下。大家多出出主意……”
達吉家的房屋像是臨時搭建的工棚,塑料板拼接成墻壁,塑料袋遮擋著窗洞,屋子中間的火爐占據了一半空間,幾乎無處落腳。女主人達吉和母親手忙腳亂地從兩面墻邊的雜物中各收拾出了一塊平板。我們把一早從縣城買的米、面和油放在墻根,擠著在平板上坐下,達吉和母親也在另一塊平板上坐下。她們穿著黑色藏袍、系著五彩的頭繩和腰帶,顯得沉靜、素雅。
從資料卡知道,她們家里共5口人,有3個孩子,養著10頭牦牛。
“孩子們都上學去了?”
她們笑著點了點頭。
“她們家有個孩子可出息了,”小蘇站在一旁說,“考取了北京的‘玉樹班’,去北京上高中了。”
聽姥姥繼續說了會兒什么,我們起身往阿增家走。
“聽說高原冬天特別冷,這房子怎么住啊。”我一邊走,一邊又扭頭看了一眼窗洞上的塑料袋。“出過一個政策,給貧困戶解決住房問題,政府出大頭,貧困戶出一部分。達吉家可能實在缺錢,聽說是悄悄把蓋房指標賣給親戚了,從登記看,已經享受過政策了。天冷確實有困難的話,只能想其他辦法,幫著多籌集一些御寒衣物吧……”小蘇說,“她們家缺壯勞力,基本沒有收入來源……”
我們沿扎曲河往前走著。河床很寬闊,河岸與水流中間隔著大片的沙灘、草地,牛、羊、馬散布其間,兩三只兀鷲在空中盤旋。路邊半人高的草叢中,幾只黑色牦牛夢游一般蠕動著。
“對了,不是養著10頭牛嗎?”
“這些年一些村探索精準幫扶新路,”小胡接過話頭,“想各種方法籌資給能養牛、愿養牛的村民買牛,先給搬遷戶、無畜戶、婦幼戶,產出歸自己,解決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度,但不能直接賣牛。這個辦法在牧區效果很好,在城鄉結合部存在較多不確定因素。”
“等那個孩子從北京讀書讀出來,”小蘇忽然感慨,“達吉家應該就算真脫貧了。”
阿增家有10口人,包括1名僧侶,1名智障兒,養了15頭牦牛。去年,在政策支持下,他家在原有的一間低矮土屋邊新蓋了一間高大的磚房。我們走進這間寬敞明亮、彌漫著酥油氣味的新屋,和在家照顧孩子的兩位老人聊了會兒,接著去冷周家也坐了坐,回到車上,繼續前行。
公路一邊的景觀從民居變成陡峭的崖壁,另一邊,河水和淺灘不斷分叉,十數條支流并行,逐漸形成了一片壯闊的網狀水系。在扎曲和孜曲交匯處,公路跨越河面,逐漸繞回縣城方向。
“這塊風景怎么樣?”小蘇說著,把車停在山腰一處平緩地帶,“按照文化活縣、旅游富民思路,我們將把這條路線打造成‘精品鄉村一日游環線’。等人氣起來,形成規模效益,周邊服務,包括電商、物流,就都跟著起來了,到時候,這里就是天然一塊絕佳的觀景休閑平臺……”
一輛車在不遠處停下。我們碰見了剛從外地開會回來的縣紀委書記、著曉鄉扶貧攻堅協調指揮員巴桑。
聽說我們剛從村民家過來,巴桑談到自己帶隊走訪著曉鄉6個村的經驗。他說,現在每個干部都有走村入戶任務,首先就是要幫村民懂得,也是幫干部自己懂得,幸福不是“等、靠、要”來的,而是奮斗出來的,不是某個人、少數人奮斗出來的,而是大家一起“闖、改、創”,共同奮斗出來的。巴桑穿一身灰色西服,說到高興時會很自然地用臉貼一下你的臉,很有親和力。
說著又下起細雨。渾黃的河水與草場、山脈、細雨、天空層疊交錯,綿延鋪陳出一幅宏闊悠遠的山水畫卷,多昌村民居點染其間,輕盈美麗。
四
白扎鄉的巴麥村位于巴曲下游,距縣城70多公里,與西藏隔山相望。單位在那里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學。學校依山而建,山頂坐落著藏傳佛教千年古寺——尕爾寺。
第四天早晨,前往巴麥村。
到達寺院建基的山巖腳下時,那里已形成一條轉山的人流。村民們拖家帶口,有的抱著嬰幼兒,沿樹林巖土間踩出的一條陡峭、潮濕的山北小徑,轉到東邊一間禪房門前,匯入一支等著拜見活佛的長隊。繼續往前轉,是深紅色外墻、五彩鑲邊的大殿;大殿中央供奉著一對“加那瑪”轉經輪,意為“漢地來的寶物”,相傳是文成公主進藏的嫁妝,幾經輾轉到此,由僧侶晝夜24小時不停轉動,為眾生祈福。
“尕爾寺是藏傳佛教最大的一座噶舉派寺院,”萬瑪加、小胡和小蘇告訴我們,“囊謙現有寺院100多座,僧侶1萬多名,每10人就有一個僧侶,堪稱藏傳佛寺僧侶密度最高的縣。”
我們登上禪房旁邊一幢兩層白色方形建筑的頂層平臺,平臺向南正對盤山公路環繞的一片盆地,其間坐落數十座排列整齊的新建盒子屋,以及巴麥村希望小學——三棟有著亮藍色斜屋頂的兩層樓房,與三棟兩層平頂樓房,圍出一個水泥操場。
利用去希望小學發放助學物資的間隙,我們去盤山公路旁的曲吉家走訪。前些年單位一位老同志認領了曲吉家兩個失學孩子作為幫扶對象,此后常托工作組給孩子捎帶些東西,探望老人。
孩子爸媽一早外出放牛,在家的只有爺爺、奶奶和姑奶奶3位老人。或許是寺院下區,屋里除了日常家具,還沿墻擺放了一圈長條形玻璃門木柜,裝滿了一摞摞像是經卷的書冊。旁邊的墻上貼著幾張學生獎狀;柜子外面還掛著孩子從學校帶回來的黑白招貼畫:一朵花、一點燭火,配著“信心”“愛”“夢想”等詞語……
告別時,爺爺要我們等會兒,示意家人取出了幾條金黃色、五彩絲線刺繡的哈達,蹣跚著走到我們面前,為每個人掛在脖子上。
五
在巴麥村希望小學,我們與孩子們聊天,聽孩子們講上學、放牧的經歷;一起唱歌;欣賞孩子們的繪畫作品:格桑花、五彩馬、獼猴、雪豹……14歲的索南靦腆而開心地告訴我們“我喜歡上學”。她干活麻利,父母就把她留在家中放牧,讓其他4個孩子上學;現在,入學一個月,過去不會說漢語的她,能用漢語流利地數到100。
聽教職工們說,學校三分之一的學生都是失學、輟學勸返的,“許多孩子承擔了太多與年齡不符的責任和壓力”。近年通過一家一戶排查、勸學,縣里5000多名未上學的孩子基本全部入學;500多名中途輟學的孩子也全部勸返。
到達位于香達鎮移民新區的第二完全小學時,天已完全放晴。陽光灼人,校園中央新建的標準400米塑膠跑道運動場紅綠分明、鮮艷奪目。北邊,矗立著藏式平頂四層主教學樓。主教學樓門廳陳列著學校50多位老師的照片和簡歷,一半以上都是囊謙自己出的本科畢業生。
會議室里,副縣長美少正與3名學生談心:“今天送你們一人一雙新鞋,希望你們從此走新路。”其中兩名學生來自縣第一民族中學,已逃學10多天,校長專程趕來將他們領走。大家談到,要通過教育改變思想觀念、“拔掉窮根”,就“一個都不能少”。現在開展的“一對一”幫扶效果很好,“但能惠及的還只是少數優秀孩子”。
課外活動時間,一位穿絳紅色藏袍、結盤頭長辮的年長者帶著一群同樣裝扮的孩子,在主樓前練習“卓根瑪”舞蹈及“牛角胡”樂器;一群穿運動服的孩子在操場上踢球;還有許多孩子三五成群地歡笑打鬧。
我想起有一年在單位食堂,看到一群穿運動服的囊謙孩子合唱的情景。此刻,這個情景,忽然異常生動地重新浮現在我的眼前,我甚至感覺到了孩子們心跳加快的聲音、調整呼吸的聲音,和我自己同樣的心跳、呼吸的聲音。我又想起漫山遍野的五彩經幡、永不停止的轉經輪、曲吉家手捧哈達的老人、達吉家綻出笑容的母親、資料卡上的全家福……
陽光逐漸變成柔和的橙黃色,操場上映照出越來越長的山的影子。靜默的群山,一重一重由近及遠淡化為云層堆積的雪峰,融入天際。
回京前的晚上,整理工作材料間隙,我對著中國地圖,在囊謙和玉樹、西寧、北京之間連線,反復觀看、確認著囊謙的位置,試著以此加深、確認囊謙與自己的聯系。我仿佛感到,這個隱于祖國大陸西南腹地的秘境,就像是隱于肝臟之中的膽囊,讓我們不時牽掛著。
六
前往玉樹巴塘機場的路上,司機小伙兒扎西說,“你們一定要再來囊謙,會有不一樣的美。你們要夏天再來,參加賽馬節,這里是玉樹小江南;冬天也要來,感受原汁原味的雪域高原;要從然察大峽谷去達那寺,看格薩爾王及其三十大將軍靈塔;要到海拔5000米以上,去宗果寺;晴朗的晚上,要記得仰頭看看囊謙的銀河繁星……”
過了尕拉尕埡口,不多久,就望見了巴塘機場,仿佛一片純凈的天空,平穩地懸浮在山脈草甸起伏的綠色波浪之間,在陽光照射下,明晃晃的,泛著夢的光輝。
(作者:閆磊,系本報紀檢監察室副主任)
相關新聞
- 2020-08-11經典詩歌 雙語誦讀|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 2020-08-11白雨白
- 2020-08-11土豆的日子
- 2020-08-11家在白云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