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八怪題畫詩考釋》:達人隨性好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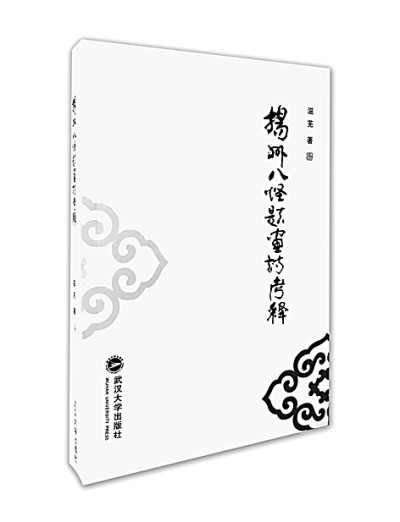
《揚州八怪題畫詩考釋》 滋 蕪 著 武漢大學出版社
“達人”一詞,在中國最早見于春秋《左傳》,載:“圣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后必有達人”。唐代詩人全德輿在《廣陵詩》中云:“……曲士守文墨,達人隨性情”。歷史上首次將藝人稱為“達人”,似預示千年后揚州由“八怪”發動繪畫變革緣于人的性情。回望歷史,“揚州八怪”就是應時而生的畫壇達人。
五代出現荊浩、關仝、董源、巨然等山水畫巨匠,后人按活動地域將荊、關視為北方畫派,董、巨為南方畫派,雙峰并峙,燭古耀今。評論家對明初戴進為首的畫家以作品、履歷認證品級,分類注疏,品鑒定性,達成按地域分類有美學意涵的畫派共識。“浙派”稱謂正式出現著錄中,中國的“畫派”由此濫觴。清代無“揚州畫派”一說,時人都稱其“怪”,贊譽者寥寥而蜚語者眾……
“揚州八怪”幸逢貿易通衢之利,商業活力的刺激使得畫家們生活得益,書畫風雅得到商賈附會,他們沉醉主流畫壇不屑的表現題材和創作手法。然而,就是這些人怪畫奇的旁門左道,卻與世俗藝術消費者和諧“共在”。“八怪”的審美理念并非主動接續歷史,而是以即興式的變法、任性般的創新而異軍突起,掀起清中期畫壇變革的巨浪,其圖式新穎、花樣頻出、風格鮮明而影響深遠,被后人貼上“八怪”標簽定格在中國繪畫史中。《美術教育研究》雜志社社長滋蕪,對語言修辭敏感,涉獵考據學,熟悉小學訓詁,了解通假字,具有較高的文字把控能力,加上幾十年浸染瀚墨,諳熟題畫詩講究意理共生、圖文相參之道,這從其出版《揚州八怪題畫詩考釋》一書就能得到驗證。
滋蕪確定“八怪”成員時有意回避“揚州畫派”提法,認定“十四人說”,而不采用包括閔貞在內較通行的“十五人說”,筆者對此并不認同。想必是他遵從歷史記載(因閔貞無行跡揚州的文本載錄),堅持以史為基的學術態度和明確考釋的嚴謹性、闡述的學理性、解讀的情境性思路。題畫詩這種由漢民族文化孕育的文人畫符號形態,自元代初成詩、書、畫、印體例,經明人深入打磨,圖像發散的詩情,蓄涵意象氣場,彌漫由看到讀、由讀到觀、由觀生意、由意至覺的遞進過程,達到精神感知與視覺觀瞻交互融合。康乾之際,“揚州八怪”繪畫經環境催化,形成變異的文人畫體。獨特、巧妙的畫風經300余年沉淀,今天觀之,依然可感畫家與時俱化的創作沖動、隨機應變的筆墨理念。“八怪”從選擇內容、章法布局、筆墨路徑的“出格”行為,快心遂意的筆墨驅弛,形成清代畫壇一道詼奇怪異的景觀。編撰“揚州八怪”題畫詩,要在收集大量資料基礎上,釋讀連通儒、道、釋、禪,注文須涉及畫作的物態呈現,感悟款題由表意引出內隱性與外顯性、自足性和多義性復合意念。因為古代題畫詩不僅是當時書面文獻語言,也是和歷時久遠的繪畫文本合體。歲月輪回,許多語意已然發生變化。如文與言、史與今的諸多表述,須借助訓詁加以詮釋。滋蕪力證部分模糊詞義清晰化,助力讀者對照畫面感知畫家寄寓的思想。題畫詩的學術依據,溯源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等滋生的詩文傳統,考釋需以訓詁眼光審慎辨別史料,避免以訛傳訛。要明白各代不同的民俗風情,對“揚州八怪”題畫詩考釋,更要通曉明清漢滿不同民族文字的變異,而非一張畫上題款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及長短句詩風問題,考釋如斷句錯,字義就錯,字義錯意思就含混不清。在后明前清滿人沒有被漢化之前,許多通假、避諱等相互糾纏。如果理義不通,就會謬之千里。以本人對西安美院古代藏畫考釋、研究的體會,認為題畫詩考釋有三難:一是賦之志讀,二是詩之意讀,三是圖之觀讀。三者相互參證,方能準確理解“揚州八怪”題畫詩的圖義。
滋蕪系統性考釋“揚州八怪”題畫詩,校勘規矩繩墨、研究鍥而不舍,耗費十年心血,竭盡心力克服上述三難。這部思維開放、邏輯嚴密,對“八怪”詩作梳理清晰,釋文斷句準確,語義闡述含情入理,符合彼時文化氛圍,充分展示滋蕪與古人對話、與大師交流過程中顯示的著文功力,可感他不凡的審美眼光,體現了作者整理傳統國粹的擔當。這部包含“工具書”信息容量的考釋集,為今人研究“揚州畫派”風云開闔的歷史畫卷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應一平)
相關新聞
- 2020-08-17《牽風記》的文學史意義
- 2020-08-17農民,永遠值得喜愛和尊敬
- 2020-08-17對時代的關切與思考
- 2020-08-14《口述王繼才》在南京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