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安到日本:都城空間與文學考古》:文學考古如何見證長安歷史

東征傳繪卷。選自1988年日本中央公論社《日本的繪卷·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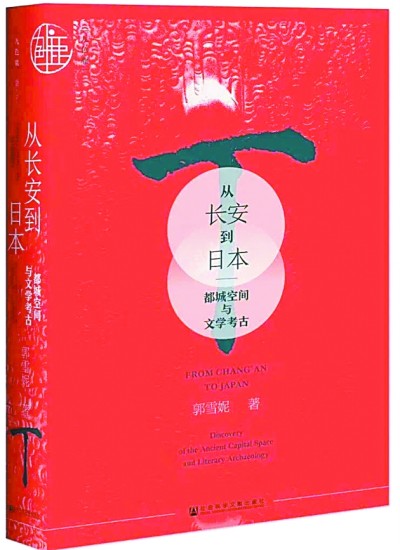
《從長安到日本》 郭雪妮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唐招提寺瓦當。資料圖片
拜占庭、阿拉伯、粟特文獻中稱呼大唐都城長安為“胡姆丹”(Khumdan),這可能是這座享譽歐亞的帝國之都獨特地位的一種表現。而且,長安實際上也是世界帝國大唐王朝的縮影和象征。現代研究者借助多元的歷史典籍、考古資料、出土文獻而融會貫通,試圖復原長安的歷史全貌,不斷推動方興未艾的“長安學”研究。然而,近年來另外一種聚焦于長安意象的“文學考古”異軍突起,長安學由此或將挺進更為廣闊和縱深的地帶。
郭雪妮新著《從長安到日本:都城空間與文學考古》,關注長安都市景觀在日本古代“漢”“和”文獻中的演變,跳脫了長安本身而突進到域外文本對于現實長安的書寫,別開生面,應該說是長安文學考古的嚆矢。全書的核心議題,即對在唐朝滅亡以前和以后日本建設國家的不同階段,日本文學文本中亦真亦幻的“真實長安”和“意象長安”進行了絕妙的對比,并將之落實到“東亞都城時代”長安都城真實空間在日本的復刻、變異和折射這一歷史背景中深入理解。
具體而言,這部作品的前三章雖然瞄準了三種“漢”文獻,但是其折射的歷史內容卻存在流變:《懷風藻》中長安的缺席,映射出建立律令制國家的日本難以將作為八世紀唐朝“國家權力和皇帝威嚴的王權之都”的長安作為歌頌對象;“敕撰三集”(《凌云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基本無涉于唐長安城,而僅以漢長安隱秘現身數次,暗含著日本文人面對強勢的唐帝國時“脆弱民族國家的話語表達”;《本朝無題詩》則大量出現指涉長安的詩作,但這些無一實指,而是以“長安”來寫現實中的平安京,并利用兩座都城名稱的重合,植入中國典故,將日本都城平安京描述為囊括唐帝國西京長安、東都洛陽的巨大存在。
后四章多元化地引入幾種“和”文獻虛構文學作品,竭力尋覓長安意象的變遷以及客觀歷史投射其上的另一種真實。圓仁的旅行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包含著從開成五年(840)到會昌五年(845)他在長安生活的四年十個月的記錄,盡管日記文本在后半段的唐武宗滅佛期間表現出與僧人整部日記大相徑庭的情緒化描寫及“不可靠”敘事,但對歷史親歷者(圓仁)而言仍是力求秉筆直書并自信為真的文本,然而后來的《今昔物語集》等說話類虛構作品卻逐漸放大、扭曲法難期間“圓仁”遭受迫害的情節,制造以“絞纈城”為重心的恐怖長安景象。院政時期“詞書”與“繪畫”交叉結合的《吉備大臣入唐繪卷》,兼具圖像和文學史料,描述了遣唐使吉備真備在長安應對唐人難題考驗的冒險傳說,長安的海岸風光、唐人的滑稽描摹等不實內容映射了日本平安末期對長安的基本知識和想象。平安末至鐮倉初的《弘法大師行狀繪》以空海生平為題材,其入唐部分的描畫將唐長安城中的青龍寺作為惠果傳授密教于空海的象征而被日本真言宗神圣化,而與真實的青龍寺相去甚遠。鐮倉初年遣唐使物語的集大成之作《松浦宮物語》,既混合了仙界等非人間的浪漫唐土烏托邦,又以漢長安的用語細致描寫唐都長安的宮殿、關隘、城市、郊外,其間的想象基礎多來自白居易的詩文和《文選》,而非正統的地志文獻。顯然,花非花,霧非霧,“和”文獻中的長安絕非唐長安的寫真,而是文學想象、歷史意識和現實感懷的雜糅造作。
其中的知識密度、探索深度、視野廣度顯而易見。關鍵是,唐都長安作為城市客觀實在本身,已然不再是研究對象,研究對象已轉變為日本人從奈良、平安時代至鐮倉初期在詩歌和說話、繪卷、物語等文本中對于長安的“忽視”或者“想象”——其間,真實的長安城在十世紀初隨著帝國覆滅而遭致毀壞和廢棄。由此,這一研究仿若是在日本人的真實長安之旅以及長安夢境囈語之間,尋覓長安的影蹤,這令人聯想到諾蘭的經典影片《盜夢空間》中“夢中夢”的多層穿越。
歷史學者圍繞著隋唐長安展開的多學科的研究,或可籠統稱之為“長安學”(雖然未必所有學者都認同此概念)。如果以其涵蓋的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地理學、宗教學以及藝術等多方面內容為“中心”領域,恐怕作為域外思想史、文學史的長安書寫無論如何都只能算“邊緣”領域。然而,誠如妹尾達彥所說,學術本身沒有“中心”或“邊緣”之分,很多學術突破恰好發生在學科交界的邊緣,因為那里“本就不是邊緣,而是被忽略的地方”(序二)。日本文人長安意象的文學考古實際上裹挾著以上以歷史為主的諸多學科的成果,反過來對認知歷史提供廣闊的縱深空間。
作為歷史學者,我更加關心的問題是在這些層層考釋的更深處,在圍繞著長安意象的“文學考古”整個過程中作者不斷強調的預設前提,即東亞所共同享有的華夷思想在都城建設和國家觀念上的投射。如何理解這一見解?
十世紀唐帝國崩潰以及東亞社會全局性的連鎖性質變作為一個分水嶺,使得全書呈現出一種上半部是擁有長安旅行經歷的遣唐使和求法僧筆端語涉長安或者絕口不提長安,下半部是無緣再前往中國的日本文人通過文學想象對于長安多種形式的異化和虛擬。在這種虛實相生、真假莫辨的強烈反差中,揭開層層包裹和修飾而袒露其本體,整個“文學考古”的過程輾轉騰挪曲折繁復,卻不失福柯知識考古學的魅力,真實歷史被懸置,“權力”在追尋中浮出水面——這個權力關乎日本律令制國家和民族國家的建設及其對唐朝中心的國際秩序的態度。
長安被書寫或被遺忘是歷史表象,它其實反映的是日本的文人在華夷思想和律令體制的多重影響下,“在現實政治運作中模仿中國,卻又在精神世界試圖對抗的矛盾心理”(序二)。唐朝的華夷秩序之下,日本等周邊政體都被納入朝貢—冊封體制,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世界格局,其典型是白江之后唐、新羅、日本摶成的國際結構,學者稱之為“東亞世界”。在中國強盛時期,日本文人刻意不去書寫長安即唐朝象征,也就意味著深層意識中不想流露出本國的屈尊地位,在唐帝國瓦解之后,日本文人或以輝煌長安的意象喻指平安京,或虛構唐都長安的恐怖夢魘,或建構日本宗教與唐朝源頭的紐帶等,則是日本民族意識高揚的時代之聲。其中,平安京融唐朝京、都為一體的理念,實際上是東亞漢字文化圈文化共享的一個典型案例,而共享得以實現是基于存異而非求同(拙作《唐朝與東亞》)。長安作為文本的線索,首先反照出日本奈良時代(710—794)、平安時代(794—1185)及鐮倉時代(1185—1333)初期的中國觀,進而折射出來自中國的“中華思想”的強力輻射。
對于日本漢文學最早的作家群遣唐使而言,長安城以及平安京固然是作為物理可感知的第一空間,而同時遣唐使群體詩文制造的“長安意象”,又是隱喻的第二空間。第二空間本質上講與第一空間越來越疏離乃至抵牾,甚至使得長安由陸地城市變成海岸城市,這就是我所說的“夢境囈語”。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第二空間的虛無荒誕,卻是囈語者其來有自的親身經歷和切膚真實——譬如,圓仁將會昌年間的道聽途說煞有介事寫入行記,我們絲毫不懷疑絕大多數情況下他自己堅信這些記載,而后世在將他神圣化的過程中,以文學虛構進一步把他在法難中罹受屈辱、迫害、苦難之地長安夸大扭曲成如地獄一般的時候,正是日本“佛法東漸”思想和與優位意識熾盛的時期。再如,繪卷中的吉備真備戰勝唐人的層層阻礙,憑借的不是真實的才華智慧,而是欺騙、盜聽、偷棋等不光彩手段,這些狡黠的智慧在作者看來是平安末期貴族文人對唐弱者意識的結果,潛藏著“一種頑強的抵抗感”。
總之,日本國家的律令制國家建設、唐風文化向國風文化的轉換、東亞局勢和本國內政的變動、日本民族意識的抬頭,這些歷史的真實無不經由作者在數量浩繁、種類多樣的文本中批揀出來的“長安書寫”(刻意不寫也是一種書寫,正如遺忘也是一種記憶)而映射顯現。統領全書的序章或因此而題為《在日本發現長安》,似與書名《從長安到日本》桴鼓相應。然而,通覽全書內蘊豐贍的知識與思想史呈現,我倒是更愿意凸顯研究者在這種探索中的主體地位和能動作用,而謂之《在日本尋覓長安》。至于其追尋的文本在生成之初是否即為長安而作,探尋所得結果是否為互文共生的文本叢的透徹解讀,抑或在尋找過程是否全面關照日本文人的中國地理知識接受史,似乎已不是癥結所在。在中國與域外往復交流的宏大背景中,苦苦的摸索和反復的尋覓,過程本身足以動人,加之其間歷史景觀不停變換,沿途滿是可堪吟味之處,讀者自可逐一賞析。諸君何不立即與作者一道,一日看盡長安花?(作者:馮立君,系陜西師范大學東亞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教授)
相關新聞
- 2020-10-12讀馮驥才《文雄畫杰》:別樣風情 亦文亦畫
- 2020-10-12“北京作家日”助力文學作品走出去
- 2020-10-12諾獎新貴,再次上海出版:世紀文景為何要引入冷門作家
- 2020-10-12“不服老”作家劉心武的敘事探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