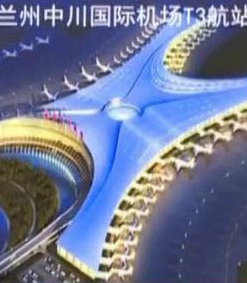詩歌,從“個人”連通時代與世界
作者:馮圓芳
2020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詩人露易絲·格麗克,如蝴蝶扇動翅膀,隨之掀起的讀詩熱潮再次印證了“詩歌從未遠離”的事實。什么決定了一首好詩?在全球疫情造就的人類文明“至暗時刻”,詩歌肩負著怎樣的時代使命?近年來中國詩壇又發生了哪些“變”與“不變”?10月11日、12日,第三屆揚子江詩會·大家講壇和“新世紀20年中國詩歌創作”研討會分別在南京、徐州舉行,詩壇名家、期刊主編、專家學者齊聚江蘇,在一個富有節點意義的歷史時刻里,重新審視詩歌這一古老而新鮮的文體。
新媒體、新技術重塑詩歌生態
“那時的春天稠密,難以攪動,野油菜花,翻山越嶺/蜜蜂嗡嗡的甜,掛在明亮的視覺里……”詩人陳先發的《最后一課》,備受南開大學教授羅振亞的推崇,“這首詩敘述一位老師穿過田埂為生病女孩補課的敬業故事,詩中有‘他’打電話、夾雨傘的動作描寫,有‘他’認 真整潔、儒雅莊重的性格刻畫,顯示了詩人介入日常生活的能力之強。”這首樸素的詩,折射了中國詩歌近年來的變化:詩人由主要依托流派、社團轉向“個人化寫作”,從加入“大合唱”轉為立足個體生命經驗,以獨特的聲音、語感和風格來展示和世界的關系。
如果硬要用一個詞概括近年來的中國詩歌創作,那么一定是“多元”。“每個詩人都八仙過海各施絕技,除了‘寫什么’,也關注‘怎么寫’。”羅振亞說,“語詞運動、仿寫、反諷、戲劇性、敘事、互文、文體互滲等‘花招’百出,呈現出同一時代背景下每個抒情主體的獨特風貌。”
當下的詩歌生態也發生了鮮明的變化。“我水銀一樣純凈的愛人,今夜我馬放南山”“陌生的姑娘,我愛你”……紀錄片《我的詩篇》,“捧紅”陳年喜、鄔霞等“打工詩人”,讓他們進入大眾視野;葉嘉瑩文學電影《掬水月在手》未播先火,同樣以“變”的形式見證著人們不變的詩心。南開大學副教授盧楨認為,新媒體、新技術正深刻改變著包括創作、傳播、消費在內的詩歌全鏈條生態:“以博客、微博、微信、豆瓣為發表陣地,線上蓬勃生長的自媒體詩人大量涌現,刮來詩壇新風;詩歌與其他媒介進行實驗性整合,黑大春的‘歌詩小組’把詩歌說唱與小提琴、搖滾樂雜糅,詩與樂相得益彰;微軟小冰、小封機器人的AI詩歌引發關于文學本質的思索;詩歌營銷推廣風氣日盛,‘為你讀詩’App、線下云上全面開花的詩歌朗誦會、詩電影等均提高了詩歌的曝光度和影響力。”
喧嘩中審視詩歌“初心”
《全唐詩》不過五萬余首,目前中國每天的詩歌產量已經超過了這個數字;詩歌網站注冊人數逾千萬,民間詩歌刊物達1100多種,名目繁多的詩歌評獎頻頻引人矚目……這意味著詩壇變得更加“繁榮”了嗎?曾連續五年擔任柔剛詩歌獎評委的南京大學教授傅元峰慨嘆,活躍的詩歌評獎客觀上催生了不少“競賽體”詩歌,它們往往包含著媚俗的修辭姿態、討巧的技術取悅。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則發現,富有創造性的詩歌常常無法在評獎中取得共識;相反,“平庸”一些的作品反倒可能獲得更多評委青睞。
抽象的“集體”逐漸隱居幕后,生動的“個體”走向舞臺中央,這是幾十年來中國詩歌的鮮明轉向。“但詩歌是個人的,也是社會和歷史的,個人化寫作只有傳遞具體的歷史情境和人類生活的普遍焦慮,才能夠引發共鳴。”羅振亞說。而放眼當下,一些詩人正無限度地張揚個體,讓自我情感經驗膨脹漫游,回避社會良心、人類理想,詩歌應有的“詩魂”被抽空殆盡。
仰望星空,詩歌要做時代的“精神高標”;棲身大地,詩歌也要察世情、觀人心。《詩歌月刊》主編李云注意到,一些詩人回應新鮮現實的能力嚴重滯后,“表現新時代鄉村時運用的意象還停留在老井、炊煙、耕牛層面,傳遞的畫面仿佛改革開放初期的鄉村,寫作手法也停留在艾青、臧克家式的表達方式上,他們筆下的詩歌與我們生活的現場之間嚴重斷裂。”或者,詩人雖然記錄下某種現實的斷面,卻無法傳遞出時代的普遍經驗,在何平看來,這是詩人的能力不足造成的,他們缺少一種對素材進行體驗、想象、審美鍛造和思想綜合的本領。
當下,眼花繚亂的詩歌營銷傳播態勢或許值得警惕。當雜糅著搖滾音樂、炫酷燈光和奇幻舞臺的“詩歌表演”引人趨之若鶩,當一首戲仿詩歌文體、充滿解構與嘲弄的“偽詩”在眼球經濟左右下形成傳播奇觀,當一場聲勢浩大的“丟書大作戰”、大V加持的詩歌沙龍收割可觀流量,人們須明白,這些現象也許擴大了詩歌的影響力,本質上卻很可能無關乎詩。盧楨提醒,“剪貼文化”“快餐文化”固然帶來了娛樂快感,卻也使詩歌特有的凝練與哲思日漸式微,“這個時候不妨問問:詩歌的初心又在哪里?”
擔起引領人類精神的使命
“當東方和西方再一次相遇在命運的出口/是走出絕境?還是自我毀滅?/左手對右手的責怪,并不能/制造出一艘新的挪亞方舟,逃離這千年的困境……”疫情期間,著名詩人、中國作協副主席吉狄馬加所作的一首長詩《裂開的星球》,立足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激烈博弈的世界局勢,呼吁捍衛自由、公平和正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他看來,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最艱難的時刻,詩人和詩歌更應該承擔起引領人類精神的崇高使命,保持傾聽,打破壁壘。
放眼國內,今年恰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吉狄馬加認為,詩歌作為詩人個體發出的聲音,應該永遠是個人性的;但是一個置身于時代并敢于搏擊生活激流的詩人,又不能不關注民族和同胞的命運,“我很喜歡的一位愛爾蘭詩人,他的詩歌書寫了很多瑣碎生活、田間植物,仿佛田野里反光的玻璃碎片,折射出特定自然歷史環境所養育的一個民族的精神史詩。因此,從詩人的個體聲音背后,我們應該聽到的是群體和聲、人類意識的回響。”
不過,詩歌與生活、時代、歷史之間并非簡單的鏡像關系,而應是一種多角度的思索與探尋。河南大學教授耿占春說,和青春熱烈的何其芳相比,他更欣賞詩人穆旦后期創作里的那種豐厚,里面包蘊著更復雜的歷史洞見,有美學的光芒,也有生活的智慧。譬如一句“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交織著生而為人的艱辛,至今仍喚起共鳴。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敬文東說,“詩歌要和新聞競賽,就必須寫出這種唯有詩歌才能表達的東西”。
詩人的“見證”使命也包含著時代問題的審視、對現實弊疾的反思。“我把車子開上高速公路,就是開始了一場對蝴蝶的屠殺/或者蝴蝶看到我高速駛來,就決定發動一場自殺飛行……”在《當代國際詩壇》主編唐曉渡看來,詩人西川的《撞死在擋風玻璃上的蝴蝶》,以精準的意象、高度凝練的現代情境,指出了人類文明進程對其他物種、生態環境造成的碾壓性侵害,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重溫這首詩,仍然能帶給讀者震撼和啟示——這便是好的詩歌在審美愉悅之外的又一種力量。(馮圓芳)
相關新聞
- 2020-10-14珍珠湖邊
- 2020-10-14在謎語的故鄉,夜夜望星辰
- 2020-10-14茶香書香
- 2020-10-14不能釋懷的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