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塑造故鄉(xiāng)的“語(yǔ)法空間” ——訪詩(shī)人扎西才讓
用文字塑造故鄉(xiāng)的“語(yǔ)法空間”
——訪詩(shī)人扎西才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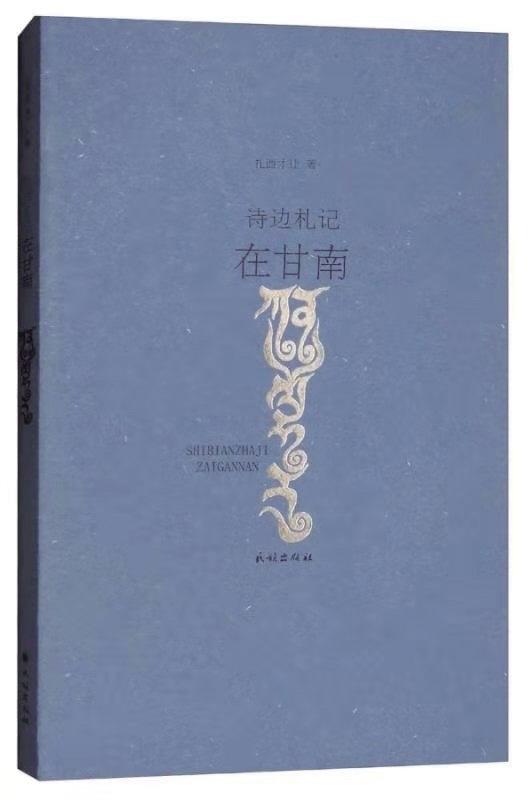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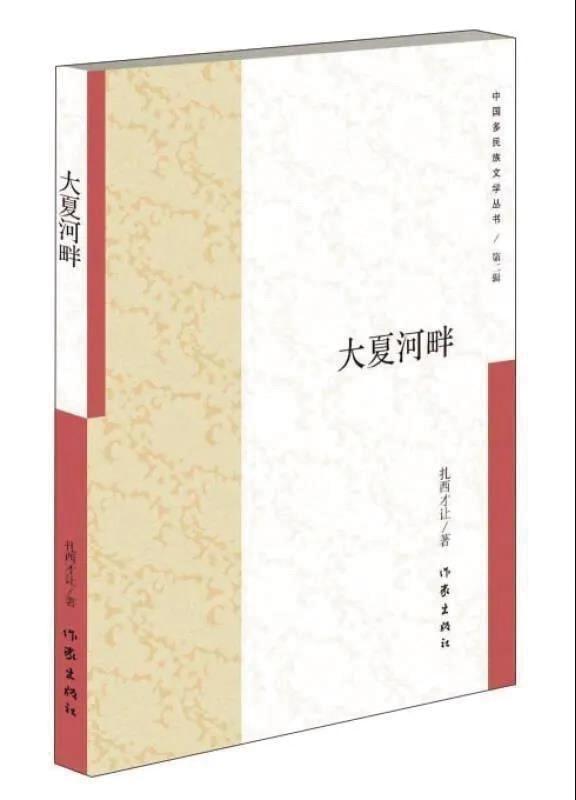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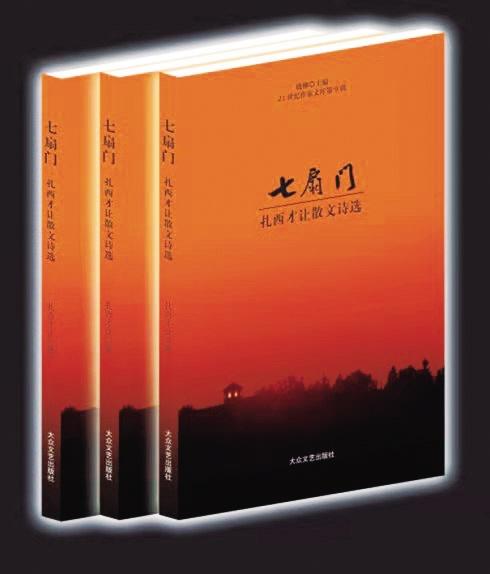

扎西才讓
藏族作家,甘肅甘南人,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作品曾被《新華文摘》《小說(shuō)選刊》《中華文學(xué)選刊》《散文選刊》《詩(shī)收獲》等轉(zhuǎn)載并入選多部年度作品選本。作品獲敦煌文藝獎(jiǎng)、黃河文學(xué)獎(jiǎng)、海子詩(shī)歌獎(jiǎng)、三毛散文獎(jiǎng)、梁斌小說(shuō)獎(jiǎng)、全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駿馬獎(jiǎng)等獎(jiǎng)項(xiàng)。著有詩(shī)集《大夏河畔》《當(dāng)愛(ài)情化為星辰》《桑多鎮(zhèn)》,散文集《詩(shī)邊札記:在甘南》,中短篇小說(shuō)集《桑多鎮(zhèn)故事集》。2017年,被甘肅省委組織部、宣傳部、省文聯(lián)授予“第四屆甘肅省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榮譽(yù)稱號(hào),先后兩次入選甘肅詩(shī)歌八駿,2019年又進(jìn)入“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之星”,以基層作協(xié)會(huì)員代表身份參加了第六屆全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會(huì)議。
“若我像螻蟻生活于草底,將能目睹圣僧的袈裟也遮不住的日出;若我睡在地底下,也能在漸漸喧囂起來(lái)的世界里,聆聽(tīng)到大地的清吟……”
這首《草原清晨》來(lái)自我省詩(shī)歌八駿之一——扎西才讓。他的詩(shī)集《桑多鎮(zhèn)》于今年8月榮獲了第十二屆全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駿馬獎(jiǎng)。
也許有的讀者有所不知,全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駿馬獎(jiǎng)”是與包括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和全國(guó)優(yōu)秀兒童文學(xué)獎(jiǎng)在內(nèi)的我國(guó)具有最高榮譽(yù)的四大文學(xué)獎(jiǎng)。近日,記者采訪了藏族詩(shī)人扎西才讓,來(lái)自甘南的他骨血里帶著藏族的浪漫與豪放,黝黑的臉上印著高原烈日親吻的痕跡,而陽(yáng)光般的笑容仿佛帶著熾熱的光芒,逼退了一切陰霾。
據(jù)扎西才讓介紹,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一個(gè)叫羚城的小城有關(guān),羚城意思是羚羊出沒(méi)的地方。羚城雖然聽(tīng)起來(lái)陌生,其實(shí)就是甘肅省的合作市。“羚城的原居民是本土藏人,后遷來(lái)了因戰(zhàn)事而遷居來(lái)此的河州地區(qū)的漢人和回民。再后來(lái),僧侶道人、游醫(yī)工匠、各族商戶等也紛紛匯聚于此,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的格局,使得這座高原城鎮(zhèn),蓬蓬勃勃地發(fā)展起來(lái),成為藏地有名的旅游勝地。而我筆下的桑多鎮(zhèn)的母體,就是她。”扎西才讓說(shuō)。
青年時(shí)期,喜愛(ài)文學(xué)的扎西才讓深受艾略特、聶魯達(dá)、惠特曼、泰戈?duì)柕任暮赖挠绊憽Kf(shuō):“國(guó)內(nèi)詩(shī)人,我比較喜歡昌耀、葉舟和阿信的作品。而藏族民歌和格言(如《水木格言》等)對(duì)我的寫作,也有直接的影響。作為一個(gè)藏族作家,藏族傳統(tǒng)詩(shī)歌里擅長(zhǎng)的賦、比、興等手法,在我的寫作中也使用得比較多,尤其是藏族史詩(shī)《格薩爾王》,讓我學(xué)會(huì)了在詩(shī)歌中如何敘述、如何描寫、如何抒情的技巧。”
1999年,扎西才讓寫了三首詩(shī)發(fā)在《詩(shī)刊》。其中一首名叫《啞冬》,里面寫到一條名叫桑多的河。扎西才讓告訴記者:“那時(shí),我還沒(méi)有要寫桑多鎮(zhèn)的打算,只想寫甘南的某一條河,在我的想象中,這條河應(yīng)該有歷史,有使命,有藏地屬性。但由于工作繁忙,與河有關(guān)的詩(shī)歌,寫得很少,究竟寫哪條河,始終沒(méi)定下來(lái)。我曾考慮過(guò)寫流經(jīng)甘南的黃河和白龍江,但總覺(jué)得不適合,因?yàn)辄S河在瑪曲,白龍江在舟曲,離自己太遠(yuǎn),有一種疏離感,不好描寫。所以這個(gè)計(jì)劃暫時(shí)擱置了,但我心中一直在醞釀著、等待著、尋找著……”
2017年,當(dāng)了幾年漢語(yǔ)言文學(xué)老師的扎西才讓離開(kāi)學(xué)校,到當(dāng)?shù)氐奈穆?lián)任職。閑暇之余,他很愛(ài)翻地方志書(shū)。一次偶然的機(jī)會(huì),他讀到了民國(guó)史學(xué)家張其昀編著的《夏河縣志》。扎西才讓難掩如獲至寶的心情:“作者用大量的筆墨,寫到夏河縣的最重要水系——桑曲,以及與這條河有關(guān)的夏河縣的歷史、氣候、地形、生物、民族、農(nóng)業(yè)、林業(yè)、畜牧、礦產(chǎn)、商業(yè)、交通、政治和宗教。那些簡(jiǎn)潔、準(zhǔn)確又優(yōu)美的文字,深深地吸引著我。一條我身邊的河流,在他的筆下,就是個(gè)自成體系的世界。我暗暗下定決心,我也得寫桑曲,得傳承他的理念、繼續(xù)他的抱負(fù)。”于是,在當(dāng)代,在藏地,在一個(gè)藏族詩(shī)人筆下,“桑多河”的雛形初現(xiàn)了,并且逐漸面目清晰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
有了“桑多河”,自然就有了“桑多鎮(zhèn)”。扎西才讓說(shuō):“在我看來(lái),河,是流動(dòng)的生命,是帶狀的歷史,是散點(diǎn)式的民俗。鎮(zhèn),則是生命的焦點(diǎn),是凝固的歷史,是民俗的萬(wàn)花筒。一條河,一個(gè)河流源頭的鎮(zhèn)子(桑多的藏語(yǔ)意思是大夏河源頭),就逐漸形成了我的文學(xué)版圖。”
從2015年始,扎西才讓開(kāi)始著手精心打造與此河此鎮(zhèn)有關(guān)的文學(xué)世界,這個(gè)文學(xué)世界用他的話來(lái)說(shuō)就是“一個(gè)藏地甘南的‘語(yǔ)法空間’”。為了使筆下的桑多鎮(zhèn)更豐富、輻射面更廣,扎西才讓甚至以甘南州其他七縣的部分小鎮(zhèn)(如拉卜楞鎮(zhèn)、郎木寺鎮(zhèn)、尼瑪鎮(zhèn)、柳林鎮(zhèn)、新城鎮(zhèn)等)作為參照的對(duì)象,既關(guān)注它們的共性,又擇取它們的異性,試圖在尊重基本史料的同時(shí),建構(gòu)出文學(xué)意義上的藏地小鎮(zhèn)史,給讀者呈現(xiàn)出一座真實(shí)、陌生又奇異的紙上城邦。
繼在《詩(shī)刊》發(fā)表《啞冬》后,扎西才讓的文學(xué)思潮一發(fā)不可收拾,陸續(xù)在《詩(shī)刊》《民族文學(xué)》《星星》《散文詩(shī)》等雜志上發(fā)表了《我覺(jué)得寂寞》《雪山的思考》《我的另類生活》《草原上這個(gè)寧?kù)o的小鎮(zhèn)》等作品。自2012年開(kāi)始,扎西才讓在《飛天》《青年作家》《中國(guó)詩(shī)人》《詩(shī)歌月刊》《上海詩(shī)人》《星星》《十月》《散文詩(shī)》《詩(shī)探索》等雜志上發(fā)表了《我的山谷》《羚城曲》《羚城十四行》《羚城》《羚城曲》《牦牛頭骨》《雪域·萬(wàn)物生》《桑多鎮(zhèn)詩(shī)鈔》等作品,“桑多河畔”系列作品呼之欲出。 2015年—2017年,隨著在《詩(shī)刊》《詩(shī)選刊》《中國(guó)詩(shī)歌》《黃河文學(xué)》《草堂》《飛天》《民族文學(xué)》《詩(shī)探索》《臺(tái)港文學(xué)選刊》等雜志發(fā)表了《高原月》《那年那月的殘酷游戲》《黑鐵鄉(xiāng)村》《桑多鎮(zhèn)》《桑多魂》《甘南夜話》《桑多河畔》《渡口》《桑多鎮(zhèn)秘史》《阿卓》《聽(tīng)說(shuō)你要去桑多鎮(zhèn)》等作品,這時(shí)候,扎西才讓就已經(jīng)勾勒出了“桑多系列”的基本雛形。
除了詩(shī)歌作品外,“桑多”題材的散文和小說(shuō)的寫作,也在同步進(jìn)行。2016年,《文學(xué)港》刊發(fā)了扎西才讓大約三萬(wàn)字的散文《詩(shī)邊札記:在甘南》,其中有一半的篇章就是“桑多”題材。“桑多”題材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也有收獲。短篇小說(shuō)《達(dá)珍》,刊于《芳草》雜志,后來(lái)被選刊轉(zhuǎn)載。之前,《西藏文學(xué)》也刊發(fā)過(guò)《來(lái)自桑多鎮(zhèn)的漢族男人》,被轉(zhuǎn)載。這些作品,都是“桑多”題材,扎西才讓都收入到自己的中短篇小說(shuō)集《桑多鎮(zhèn)故事集》中了,這本小說(shuō)集也入選了2019年《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之星叢書(shū)》。
扎西才讓總結(jié)道:“這些作品都以青藏高原上的藏地小鎮(zhèn)——桑多鎮(zhèn)為故事發(fā)生地,以上世紀(jì)90年代至今為時(shí)間段,通過(guò)塑造桑多鎮(zhèn)的一系列人物形象,集中呈現(xiàn)了桑多人對(duì)世界的認(rèn)知,對(duì)人生的看法,對(duì)生存價(jià)值與生命意義的反思。我的想法,就是想借這些小說(shuō),來(lái)探究深藏在人性中的幽暗與光明。”
2018年—2019年,在長(zhǎng)達(dá)一年半的時(shí)間里,扎西才讓在一個(gè)藏族村落駐村,做精準(zhǔn)扶貧工作,這段經(jīng)歷也對(duì)他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和創(chuàng)作源泉。他說(shuō):“在田間地頭,在高山牧場(chǎng),在村落莊院里,頻繁地接觸,使我從村民的身上,感受到或豪邁或含蓄、或陽(yáng)剛或陰柔、或熱烈或安靜的生命的氣息。這氣息是如此明顯強(qiáng)烈,小時(shí)候我感受不到,也不曾體驗(yàn),而今我意識(shí)到,他們始終這樣真實(shí)而堅(jiān)韌地生存著,其此起彼伏的呼吸,若有所思的眼神,濃郁腥味的汗氣,甚至或高聲大嗓或低沉嘶啞的聲息,都讓我覺(jué)得:他們要走進(jìn)畫(huà)布,走進(jìn)文學(xué),走進(jìn)電影,走進(jìn)歷史文化的長(zhǎng)廊,在中國(guó)文學(xué)人物群像譜里,留下他們濃墨重彩的肖像。這使我更清楚了今后的寫作方向,明晰了我的作品應(yīng)該呈現(xiàn)的內(nèi)容。我分明地感受到了身上的重?fù)?dān):做一個(gè)有擔(dān)當(dāng)?shù)淖骷遥梦淖謥?lái)塑造桑多人的形象,勾勒他們的歷史,釋放他們的愿望,觸摸他們的靈魂。桑多題材的創(chuàng)作,其意義莫過(guò)于此。”
回顧自己的寫作生涯,扎西才讓感慨地說(shuō):“青年時(shí)期的寫作,我癡迷于對(duì)自身生活特別是愛(ài)情生活的展現(xiàn),覺(jué)得人世間最美好也最痛苦的,莫過(guò)于愛(ài)情了。歌頌地域和民族文化時(shí)也一樣,走的是籠統(tǒng)的、單純的、直接的路子,仿佛一個(gè)在狂野上橫沖直撞的醉漢。隨著歲月的磨礪,我從一個(gè)相對(duì)狹隘的創(chuàng)作領(lǐng)域拓展為人類社會(huì)觀察者的時(shí)候,我才真正感受到寫作的重要性。自從解決了‘寫什么’的問(wèn)題后,慢慢地,我在紙上,用文字畫(huà)出了雪山之下、長(zhǎng)河之畔的桑多鎮(zhèn)。我寫作時(shí)的聚光燈,不再僅僅聚照我自己,而是更關(guān)注他人的世界:他們?cè)诟墒裁矗克麄冊(cè)谙胧裁矗克麄冊(cè)噲D保留什么改變什么?他們的命運(yùn),是否關(guān)系到更多的民族?他們的努力,是否影響并改變著人類的生存?就這樣,我用自己的作品,對(duì)桑多河畔的藏區(qū)村落作了深描,把小鎮(zhèn)居民——桑多人的生存狀貌,推向了可敬的讀者。”
近幾年,扎西才讓正在投身于新詩(shī)集《甘南簡(jiǎn)史》的創(chuàng)作。他說(shuō):“這是一部以詩(shī)歌的方式來(lái)講述甘南州從古至今的歷史詩(shī)集,在體例上,我采用了編年體的形式,內(nèi)容涉及到地方歷史的發(fā)展脈絡(luò)、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呈現(xiàn)的是一位詩(shī)人在中華大歷史的長(zhǎng)河里,如何回看、認(rèn)知地方史的態(tài)度、感情和觀點(diǎn)。我希望這部作品,能為我的知天命之年,畫(huà)出完美的句點(diǎn)。”
蘭州日?qǐng)?bào)社全媒體記者 華靜
相關(guān)新聞
- 2020-12-03《彭高棋傳》在蘭首發(fā)
- 2020-12-02異鄉(xiāng)人作客甘肅戈壁灘三十載:“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
- 2020-12-02科幻作家星河:科幻作品將逐漸從神秘走向?qū)憣?shí)
- 2020-12-02《錢鐘書(shū)的學(xué)術(shù)人生》出版 首次公開(kāi)一批書(shū)信、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