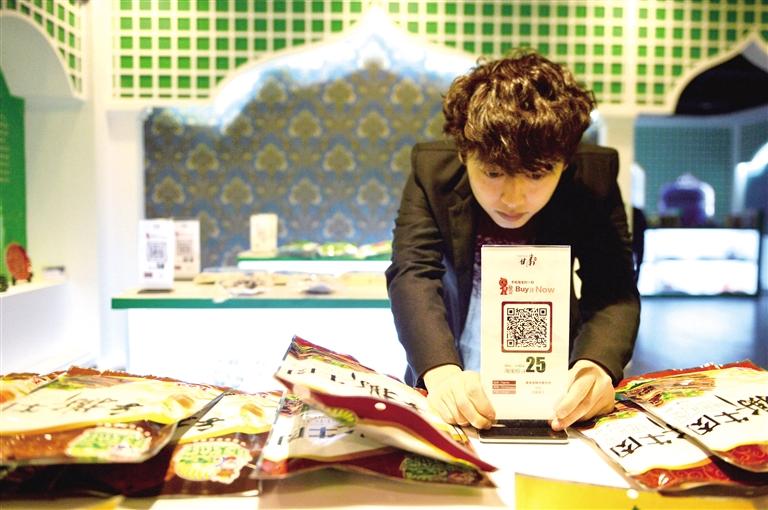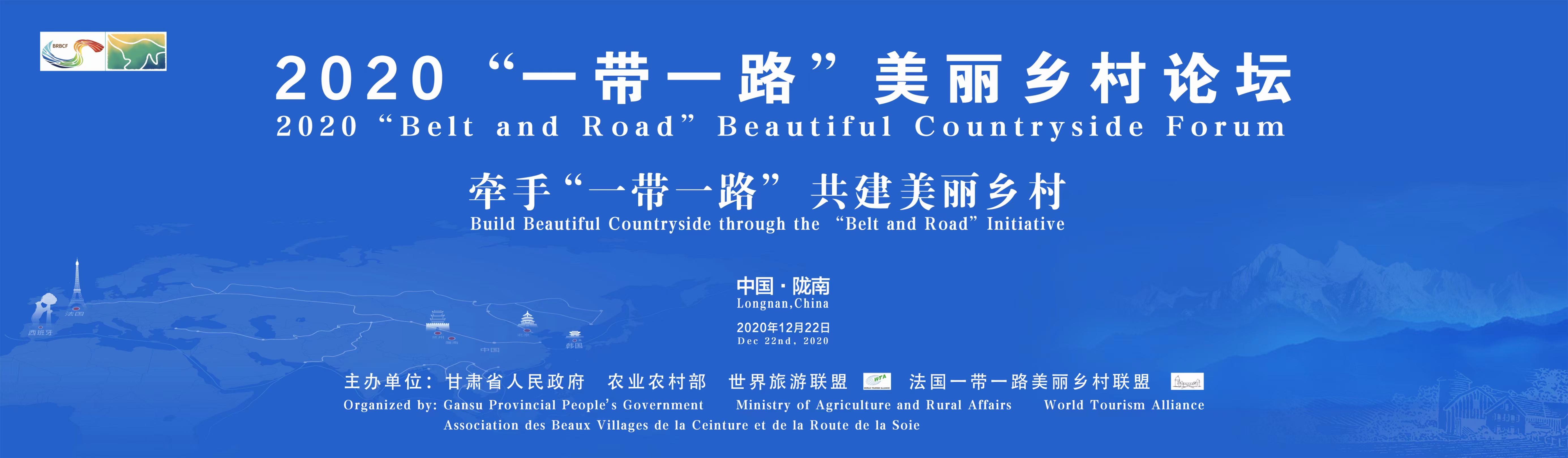南川界碑亭
重陽節那天,因有事去沿安西溝村,順便來到南川界碑亭。
南川是一個一百多戶的村子,五百多人,屬于武山地界,向南行不足五百米便是岷縣的馬塢鎮。中午時分,一行人到達南川村。由于山區地勢高再加上天氣突變的緣故,天空中不時從翻騰的云朵縫隙中射下的秋陽及時地送出絲絲溫暖,不遠處的田野里,正待收掰的玉米棒子,彎著腰探出金黃的笑臉,葉子讓風吹得嘩啦啦作響,沐著迎面而來的風,讓每個人熱乎乎的心里,頓時產生了激動不已的情愫,因為馬上就到向往已久的界碑亭了。
界碑亭位于南川村的南邊路口,洛門至岷縣公路從旁而過,過往的車聲和笛鳴映著村莊深厚的文化底蘊。停下車,大家走下來,眼前一座新修的建筑映入眼簾:公路左側的仿古六角翹檐亭,坐東朝西,石基琉瓦,畫棟雕梁,青松翠柏遍植四周,蔚為壯觀。頂上深紅琉璃瓦裝飾,混凝土造頂,六檐下檐邊為大紅色,迎著路的正面有界碑亭三個字,乳白色。六根桔紅水泥柱下鋪著紅、白和芝麻白三色地磚,柱頂為草綠色,邊上繪有山水草木圖案及木格圖式,顯得古樸典雅。里面中間大面積是蘋果紅色地磚,走上去,給人清亮舒緩之感,正中紫赭花崗石質界碑,呈圓首長方形,上寬下窄,上陰刻楷隸相間“寧遠縣交界”五字,凹形字用鮮艷的大紅涂著,碑座是淺紅色地磚做的,碑高約七八十公分,上郊寬四十多公分。是現存寧遠縣最早的實物佐證。據說,更早的時候,在寧遠縣界碑的另一側,還有一塊岷州的界碑,如今已找不到蹤影。轉過去,背面石紋粗糙,估計沒字模糊看不清,人們懷著虔誠膜拜的心愫,手撫著界碑,仿佛觸摸到歷史的陣陣心跳。
武山,自古為“絲綢之路”要塞,素有“東通三輔,西控五涼”,具一夫當關之勢,誠隴右重地之稱,雖處古之邊陲地帶,但建縣極早。史載,春秋為戎地,秦歸隴西郡,東漢中平五年(188年),始置新興縣,宋,元,明,清至民國初,均為寧遠縣,民國三年更名為武山縣至今,北宋祟寧三年(1104年)寧遠建縣時立此碑,碑文書體寬博疏朗,拙樸雄健,有石門頌,秦鶴銘之遺韻。
沿安鄉南川村南頭,豎立的寧遠縣界碑,是縣級行政界線的分界標志。立于分界線上的特定地方。這塊寧遠縣界碑,北宋王朝升寧遠寨為寧遠縣的時候,被立于沿安鄉南川村內,從北宋祟寧三年(1104年)算起至今已過900多年。來來往往的游人,立于碑前,一次次注目于上寬下窄圓首長方形紫赭花崗石質碑,雙目閃現于歷史的浪花之中,在敬仰中搜尋,在膜拜中贊譽,讓心潮久久不能平靜,一個個縱馬馳騁的硝煙年代,一段段休養生息的治世時期,都在界碑的記憶深處留下刻骨銘心的烙印。轉過身,亭子右側不遠處,有一個一人高的記事碑,為新建界碑亭而立,擇錄部分碑文如下:“千禧龍年,世紀之交,又逢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機遇,為保護文物勝跡,弘揚地方文化,經縣政府倡導,縣民政局,沿安鄉黨委,政府及各界有識之士鼎力相助,在界碑處新建仿古六角檐尖碑亭,其前有洛門至岷縣大道直通隴南,合作。其背聞馬塢河急湍潺湲,流經南河匯入渭水,亭左與岷縣馬塢鎮隔河相望,亭右沿安鄉政府依山傍水,土質肥腴,物華民豐,登高遠望,東有竹子山諸峰高聳崔嵬……”洋洋碑文,記述著重建緣由、過程及所處的優越地理位置等等一些事宜。
在界碑亭公路對面,還有一口井水,清澈甘甜,一年又一年的寒來暑往中,用脈脈的溫情,見證著交界碑亭的悠遠往事!
據村里人講,在界碑亭建成以前,界碑立于南川村水井之旁,關于南川村,還有好多故事,說到南川,也不得不提及消失了的永安鎮。北宋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原秦州屬寧遠寨的馬塢鎮劃歸舊岷州后,寧遠以舍鎮保莊的辦法,留下二十多個村莊未劃給岷州,均在寧遠治轄之內,不難想象,辦事人有著深謀遠慮。此后,寧遠縣為了防范蕃民的進犯,以保鞏昌府、秦州的安危,以“永遠安寧”之意設立了永安鎮,設關隘屯兵把守,為歷史戰略要塞。
據清康熙四十一年編撰的《岷州志》 疆域中記述:“馬塢鎮之宋家莊,與寧遠永安鎮接壤,勒石定界,疆土劃然……”永安鎮何代所建?何時消失?經查閱康熙、乾隆、道光三朝的《寧遠縣志》 均有永安鎮文字和疆域圖記載,與馬塢鎮隔河相望。并記述寧遠縣有九處關隘,分別是:大木樹、馬塢、水關、文盈、魯班峽、石門、太陽山、硯石峽和木林峽,馬塢為其中之一,有岷州番兵設墩臺了望把守。《清康熙寧遠縣志》記載,永安鎮古址,在現在的南川村北,永川河(今天的西溝河,歷史上河水很大)南地段,為當時的邊陲小鎮,規模較小,百余戶人,背靠古莊坪,南北一字形街道,鎮南北兩端修建上殿下殿各一座,據老人回憶,從殘留遺址上看很像隴西的鐘鼓樓,中間為民居和商鋪,后溝(今西溝)建有金蓮寺,紅崖寺等,古鎮的文化商業設施齊全。清同治二年,古鎮衰落。清光緒初年,暴雨成災,古莊坪后山山體大面積滑坡,泥石流順坡而下,摧壞淹沒了古鎮的大部分房屋,一些房屋埋入地下,人員傷亡很大。近年來出土大量的方磚、大瓦、絲綢碎片、亡人殘骸,見證著古鎮的歷史輝煌……
站在界碑亭,與古鎮馬塢隔河而望,一邊是武山,一邊是岷縣,依衣帶水,這邊雞鳴,那邊犬吠,語音交際,穿衣帶帽,姻親往來無不相互在影響中相互發展著,穿過歷史云煙的時光如一件禮服,界碑恰是一枚閃著光與亮的扣子。而現實中的兩縣劃界和邊界形成的過程,而非一朝一夕,是在各民族的交融發展中發展,孕育著無言的潛移默化而逐步形成起來的,結果是光明可見的,而言及過程則是曲折漫長的,給人留下了無限的遐想。
界碑,將一段紛擾的歷史,以承前啟后進行了梳理安排,從此,少了紛爭和無奈,多了發展和希望,出現修養生息后的太平局面,永安鎮的輝煌,不得不說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而今天守望兩縣的界碑亭,更是目睹著西部大發展中鄉村振興的藍圖在日新月異中奮斗著,為可喜的小康生活闊步前行著。
離別的腳步總在依依不舍的留戀中讓夕陽相催,該起程了,望著豐碩的玉米棒子,莊嚴的界碑亭,多情的鄉風映著村民淳樸的笑聲,伴隨滾滾前行的車印,送了一程,又一程……
□毛韶子
相關新聞
- 2020-12-23雪落村莊
- 2020-12-22冬至已至
- 2020-12-21庚子的云彩
- 2020-12-14來高臺 咥一碗拉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