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我也是個裝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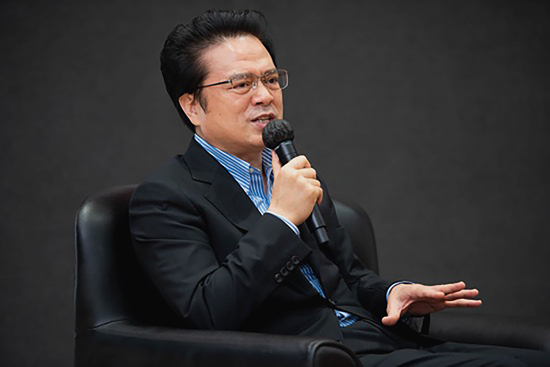
陳彥
多年以后,不僅是縣城,全國很多人可能都在關注陳彥:他的長篇小說《主角》在2019年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近日,由他小說改編的同名電視劇《裝臺》收視和口碑雙贏。
十幾歲就喜歡的寫作,是陳彥“最無悔”的選擇,一頭扎進去,再也沒有出來過。17歲,還在縣城生活的他,第一次在《陜西日報》發表散文,又在《陜西工人文藝》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說。看到作品變成鉛字,陳彥非常激動,一度覺得“整個縣城的人都在關注我”。
多年以后,不僅是縣城,全國各地很多人可能都在關注陳彥:他的長篇小說《主角》在2019年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近日,由他小說改編的同名電視劇《裝臺》贏得收視和口碑雙贏。
最開始寫作,就是想發表;漸漸地,是自己想說點什么。陳彥說,既然活在這個世界,就想對這個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
記者:電視劇《裝臺》熱播,讓很多觀眾第一次知道有這樣一個工種。你在劇團待過幾十年,對哪個工種最感興趣?
陳彥:那還是編劇,能夠把很多思考融入到一個劇里,用一些獨特的方式表達出來。但我很早就和裝臺工熟悉,隨著戲劇舞臺越來越復雜,本團的人完成不了裝臺的工作,就要雇人。一開始雇一些農民工,請他們做搬運等一些基礎性工作,漸漸地,雇傭的人越來越多,也包含了一些技術活,也有了團隊,《裝臺》中的刁順子就是這樣一個工頭。
一開始關注裝臺工,是因為寫一個舞臺劇《西京故事》,講的是農民工進城后遭遇的生活挫折、心靈煎熬,以及他們在困頓中的奮進。寫完舞臺劇,感覺很多東西沒有完成,就寫了一個50萬字的同名小說——還是意猶未盡。
這時,剛好我從劇院調離,跳出去后再看,越來越感覺到農民工在社會大廈建設工程中的作用和意義——卻往往被忽略,就用了兩年時間來寫《裝臺》。《裝臺》中寫到三次螞蟻搬家,螞蟻們頂著比自己身軀還要大得多的東西爬行,我也努力想寫出底層人的悲苦和奮斗。
記者:電視劇比小說的色調更溫暖一些,你覺得影視和文學對觀眾或讀者而言,承擔的功能有什么不同?
陳彥:文學總體來說是藝術的母體,影視劇在改編過程中,會受到外部條件比如市場、觀眾喜好等的牽引,會有不同的走向。《裝臺》改編成電視劇后,更溫暖,觀眾接受起來也比較愉悅,這是按照電視劇的創作規律進行的。
從某種角度來說,文學和影視承擔的功能相同也不同:相同的,都是引領社會的真善美;不同的,可能文學的處理方式會更豐富、多側面,但這在影視劇呈現中也許會帶來歧義,所以影視劇會更簡潔、清晰一些。
記者:一部《主角》一部《裝臺》,一個臺上一個臺下,寫的時候會有什么不同?
陳彥:先寫的《裝臺》,后寫的《主角》。《裝臺》故事的延續時間是十幾年,《主角》則是從改革開放到現在的40年。如果寫《裝臺》僅僅寫裝臺工,意義不大,同樣的,《主角》也不僅僅寫舞臺上的主角,而是通過這么一個形象、一群人物,對作家自己長時間以來的社會閱歷——包括所認識的世界——的藝術建構。
記者:聽說在創作過程中,你會花很多時間去體驗生活?
陳彥:如果寫舞臺,說實話我太熟悉了。我在里面浸泡了幾十年,不是體驗生活,這就是我的生活,我本身是其中一員。當然有時候,我也會刻意去接近一些人物。寫《西京故事》時,我經常到單位對面的勞務市場,還深入到周邊農民工居住的村子,和農民工聊天,下了一番功夫。
我有一個觀點,寫作時,如果你對一個東西不熟悉,下筆的時候就沒有游刃有余的感覺;反之,則會下筆如有神,還可能有神來之筆——這需要你對生活有提煉能力、概括能力,當你沉浸其中再跳出來,越看越清晰,感受到生活的別樣意味,寫的東西就可能是最好的。
記者:你覺得自己屬于舞臺的哪個位置?
陳彥:我有時候像編劇,有時候像導演,有時候可能也像裝臺工。
記者:怎么理解像“裝臺工”?
陳彥:我把我心中所認識的戲劇、舞臺、人物,以及周遭環境,都裝起來、建構起來。戲劇本身就是社會的產物,無論古今中外,都應該是文學藝術比較早期的一種創造形式,裹挾的歷史和社會信息比較豐沛。把戲劇放到今天大的社會背景下,去透視它,又通過戲劇這個窗口,去看社會的滄桑巨變,這里面很有味道。
裝臺也是一種隱喻,人生也可以歸納成兩個狀態:一個是自己替別人裝臺,別人唱主角;一個是自己唱主角,讓別人給自己裝臺。人們相互搭臺,無非就是舞臺大小和角兒大小不同。
記者:如果接下來還寫舞臺,你想寫什么?
陳彥:其實已經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說《喜劇》,大概今年春天出版,寫的是關于小丑,在舞臺上演小丑的父子三人的人生。
記者:在工作之余,你喜歡做什么?
陳彥:我是一個生活比較簡單的人,不喝酒、不太參與應酬,上班時候好好上班,下班以后讀書寫作。其實一個人如果減少了應酬,就有大把的時間讀書、做事。有些東西看著熱鬧,有時候非常痛苦且浪費時間。
記者:小時候讀過的第一本讓你記住的書是什么?
陳彥:我小時候生活在商洛的山里,家里沒有多少書,印象中看的第一本比較“大”的書是《高玉寶》,當時我大概10歲。等到了十幾二十歲,開始從事文學創作,當時最盛行的是俄羅斯文學,托爾斯泰的、屠格涅夫的、果戈里的、普希金的,還有法國巴爾扎克的、雨果的,都看過,閱讀量很大,讀得很瘋狂。
在縣城一個單位工作時,住在宿舍,床上靠墻碼著半人高的書,晚上就睡在書堆邊。每一本書都認真看,還在上面畫各種杠杠、做筆記。
記者:哪本書對你的影響最大?
陳彥:這是一個綜合性的東西,一段時間我喜歡看西方文學,一段時間又喜歡看中國文學,有時候是現實主義,有時候是先鋒小說,有時是歷史,有時是哲學,有時還會大量關注天文學。但自從我喜歡文學,一直就沒有改變。我始終覺得,人一輩子要死死守住的,就是自己所喜歡的東西,就像福克納守住了他的約克納帕塔法。
在今天這個時代,誘惑很多,尤其對年輕人來說,有各種速成法、厚黑學,教你怎樣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回報,聽著有道理,但真的沒道理。所有事情都是一步一步去扎扎實實扛下去的,扛到最后可能做出一點事情,但扛不到最后一定不行。
記者:幾十年來沒有過想放棄的一刻嗎?
陳彥:真沒有,幾十年來工作單位、職務都在變,但始終沒有放棄創作。沒有創作,工作之余我干啥?不過我一直有個主張——作家不要當專業作家,這可能會固化自己的圈子和認知,不免影響創作。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是多樣的,其中一種就是你本身就在現場,這可能對寫作會更好。
記者:最近手頭正在看什么書?
陳彥:英國作家拜厄特的《巴別塔》,寫的是一個女性在事業與婚姻、自由與限制之間的痛苦與掙扎。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女性話題,作家寫得很獨特,會提到此前一些經典的關于女性的小說,比如《包法利夫人》《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等。作家跳開了小說的情感走向,有時候會非常理性地夾雜評論體、書信體和法庭審訊詞,探討女性到底是要做自由的主人、還是進入自由受到限制的家庭生活,如何掙脫,掙脫之后又帶來別的傷害等等……
記者:你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怎樣的?
陳彥:比較中性。性別只是大自然的一種分別,生命是千差萬別的,有的可能專注事業,有的可能獻身家庭,很復雜,最重要的是女性自己的生命感受,她到底想要什么。其實男性也是如此,到底想要怎樣的活法。(蔣肖斌)
相關新聞
- 2021-01-28梁曉聲《我和我的命》:人有“三命”
- 2021-01-11王蒙:在手機時代,文學依然是“硬通貨”
- 2020-12-09阿來:一本書是自然發生的
- 2020-12-07阿來:讓道路筆直 讓靈魂清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