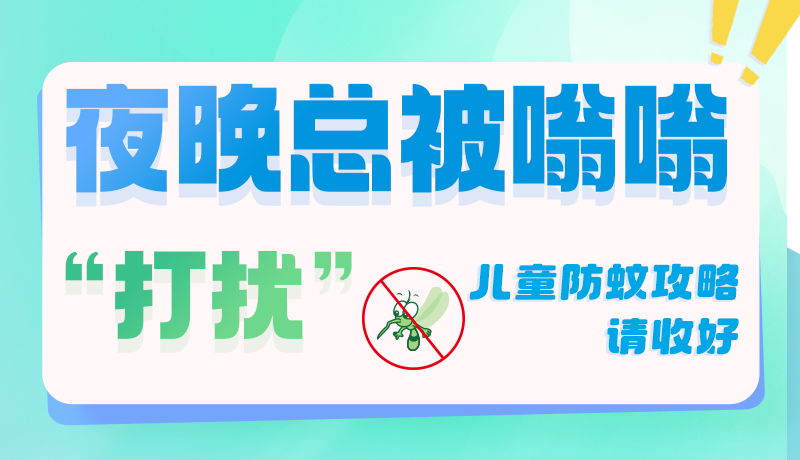雨水從未停止澆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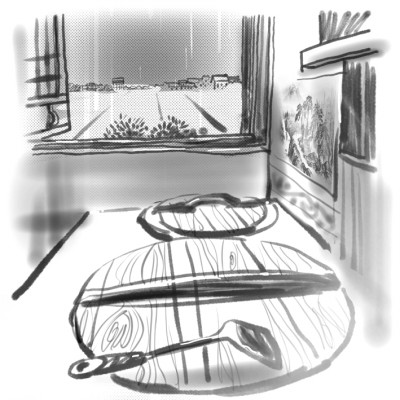
郭紅松繪
“時候頻過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站在小雪時節綠意依然的杭嘉湖平原上,我想起了陸龜蒙的這句詩。經歷了連續的雨天和氣溫的驟降,大地即將進入休眠。
走在那片土地上,我時時忍不住微笑。此刻,當我回想、記錄,又忍不住微笑。我愿意回想那些美好的畫面,享受一份由衷的歡喜。
一
從木窗望出去,一大片金色稻田鋪向遠方,一陣濃郁的稻香瞬間逼近,漫至鼻尖。將目光收回,一個古老的灶頭、灶頭上同樣古老的一幅幅彩畫落入了視線。
雪白的底色,濃烈的色彩,畫的是神話故事、歷史人物、花鳥竹魚,也有百姓勞作、生活的場景,勾勒的,是一屋、三餐、四季的回憶,傳遞的,是浙北水鄉漁農文化和運河濕地文化交織的濃郁韻味。
“有家必有灶,有灶必有畫”,嘉興古塘村的鄉土藝術,體現了生活的儀式感,也是對人生的慰藉。已過古稀之年的灶畫藝人施順觀從18歲執筆至今,畫過的灶頭不計其數,收過的徒弟也不少,灶畫藝術卻瀕臨失傳。讓老人欣慰的是,去年夏天,30名小學生第一次在古塘村認識了灶頭畫,當場拜了師。
灶頭窩著兩口大鐵鍋,冒著熱騰騰的香氣。主人揭開靠窗的鍋,燉了幾個小時的紅燒鵝嘟嘟沸滾著,揭開另一口鍋,細密的竹籬笆片托著一大塊用稻草系著的紅燒肉,已燉得酥爛,油光锃亮,熱氣騰騰,令人垂涎欲滴。
“晚飯馬上好了。”他砰地蓋上鍋蓋。
我將凍得冰冷的雙手伸向灶里的柴火,柴火即將熄滅,微微的星火一呼一吸,像在說,屋后有田,鍋里有肉,別急別急。
等晚飯的時候,我站在橋邊看一群鴨子游水,一群雞在水邊的籬笆墻邊喊加油,有幾只飛上了結滿紅果的柿子樹,伸長著脖子,一只小黑狗沖鴨子叫兩聲,又沖雞們叫幾聲。我站在橋上看熱鬧,呵呵笑。橋的另一邊,一個農婦在岸邊鋤地。我遠遠地看著她,想,村里的農耕文化館里,是否有她家捐的農具?繡娘工作室里,可有她的繡品?某個周末,會有一群城里來的孩子到她的田里跟她做農事嗎?她顧自鋤地,顧自接手機來電。我又想,她家里一定也用上了煤氣灶、抽水馬桶,臨睡前也會刷抖音,冷了也會開空調,過節了也會網購,她走的夜路,每一步都有路燈照亮。
稻草肉和紅燒鵝太好吃了。嘉興禾幫菜最大的特點就是“土”,土得活色生香。此時此刻,應了離此不遠的海寧徐志摩故居里的一句話:“我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份,我只要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二
畫了30多年畫的農民畫家美寶站在油車港菱瓏灣小巷入口的廊檐下,仰頭看著腳手架上畫著墻畫的三個兄弟。零星的微雨飄過,打濕了她摻雜了幾絲白發的短發和近視眼鏡。已經畫了三天,要將整面墻畫滿。都是喜慶的題材,鯉魚跳龍門、賽龍舟、糧倉、桃樹。
千百年來,源于逢年過節、衣食住行、生喪嫁娶等民俗,汲取了傳統剪紙等民間藝術的嘉興農民畫成了江南水鄉的一朵奇葩。上世紀80年代起,20歲左右的美寶們便開始涂鴉。這是一群從田埂上赤腳走來的農民,他們白天下地,夜晚作畫,用最稚拙的筆法、最農民的審美、最無拘無束的想象、最真摯的鄉情,把密布的河網、清澈的水流,把白墻黛瓦、小橋流水、桑綠稻黃、蠶肥鴨壯、古芳流韻和自己的生活都畫在了房子里、圍墻上、灶頭上以及畫布和白紙上。承載著中國鄉村幾十年巨變的一幅幅農民畫,不僅是一種藝術,更是一種文化記憶、一卷史詩。
在農民畫館里,我見到了“油車港十姐妹”的畫——是12位農村老太太,最大的快八十了,最小的快六十了。畫的大多是勞動的場景,采桑、捕魚、曬谷、收糧、車水、插秧等。有幾幅印象派風格的,是她們的老師繆惠新的畫,他的畫已在十幾個國家展出,登上過《時代周刊》。
美寶的《月夜》畫的是一個老人抽著煙斗,長滿菱角的湖水里張著網捕魚,一彎月和一只狗陪著他;《新絲綿上市》畫的是女人孩子們圍著一個水缸剝蠶繭套絲綿兜,身邊是雞鴨貓狗們,每個人每只動物都憨態可掬,讓人一看就不由自主地微笑。
美寶和這些老太太的畫都曾在全國美展展出,并遠渡重洋去澳大利亞等多國展出,她們仿佛也隨著畫,走到了很遠的地方。
三
風很大,很冷,我繞著那棵巨大的、棕紅色的“稻穗”走了一圈,感覺到了暖意。
這座造型奇特的建筑是運河畔陶家村舊糧倉改造成的網紅空間——陶倉理想村。幾個月前,十多場藝術活動吸引了長三角上萬游客來此打卡。嘉興這座建制于秦朝的歷史文化名城,自古繁華富庶,名人輩出。陶倉,曾是明清時期王江涇名門望族陶氏宅居所在地,后被征作糧站、植絨廠,閑置時經歷了一場大火,廢棄多年。一群年輕的“80后”保留了糧倉主體和紅磚元素,將它變成一個三千多平方米的藝術中心,像高聳入云的一棵稻穗。中庭,一束天光漏下來,對比并不強烈的光影給人無限的想象。東倉和西倉,黑色鐵質旋梯與磚紅墻面,水磨石荷花圖案地面,巨大的拱形落地玻璃窗,玻璃窗外層層疊疊的拱形連廊,讓人有一種穿越時空進入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錯覺。
顏值只是陶倉的一個元素,這里定期舉辦的藝術活動如“新陳代謝”當代藝術展、植物裝置藝術展、新車發布會、創意市集、迪斯科舞會等,吸引了遠方的年輕人和近處的居民,讀詩、彈唱、燒烤、吹風、遛彎、看露天電影、住帳篷、看星星。
陶倉對面的一幢小白樓里,住著十來個工作坊的年輕“村民”,大多做文創和藝術,彼此間已親如家人。這里,高度契合了他們的生活理念和審美方式,他們將這里營造成了人與天地對話的樂土,人們最容易抵達的“詩和遠方”。
就這樣迎風走著,忘了是哪一個村莊,初冬的灰暗底色上,驟然亮起一片新綠,水邊一畦畦蘿卜芹菜萵筍如一群孩子嘰嘰喳喳圍在老人身邊。這個村莊已經很像一個城市了,甚至有花園,如果有一大片草坪就更像了。好在沒有。村里將本該做草坪的地分給了家家戶戶用來種菜,圍上了籬笆。鄉村空間的重塑,不是簡單模仿城市,而是與鄉村風貌契合,菜地和村莊才是絕配,就像我走進一戶農家,聽到鵝齊聲叫喚,隨后聽到一位老人問我“飯吃過了嗎”,而不是“你好”。
四
賣爆米花的中年人悠閑地坐在橋邊的一條石凳上,爐子自動旋轉著,香味隨風彌漫了小雪時節的梅花洲。我們站著,不說話,就十分美好。
“伍胥山頭花滿林,石佛寺下水深深。”千年石佛寺靜靜佇立,兩棵千年銀杏隔水遙望,滿地金黃的落葉讓我想起秀水新區的銀杏天鵝湖。天鵝湖邊剛栽下了一大片銀杏林,像正在發育的少年,散落其中的小火車站、咖啡吧文藝范十足。我想象著這些樹長大后的樣子,眼前浮現了一大片和陽光般純粹堅挺的金黃。
又想起一個村莊,進去才明白,是個村子,也是個動植物園,有猴子、天鵝、梅花鹿、羊駝,還有浮在水上一動不動以假亂真的野鴨,真是煞費苦心——我忍不住笑了,一邊想,日日生活在這里的人該多么歡喜。
四十年前,父親為了讓我們幾個孩子在綠水青山間長大,將家從鎮上搬到了村里。然而,門前通往小鎮的小路,一下雨全是泥濘,鄰居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咸菜就番薯絲湯。一次,父親下班回家見兩個纖弱的女兒正從村口大水井打滿一桶水吃力地抬回家,突然覺得心疼,他心目中“鄉村樂園”的概念里沒有這一幕,無數人對“詩和遠方”的向往里,也沒有這一幕。
四十年過去了,某個夜晚,父親給我發來微信,說娘家小院通往小鎮菜場這最后一條泥路也澆上了柏油。
走在任何一個被現代化改頭換面的村莊,我不會一味懷念從前的鄉村,誰都有把日子過得更舒坦的權利,誰都不能想象所有農村人都待在村里哪兒也不去,炊煙裊裊地等著你來拍照,我們也不愿看見村子里只剩下老人。
村莊像一位老人,他的目光是黃昏時分村口亮起的燈,燈照見大地上無數個村口,一些年輕人的腳印伸向村外,一些年輕人的腳印伸向村里。行色匆匆的人們在無數個村口擦肩而過,每一個人都在用力生活用力愛。
小雪后,大地即將休眠,進入屬于它的夢境,而后,又一次迎來春雨的澆灌。(蘇滄桑)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