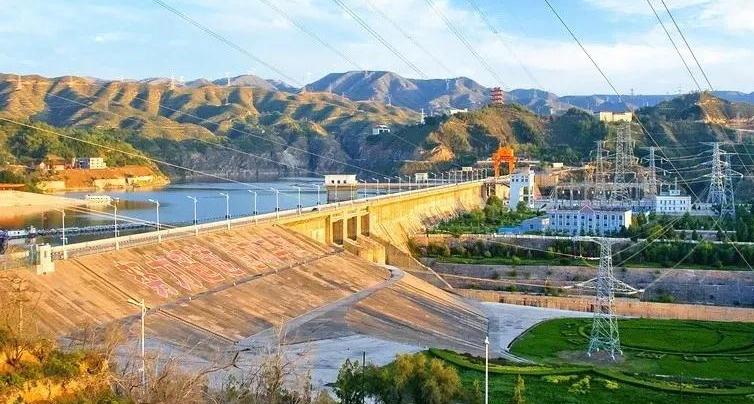丁玲:與世界文學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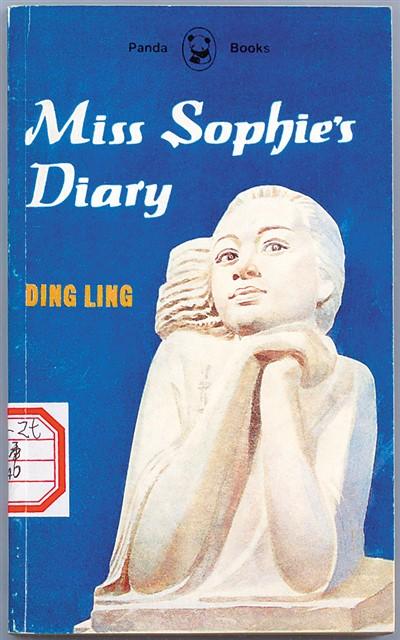
《莎菲女士的日記》英譯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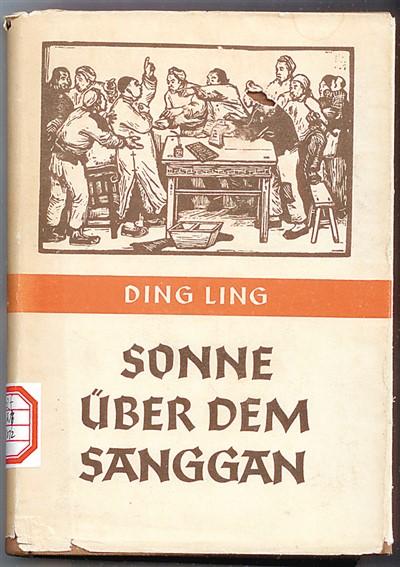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德譯本
世界文學當然應該包括世界上存在的所有文學,但文學文本需要通過讀者的閱讀才能成為有生命的“活的文本”,無論怎樣杰出的經典之作,只有進入跨國家跨地區跨語言的閱讀,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發端于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新文學,在其醞釀、萌生和初創時期,就以前所未有的自覺去汲取域外文學的營養,但由于當時的中國在歐美列強主導的“世界體系”中處于“被殖民”的弱勢位置,中國文學,尤其是新文學,自然也備受漠視。直到國際左翼文學思潮蓬勃興起的“紅色三十年代”,中國的新文學特別是左翼文學開始在世界范圍內獲得廣泛關注,與同時代世界文學產生共時性互動,丁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到域外讀者視線之中的。
“營救丁玲”:國際左翼同聲相應
丁玲最初引起國際文學界的關注,緣自1933年5月國民黨特務對她的逮捕。1927年底以《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登上文壇的丁玲,先以描寫“摩登女性”著稱,不久便以《韋護》《水》等作品,成為中國左翼作家的代表。而國際文學界針對丁玲被捕事件發聲,既表達了對國民黨政權所制造的白色恐怖的抗議,也促成了中國左翼文學的國際性傳播。
當時活躍在上海的美國記者、小說家史沫特萊和她的左翼朋友伊羅生等人,不僅迅速把丁玲被捕的消息發表到英文媒體,廣泛呼吁營救丁玲,同時也翻譯了丁玲的小說作品,發表在美國的著名雜志《亞洲和美洲》(Asia and the Americas)上。據有關研究,史沫特萊和美國著名作家厄普頓·辛克萊都注意到了丁玲的寫實主義作品里潛在的政治感召力,注意到她的小說《水》所表現的自然災害景象,能夠讓美國讀者聯想起中西部地區的相似天災,而“洪水”所隱喻的底層民眾逐漸增長起來的集體抵抗意志,則可解讀為超越了文化差異且能廣泛號召不同國家和地區讀者加入人類憤怒大潮的象征。史沫特萊參與翻譯的《水》英譯本,有意突出了原作中奔騰的洪水和急劇運動的人的身體的描寫,從而把丁玲小說融入到上世紀30年代興起的美國左翼小說潮流之中。(參見蘇真《如何營救丁玲:跨國文學史的個案研究》)
幾乎在同一時期,歐洲的左翼文學界也參與了“營救丁玲”的行動。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巴比塞、伐揚·古久列等公開發表聲明表示抗議,其中,伐揚·古久列是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的主編、法國革命文藝家協會秘書長,他深刻關切中國及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命運,曾與以描寫同時代中國革命著稱的小說家馬爾羅一起組建中國之友委員會。1933年7月,伐揚·古久列和阿拉貢創辦《公社》月刊,翌年便登載了艾登伯翻譯的丁玲小說《某夜》。艾登伯二戰后曾參與薩特、雷蒙·阿隆等創辦的《現代》雜志,并以研究象征派詩人蘭波和古代中國文明與歐洲的關系成為享譽世界的學者。但在當時他還是一位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旅居法國的中國詩人戴望舒幫助了他,使丁玲的作品初次轉換為法文便以高品質的譯文呈現在具有前衛色彩的左翼文學讀者面前。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后來成為布拉格學派漢學研究奠基人的普實克也參與了“營救丁玲”。1932年他來中國留學,專業興趣本在古典文學,但中國和捷克所處的共同境遇,讓他在中國新文學作品中感受到了共鳴,而魯迅等新文學作家為翻譯弱小民族文學所做的努力,更讓他感佩不已。1934年,他在捷克的《創作》雜志上發表關于丁玲的評論,第一次把這位女作家介紹給地處歐洲的弱小民族國家,其意義遠遠超過了一般所說的跨文化譯介。
透過丁玲理解中國革命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逃脫了國民黨囚禁出現在陜北革命根據地的丁玲,以一個文藝戰士的姿態奔走于抗戰烽火前線,她的傳奇經歷使她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對象。這一時期來到陜北采訪的外國記者都競相把丁玲作為報道對象: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人類的五分之一》、史沫特萊的《中國戰歌》、尼姆·韋爾斯的《續西行漫記》等,都生動記錄了丁玲的戰地生活和文學創作。而在抗戰勝利之際,丁玲抗戰時期的新作很快被譯成多種文字,成為各國讀者借以認識中國革命及革命文學的重要文本。
1944年,胡風在桂林選編出版了丁玲作品集《我在霞村的時候》,為丁玲作品集中外譯提供了便利。1945年,印度的Kutub出版社印行了此書英譯本,使丁玲的名字為南亞地區人民所知。
耐人尋味的是,在二戰戰敗國日本,丁玲也成為備受關注的作家。據已故東京大學教授丸山升考察,《我在霞村的時候》“是戰后日本翻譯中國抗戰時期文學作品最早的一篇”。譯文發表于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等創辦的《人間》雜志第2卷第1號(1947年1月),在目錄上和法國作家馬爾羅的小說《希望》并置于一欄。該刊同年第4號的卷首位置刊出4位外國作家的近照,分別是海明威、薩特、肖洛霍夫和丁玲,在明治維新后歐美文明深度浸透日本社會文化的背景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
這種變化的發生,緣自部分已經開始反省侵略戰爭的文學家。他們從丁玲的作品中感受到了近代以來備受帝國主義列強欺侮和蔑視的中國的堅強崛起和中國文學的煥然一新,戰后派作家武田泰淳感佩地寫道:“八年艱辛的戰爭,使中國作家們都在向前進步。家被燒毀,背井離鄉,失去親人,在東奔西走之間,被錘煉成銳利的刀鋒。”評論家小田切雄秀則從追問戰爭責任的角度解讀《我在霞村的時候》,認為“這篇小說是對日本人的一篇控訴書,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同時他也從書中女主人公的形象讀出了“一個人的倔強”和一個民族的“堅實底力”。作為戰后新一代學者的丸山升在東京大學選擇了丁玲作為畢業論文的課題,他更關注的是“作為知識階級出身”的丁玲如何“完成‘自我改造’而成為了‘人民作家’的代表”,當時的丸山因參加“五一”游行而被捕,他在獄中寫給大學研究室的信中說:“現在,我每天上午讀丁玲,下午讀《資本論》”。由此可以窺見丁玲在日本戰后進步青年中的影響。
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1951年度斯大林文藝獎,不僅使丁玲在社會主義陣營獲得巨大聲譽,也讓她在世界范圍內廣為人知。通過丁玲作品了解中國革命和革命后的中國,成為很多希望了解中國面貌的人們樂于采用的觀察路徑。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法國作家波伏瓦,這位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在東西方冷戰格局已然形成、新中國被封鎖圍堵時,為了了解中國的“真實面目”,于1955年9月和薩特一起訪問中國,考察了40多天,回國后又做了大量的文獻調查,兩年后出版了題名《長征》的“中國紀行”。《長征》包括了作者所觀察的中國社會的很多方面,從農民、家庭到工業、城市,宛如一部小型的中國百科,其中屢屢提到丁玲。在“前言”里,她說:“如果我沒有見過中國的農村和農民,我就不可能那么深刻地理解丁玲和周立波關于‘土地改革’的小說”。在“農民”章里,波伏瓦大量引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風驟雨》的情節,和她眼見的實際情況相互參照。波伏瓦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在農村的變革實踐更多地獲得了農民的信任和支持,有效推進了“社會主義和個人解放”的同步進行。這可謂是一個頗具洞見的觀察,而包括丁玲小說在內的中國新文學作品,為波伏瓦的觀察提供了資源和參照。
用行動回答世界文學重要命題
波伏瓦的《長征》當然談論到文學,其中“文化”章里的“文學”一節,幾乎是一部濃縮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波伏瓦以贊賞的語調談論丁玲的《桑干河上》,但也坦率地批評了小說結尾的簡單化處理。在討論到作家的主體經驗與文學寫作之關系時,她特別提到丁玲的文章《生活與創作》。針對丁玲提出的作家應該深入生活的呼吁,波伏瓦首先給予肯定,并認為丁玲本人“長期參加革命斗爭”,是“真的深入到了人民的生活當中”,但她對丁玲的經驗能否普遍適用不無擔憂,因為一般所謂的“深入生活”仍然是作家的由上而下,可能只停留在“了解情況”,而做不到從內心分享人民群眾的經驗,并將之內化為自己的體驗。波伏瓦認為丁玲的建議“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在實踐上太寬泛了”,在她看來,只有當“文化成為工人和農民熟悉的東西,語言不再使他們感到懼怕,那樣,他們就能真實地講述自己的生活了”。很顯然,波伏瓦期望的是真正“來自人民”的作家,是工人農民的直接述說和書寫。實際上,作家與人民的關系始終是世界文學所需要面對的課題。
在北京訪問期間,波伏瓦曾受到丁玲的家宴招待,但沒有就上述話題進行交流。丁玲一直沒有讀過《長征》。1983年,她訪問法國,老友重逢,波伏瓦也沒有重拾舊日話題。不過,從另外的角度看,丁玲1950年創辦并主持文學講習所,目標就是想讓“來自人民”的青年學會文學寫作。1958年到北大荒后,她盡心盡力地教農場女工識字,當然也是希望她們能夠學會自我表達。1979年復出文壇之后,丁玲最先寫出的作品是記敘農場女工的小說《杜晚香》,訪問法國期間,送給法國朋友的禮物也是這本小說的法文譯本。既幫助底層人民學習自我表述,也為底層人民代言,丁玲以這樣的行動,回應了波伏瓦的問題,也回應了同時代世界文學的前沿性課題。
(作者:王中忱,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本文配圖由中國現代文學館提供)
相關新聞
- 2021-06-23“閱讀蘭州”系列活動打造書香金城
- 2021-06-23“樂呵呵”幽默書店“靜悄悄”地開
- 2021-06-21展現豐碩成果《“一帶一路”建設案例研究》出版
- 2021-06-21新時代語言規范:穩定與發展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