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蕩:晚清二十年》:用理性與溫情走出悲憤、走近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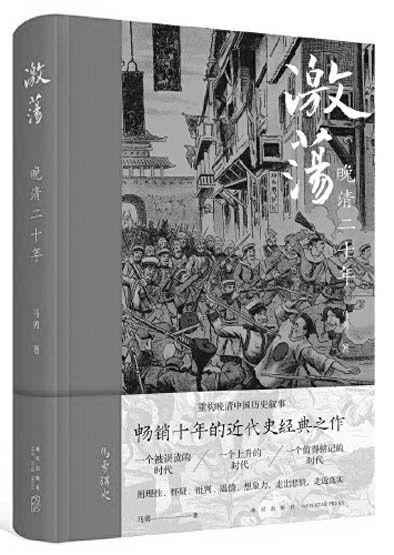
《激蕩:晚清二十年》/馬勇 著/新星出版社2021年出版
在《激蕩:晚清二十年》中,我想表達的意思非常簡單,就是我們能不能重構我們的晚清史。大致而言,幾十年前,當我們這一代學者還沒有出道時,我們的晚清史,不論中外,也不論兩岸,其實都是一個敘事模式,都是將晚清視為后世中國發展的拖累,是后世中國一切罪惡的根源。不論我們去讀臺灣學者的著述,還是去讀《劍橋中國晚清史》《哈佛中國史》《講談社中國史》,可以發現東西方學者的晚清敘事,都在強調晚清中國的悲劇意義。
就拿美國學術界來說,自費正清的“沖擊-反應”論,至其及門弟子、再傳弟子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以及“新清史”等各種各樣的新視角,其對晚清中國的整體觀感總體是負面的,帶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情緒。
對于這些中外前輩以及同輩時賢的研究,我始終心懷敬意,汲取甚多。只是我所接受的知識、信息,又讓我幾乎從一開始就不太認同傳統的晚清中國歷史敘事。我以為傳統敘事太過于悲傷了,這個敘事看到了晚清中國受到的傷害,但也極大低估了晚清中國的歷史進步,忽略了歷史主導者的話語。
不論是清帝國的自我歷史建構與描述,還是接替清帝國的中華民國早期對晚清中國的歷史敘事,并不是以悲情為主基調。民國初年的中國人對于走過的路固然有反省,有批評,但總體而言對于晚清中國幾十年特別是最后二十年的進步并不是完全抹殺,而是接續。就制度層面說,清帝國與中華民國固然是帝制與共和之別,但這個“別”用當時人的話說,是“國體變更”,是“君主立憲”與“人民立憲”的不同,并不是另起爐灶從頭開始。那時人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巨變”,用歷史研究者習于使用的話來說,是社會性質在這連為一體的幾十年發生了變化,而不是帝制結束之后的突變。
對于“三千年未有之巨變”的內涵與外延,中外學者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看法是要從兩個相互關聯的視角解析這個變化。第一個視角,是時代性質的突變,是一個時代的覺醒。
我們今天都知道,近代中國的全部問題均不來自于中國內部,中國經過先前幾千年的發展,在政治、社會、文化、教育諸方面,均獲得了長足進步,如果我們去讀大航海之后至十八世紀晚期長達三四百年間進入中國本土的那些域外有識之士的記錄,大有幾十年前福山所謂“歷史終結”的感覺。中國的政治架構,根據利瑪竇的觀察,大致實現了西哲“哲學家治理”之模式,君主、大臣,以及帝國全境的大小官員,個個接受良好教育,彬彬有禮,上馬打仗,下馬治國,公平正義得以彰顯,上下聲音的傳導反饋,更有機制性保障。即便是商業、貿易、城市生活,那時的中國,并不比東西洋落后。乾隆皇帝不愿向西人學習,他的自信有足夠的理由,僅僅是憑借巨大的貿易順差,他也有資格對強行入境貿易者說不。
但是,就在乾隆大帝對馬戛爾尼說不的時候,西方社會正在發生一場劃時代的革命,蒸汽機改變了世界,讓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被迫卷入工業化運動。那時的中國有足夠的貿易結余,乾隆皇帝那時如果答應了英國人的要求,與英國重構國家關系,打開國門,自由貿易,像英國一樣發展自己的工業化,那么十九世紀之后的中國史甚至世界史都會改寫。然而,聰明過人的乾隆大帝并沒有看到人類歷史的趨勢,不知道正在發生的工業革命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中國錯過了工業化的早班車,這一錯就是一百年,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才不得不開始自己的工業化。
一百年的錯失,讓中國后來的步履幾乎全亂。中國被迫開始自己的工業化之后,以為這個運動只是“堅船利炮”四個字,最多是“堅船利炮聲光電化”八個字。因而那時的中國拼命追趕,集中一切精力、一切資源發展自己的工業化。實事求是地說,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獲得了巨大成功,重工業、制造業、交通、通訊,以及城市化方面都有驕人進步。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已走出半個世紀以來的困境,甚至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已經在某些方面成為世界經濟一個重要因素。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讓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相形見絀,他們期望進入巨大的中國市場,但是他們的力量根本無法與清帝國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相抗衡。如果我們仔細閱讀甲午戰爭之前十年、二十年的中國外交史,就可以深切體會列強面對想象的中國市場,貪婪而又無奈。這時的西方外交官已經不再有威妥瑪、蒲安臣那一代人的想法,他們不是要引導中國走上世界,而是思考如何讓世界進入中國。
中國的大門沒有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而逐步打開,反而因中國實力增強而逐步關上。中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 這其實關系到我想說的第二個視角,也即傳統與現代。
十八世紀的中國沒有跟上工業化的節奏適時進入工業化時代,不僅錯失一百年,而且使中國人的心理發生微妙變化。當中國不得不開步走向工業化時,充分利用了“后發優勢”彎道超車。因而中國沒有西方工業化發展初期自然發生的思想啟蒙運動,沒有社會改造、階級重構,中國的工業獲得了巨大發展,但中國的社會其實還處于傳統時代,與現代社會并不吻合。于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在工業化發生初期格外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強調中國只是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而不是從制度、文化上重構中國。
假如不是甲午之役后一切歸零從頭開始,中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謙虛謹慎,增加向東西洋各國學習的力度、廣度,逐步從經濟增長擴展到教育重建、社會重構、軍事再造,甚至制度方面的適度調整,那么中國后來的道路肯定不一樣。
許多人會說,這是歷史的假設而不是歷史真實。其實,甲午后中國不就是沿著這些假設的路徑進行調整的嗎? 社會改造是一個整體工程,社會的進步必須拾階而進,整體推動,而不能想當然地實現優勢互補,不可能將馬的速度與牛的負重完美結合起來。
甲午戰爭后中國付出的慘痛代價無疑是后世中國人永遠不會忘懷的恥辱。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甲午一役終于讓中國人從酣睡中驚醒,終于明白什么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從此開始了自己的思想啟蒙運動、政治維新,新教育終于開始起步,新階級終于出現。中國的政治架構也必然會隨著這些新因素而逐步增加,逐步調整,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必然隨著這些新因素的添加而逐步變為事實。
這本書就是描述甲午前后至辛亥前后中國的變化,用“激蕩二十年”一語概括應該最為貼切。在經濟上,甲午前中國是最典型的國家統制型經濟模式,盡管開始了工業化、城市化,但這些幾乎與社會無關,“鹽鐵官營”在新經濟時代更進一步擴大了范圍,民間資本根本無法染指這些新經濟。但是,經過甲午之役,中國市場被打開了,不十年,在那些通商口岸上就形成了一個孱弱卻巨大的新階級,必須承認經濟基礎依然是社會變動的根本。
在文化教育、社會重建上,也無不如此。中國的新教育是維新時代第一主題,一個與世界一致的現代教育體制開啟了。傳媒業也是如此,至甲午,新聞紙不僅有了與東西洋相似的新聞體制,而且短短幾年,新聞成了一個行業,一大批人憑借著這個行業成名、就業、影響社會。
總而言之,晚清二十年是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起始階段,一個與傳統中國完全不一樣的新階段從這兒開始,中國終于開始從傳統、從農業文明中出走。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時代。(馬勇)
相關新聞
- 2022-02-25《西行悟道》:與文明對話 讓文化發光
- 2022-02-21茅獎作家張煒最新隨筆集解析“唐代五詩人”生命際遇
- 2022-02-18《人生能有幾回搏》出版
- 2022-02-18孫晶巖:用體育和文學與世界對話 講好中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