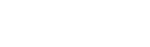如果用重量來衡量一首詩,那么格風的詩是有重量的,但他的語言是輕質的。輕中包含了重,或者說詩人在將時間或空間拉長延宕的過程中,將重量變得輕了。詩的語言非常干凈,他在詩的外在形式上追求“減量”,無不必要的詞語或是點綴物。詩人盡量以一種旁觀的角度,讓詩意“立”在那里,對于情感較為克制,常常有一種戛然而止的感覺,下筆利落。“手起刀落/無影無蹤”(《雪夜重讀水滸》),或者說,它往往帶給人的,是一種舉重若輕的印象。在現代詩詩壇當中,格風的詩保持著自我的鮮明風格。雖然語言極為簡單,卻為評論家留下足夠寬 敞的闡釋空間。
詩人對于聲音的敏感屹立于其它知覺之上。如《談論美好生活的時候》,詩人寫道:“我知道他們耳朵里塞著另一個人/另一只耳朵/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聽覺是支撐他回歸現實的一個震顫、敲擊。《在江心洲喝茶》的蛙鳴和鳥叫先是叫醒了一個早晨。接著是,藍色玻璃外的鐘聲驚動了正在喝茶的我們。抒情主人公的注意力是隨著聽覺的感應而轉換的。《天亮之前》中,杜鵑的啼鳴也是相對于雨的混沌狀的一個尖銳的存在,它是兀自切入到這個時空之中的。詩人對于聽覺有某種程度的依賴。加拿大學者梅巴爾·卡迪·基恩曾經提出:“耳朵可能比眼睛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對世界的認識,但感知的卻是同一個現實。具有不同感覺的優越性在于,它們可以互相幫助。”
將未知事物視覺化處理也是格風的一個特征,其中,《可是》一首非常典型。那是從一個關聯詞當中感知到的一切。他說“可是”當中有一個“霧蒙蒙的人”。“可是”當中包含了很多信息,可是這一個關聯詞里本身便包含了欲言又止的邏輯因素,而格風巧妙地將這一切視覺化了,有抽刀斷水的效果。對于事物的直觀把握,也體現出格風對自然天成的詩意生成方式的一種偏執:“脫口而出的鯨魚,找到了自己的語言。”(《魚腥草的味道》)
對于時間和位置的記憶總是在字里行間顯現。如《十朝公園》開頭就是“新年第三天”;《過年》當中一些確鑿的時間或是數字“現在是二〇一八/戊戌年正月初五”,時間像是某種刻度,對作者而言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又帶著點結繩記事的古老的傳統意味,透露出某種懷舊傾向。《永興島》當中,詩人不厭其煩地以經緯度來指代地點,“一架鋼琴停在大海中央”,以此形成的重復讓整個篇章具有了音樂性……
但與之相悖謬的是,格風對于事實常常呈現出一種遲疑的態度,他對記憶表示出含糊、不確切、不確信。這倒是很有趣——這一點似乎出賣了格風的一種認知態度,即真相永遠是無限逼近的、相對的,不存在一個百分百確證的事實,它似乎更像是一面之詞。他對陳詞表示一種存疑的、警覺的態度,這恰恰是對于真實的一種忠誠。沒有一種記憶可以真實地如監控器一般還原所有細節。(郭幸)
- 2022-05-06由《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一書想起的往事
- 2022-04-29讀散文集《黑夜之美》:在貼近土地中書寫生命體驗
- 2022-04-28在貼近土地中書寫生命體驗——讀散文集《黑夜之美》
- 2022-04-22對紅色精神的追尋與弘揚——評長篇小說《虎犢》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