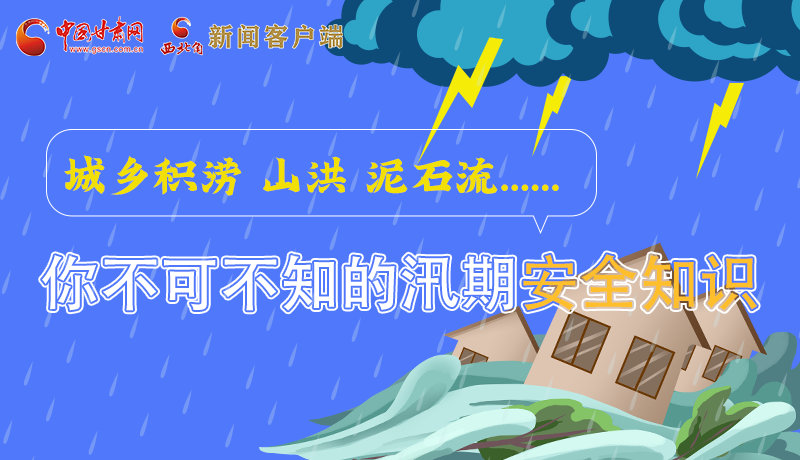80年代“魯迅傳”為何成為一道風景
魯迅是中國現當代作家中被立傳最多的人,同時也是近現代文化名人中被立傳最多的人。據多方搜集與統計:自20世紀20年代出現“魯迅傳”的雛形,到2021年1月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在生活·讀書·新知出版修訂版,近一個世紀出版各種由他者書寫的、成書意義上的“魯迅傳”已達300種之多。如此長的時間跨度和如此多的數量,成為中國現當代作家傳記文學史上最引人矚目的風景。
作為百年“魯迅傳”寫作的一個重要階段,20世紀80年代的“魯迅傳”一方面繼承、總結了以往寫作的經驗,預示了“魯迅傳”創作新時代的到來;一方面則以全新的觀念和文本的有效探索,為跨世紀“魯迅傳”的發展與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繼往”與“開來”的地位決定了研究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張立群,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島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中青年杰出學者。在近期舉行的2022中國小說論壇中,張立群以《一段“繼往”與“開來”的歷史——1980年代“魯迅傳”寫作論析》為題,作出闡釋——
“魯迅傳熱”生逢其時
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魯迅傳”共計43種。在“新時期文學”伊始,就有如此規模的“魯迅傳”出版,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魯迅傳”在20世紀80年代迅速發展首先與現代作家作品和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復興有關。隨著現代作家研究逐漸走向正常狀態、文獻資料發掘日漸豐厚,現代作家傳記作為現代文學研究之一,在學術研究的推動下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其次,思想解放、文藝政策的調整和改革開放的社會形勢,使文化界呈現繁榮的局面,出版業的發展、刊發傳記園地的出現,西方現代傳記作品和研究文章的引入,都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促進了現代作家傳記的創作。再次,現代作家傳記作為一種創作形式,同樣受文學創作整體發展形勢的影響,而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旗手,這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又在客觀上決定其是被立傳的最佳人選,這也是“魯迅傳”數量多、作傳者眾的重要原因。
此外,1981年正值魯迅誕辰一百周年,文化界圍繞魯迅誕辰百年開展各種紀念活動,“魯迅傳”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除了多部“魯迅傳”或是再版或是出版修訂版來呼應紀念活動之外,一批當時尚年輕的作者也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從曾慶瑞的《魯迅評傳》直接在正文之前的扉頁印有“謹以本書獻給偉大的文學家 偉大的思想家 偉大的革命家魯迅一百周年誕辰(1881.9.25—1981.9.25)”,到林非、劉再復的《魯迅傳》在“后記”中提到“謹以這本極不成熟的書,作為魯迅誕生一百周年的紀念”,以及陜西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于同期出版的同題為“魯迅研究叢書”中的傳記類著述,都說明歷史為“魯迅傳”提供了前所未有、生正逢時的契機。
“再版”與“修訂”一方面接續了20世紀40年代“魯迅傳”的創作史,一方面則是和20世紀80年代新生的“魯迅傳”一起構成寫作的“新起點”。應當說,對于20世紀80年代第一次書寫“魯迅傳”的作者而言,之前的“魯迅傳”既是其必要的參照,又是其渴望超越的對象。這種邏輯對于“再版”與“修訂”的前輩傳記家來說同樣適用。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的“魯迅傳”最致命的弱點是先驗設定,將魯迅局限于已有的歷史判定之中,以致以謳歌代替記述,以尊崇簡化歷史,這種以英雄、傳奇代替人物生平的做法自是極大限制了“魯迅傳”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的“魯迅傳”通過“再版”“修訂”與“重寫”適時推動了“魯迅傳”的書寫,提升了“魯迅傳”的水準,這不能不說是新的歷史機遇塑造了“新的起點”。
把“神化”的魯迅請回人間
“寫出我心中的魯迅”作為20世紀80年代魯迅研究界十分響亮的口號,在相當程度上激發了這一時期“魯迅傳”寫作者的熱情。“寫出我心中的魯迅”之所以令傳記寫作者追崇,是因為它在反思以往“魯迅傳”寫作模式中,抵達了傳記寫作的理想狀態:在充分掌握傳主已有材料的基礎上,融入了對傳主寫作的個性化體驗,從而實現了傳記寫作過程中客觀與主觀的統一。
顯然,即使面對相同的材料,由于傳記家個性及理解的差異,也會形成有多少寫作者就有多少本不同的“魯迅傳”的局面。“寫出我心中的魯迅”當然無法等同于寫出完美無缺的“魯迅傳”,因為任何一位寫作者在具體寫作、材料取舍、謀篇布局的過程中都會有自己的印記和局限,但“寫出我心中的魯迅”卻可以在最大限度發揮傳記家能動性的過程中,顯現當前這本傳記的藝術個性,符合人物傳記的寫作規律,從而向優秀的“魯迅傳”行進。
20世紀80年代的“魯迅傳”就篇幅上說,相對于以往有顯著的增加:無論是再版修訂,還是新生的文本,史料的發掘、整理與日趨豐富自是一個重要因素,但與之相比,刻畫更為完整、真實的魯迅形象以“寫出我心中的魯迅”顯然更具目的性。
以林志浩的《魯迅傳》為例:“忽略雜文,對共產主義者的魯迅缺乏足夠的描述和評論,這幾乎成了魯迅傳記寫作中的慣例。我私自以為,這似乎不是一般的問題,而是關系到能否真正表現魯迅偉大人格的大問題。”正是看到了以往傳記的不足,林志浩的《魯迅傳》才有意加重了魯迅后期部分寫作的分量:他的《魯迅傳》分三編、共27章,“第三編1927—1936”共14章,從篇幅來看超過全書的一半以上。不僅如此,他還有針對性地加強了對魯迅雜文作品的分析,從而在填補以往“魯迅傳”寫作不足的過程中凸顯了自己作品的特色。
形式、手法“百花齊放”
僅從書名上看,20世紀80年代的“魯迅傳”已包括“正傳”“評傳”“故事”“畫傳”“印象記”等形式,這種表面上籠統的區分方式,結合具體文本還可以進一步劃分:如郭同文編著的《魯迅青少年時代的故事》、何啟治的《少年魯迅的故事》等,就因為只描寫了魯迅生平的一個階段而成為具有“階段性”或曰“半部書”性質的傳記(即敘述傳主部分生平);而像羅慧生的《魯迅與許壽裳》、范志亭的《魯迅與許廣平》等,則可以列入“關系式”的傳記;此外,還有像李霽野的《魯迅先生與未名社》這樣難以歸類、但又對傳記研究本身提出特別案例的文本等。值得補充的是,“連環畫”也豐富了“魯迅傳”的書寫。“連環畫”雖圖文并茂、文字內容不多,但與人物傳記在敘述上沒有區別。20世紀80年代魯迅的“連環畫”主要包括黃侯興的《魯迅的青少年時代》等。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位作家傳記形式的多樣,可以理解為其傳記寫作已進入繁榮的階段。“魯迅傳”在20世紀80年代現代文學研究復興期就取得如此成就,預示了其不斷走向成熟的未來。當然,在形式多樣化的同時,手法也必將相應地豐富起來進而適應于形式、作用于結構。
在曾慶瑞的《魯迅評傳》中,著者寫到“本書不是傳記文學,也不是理論著作,而是帶有較為濃厚的評論色彩的人物傳記。不同于舊有的一種‘評傳’的是,拙著不是‘傳記’加‘評論’的截然兩部分,而是寓評于傳,傳、評結合,追求題材的連貫性,結構的完整性。”
與之相比,林賢治的《人間魯迅》則呈現了另一種圖景。《人間魯迅》分為三部,分別有17萬字、30萬字、30萬字,第三部雖于1990年5月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第1版,但就其寫作時間,顯然在20世紀80年代。在“魯迅傳”剛剛起步、初現繁榮的年代,林賢治便以“三部曲”的形式書寫魯迅,自是深入理解傳主并攢足了力氣,并開創了“魯迅傳”系列寫作之先河,由此成為20世紀200余部“魯迅傳”中最長的一部。
另外,《人間魯迅》第一部“勒口”的“內容說明”也提及“歷史哲學的高度”“散文的抒情筆調”。仔細閱讀全書,不難發現作者在“散文的抒情筆調”之外,還運用了大量的議論、描寫、分析和詩性的筆法,力求在展現魯迅生平各個階段、生命各個方面的過程中深入內心世界,揭示其心路歷程。在和張夢陽的通信中,林賢治曾不無動情地表示想寫出一點關于魯迅的“本質的東西”即“魯迅的獨立的哲學品格”。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是林賢治詩人兼文化學者的身份決定其采用了文學的筆法,不如說他是期待以文學的筆法呈現更為生動、真實的魯迅。
80年代“魯迅傳”的得與失
任何一個時代的傳記書寫都擺脫不了這一時代賦予它的權利,同時也必然呈現相應的限度。20世紀80年代“魯迅傳”在取得突出成就之余,也存有一些不足,這些可以稱之為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以凝結和留存的方式見證并影響著“魯迅傳”的創作史。
從問題方面上看,20世紀80年代的“魯迅傳”書寫必然帶有轉折年代的痕跡。從沿革流傳的角度,20世紀80年代的“魯迅傳”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還無法完全擺脫之前年代的印記:“左”的痕跡。這會在不同程度上削弱“魯迅傳”的真實性和歷史價值。
與魯迅有過交往的現代作家、報人曹聚仁曾認為,為魯迅作傳的人應當與魯迅結識。他的看法從當代人寫當代人的角度上說,自有其道理,但從為歷史人物立傳的角度說,卻未必符合實際。在充分掌握史料、深入理解傳主和具備高超文學性的前提下,后人同樣會寫出優秀的“魯迅傳”。只是在此過程中,傳記家應當先成為一個優秀的歷史方面的學者,而后還要成為一個優秀的文學寫作者,并最終在傳記文本中彰顯自己的“德、才、識、力”。結合20世紀80年代“魯迅傳”具體文本,林非結合自己《魯迅傳》寫作提出的“素樸而又高峻”;陳漱渝在《民族魂》中所言的“要在選材上做到‘博學約取,厚積薄發’,在語言上做到‘文華而不失實’,似乎也多少要有些功力”,都是值得借鑒的經驗。
20世紀80年代“魯迅傳”寫作方面積累的經驗還有很多。比如,何啟治的《少年魯迅的故事》涉及現代作家傳記的閱讀與接受的問題。單演義的《魯迅在西安》,朱忞、謝德銑、王德林、裘士雄編著的《魯迅在紹興》等敘述形式較為特殊的文本,則涉及對傳記本質和范疇的理解,在實踐層面上豐富“魯迅傳”寫作與研究的同時也豐富了傳記的寫作與研究。還有一些院校編輯的收錄魯迅生平的“內部資料”,它們的存在豐富了“魯迅傳”的認知域。
總之,20世紀80年代的“魯迅傳”是一個具有起點意義的獨特存在。20世紀80年代“魯迅傳”不僅在超越以往寫作過程中,進入到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而且還以其蓬勃發展的態勢開啟了20世紀90年代“魯迅傳”的書寫,并為“魯迅傳”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多樣化的寫作經驗與物質基礎。
本報記者 李夢馨 本報實習生 王冉
- 2022-07-20納格拉洞藏文古籍保護項目在云南迪慶掛牌
- 2022-07-20瞭望 | 鄉村木匠辦書屋19年,他說:“農民渴望知識”
- 2022-07-20戈壁小城里的“文化驛站”
- 2022-07-18王安憶:熱眼看自己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