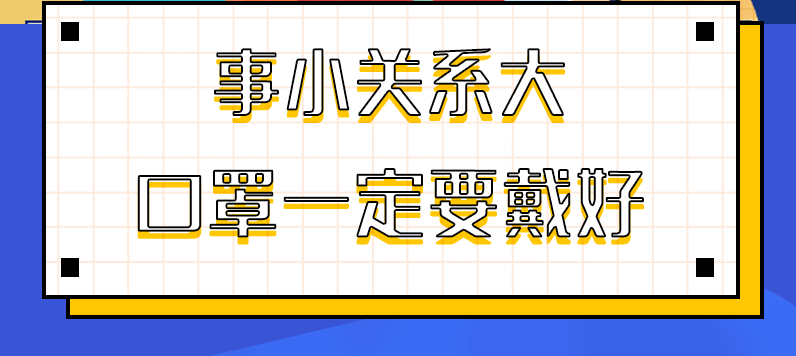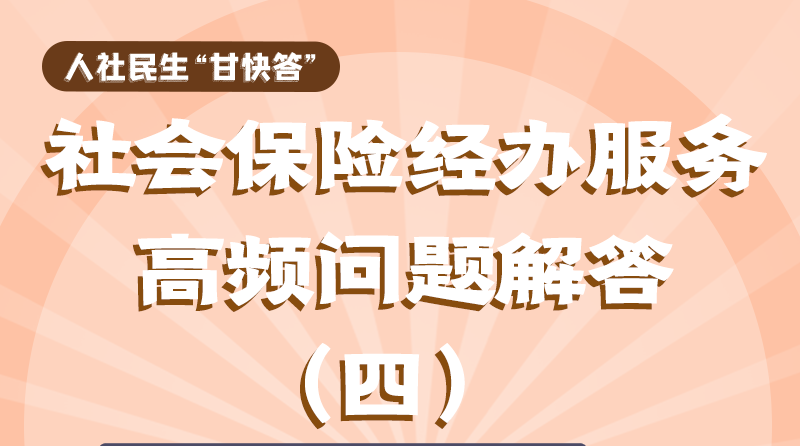富有傳統(tǒng)底色的沉穩(wěn)之氣——讀長(zhǎng)篇小說(shuō)《銅行里》
【奮進(jìn)新征程 建功新時(shí)代·好書薦讀·文學(xué)】
富有傳統(tǒng)底色的沉穩(wěn)之氣
——讀長(zhǎng)篇小說(shuō)《銅行里》
作者:周榮(遼寧文學(xué)院副院長(zhǎng),本文系遼寧省文聯(lián)2022年度文藝評(píng)論重點(diǎn)課題“遼寧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創(chuàng)作研究”〔LWL202214〕研究成果)
從文學(xué)履歷上看,作家老藤屬于一開始寫作便有著明晰而堅(jiān)定的文學(xué)理念和美學(xué)追求的作家。新時(shí)期以來(lái),各種文學(xué)潮流翻新更迭,閱讀趣味的個(gè)性化和文學(xué)生態(tài)的多樣性,構(gòu)成了當(dāng)代文學(xué)燦然而斑駁的文學(xué)景觀。“變”成為常態(tài)。而老藤篤定地沿著經(jīng)典現(xiàn)實(shí)主義一脈寫下來(lái),耐心地用扎實(shí)、干凈的筆法狀寫腳下的大地、身處其中的生活,把那些目光所及的面容和風(fēng)景妥帖地安放在一個(gè)個(gè)樸素、豐盈、好看的故事之中,而雅正蘊(yùn)藉的中國(guó)傳統(tǒng)美學(xué)也就隱身在文字的行間與故事的縫隙之中。

老藤的小說(shuō)傾心于建構(gòu)一個(gè)明亮、清正、善意的文本世界。大興安嶺之蒼茫遼闊、納謨爾河濕地的旖旎風(fēng)光、街邊攤上的雞架杏仁粥……都被那個(gè)文學(xué)信仰照亮而熠熠生輝,又在充實(shí)、延伸著那個(gè)明亮的文本世界。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小說(shuō)中的人物在世事變化中堅(jiān)守、承續(xù)著恒久的精神與信仰。老藤的小說(shuō),每一部單獨(dú)看是“獨(dú)特的這一個(gè)”,放在一起又是彼此照應(yīng)、彼此照亮的“互文本”組合,共同指向明亮之所在。這也是老藤小說(shuō)抵達(dá)“無(wú)窮的遠(yuǎn)方,無(wú)數(shù)的人們”的方式。
將長(zhǎng)篇小說(shuō)《銅行里》(作家出版社、沈陽(yáng)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置于老藤的文學(xué)履歷中不難發(fā)現(xiàn),這部作品延續(xù)了他小說(shuō)注重故事性、文化底蘊(yùn)厚重、善用傳統(tǒng)意象等共性特質(zhì),又在鉤沉城市歷史、挖掘傳統(tǒng)文化精神等方面進(jìn)行著新的拓展與嘗試。老藤的小說(shuō)與他切身的生活經(jīng)歷關(guān)聯(lián)密切,即使是行使小說(shuō)天然的虛構(gòu)權(quán)利,也嚴(yán)謹(jǐn)?shù)刈裱?xì)節(jié)真實(shí)的規(guī)則,這也構(gòu)成其創(chuàng)作鮮明的在地性與及物性。《銅行里》是對(duì)他工作多年的沈陽(yáng)近代城市歷史的全景掃描。作品取材自始建于清朝皇太極年間的銅行胡同,以銅行胡同里富發(fā)誠(chéng)石家、永和興唐家、永昌號(hào)令狐家的興衰與傳承為主線,敘寫了與銅器、銅行胡同相關(guān)的一百個(gè)人跌宕起伏的命運(yùn),在銅行變遷與個(gè)體命運(yùn)的交織中折射出沈陽(yáng)城的百年沉浮與文化底蘊(yùn)。小說(shuō)敘事時(shí)間跨越百年,中華民族百年的滄桑巨變濃縮于一條胡同的迎來(lái)送往、煙火生活中。
《銅行里》最吸引我的還不是眾多的人物和曲折的故事,而是氣場(chǎng)。小說(shuō)通篇散發(fā)著一種處變不驚的沉穩(wěn)之氣。近代百年風(fēng)云際會(huì),在大歷史帷幕下,銅行胡同也歷經(jīng)磨難,但始終不慌不亂,平日里本本分分,不顯山不露水,專研手藝做好買賣;動(dòng)蕩時(shí)毫不含糊,披甲執(zhí)刀走到歷史前臺(tái),舍家為國(guó)在所不惜。這股沉穩(wěn)之氣的底色是小說(shuō)中歷代銅匠口口相傳并親身踐行的“具銅心、辨銅氣、結(jié)銅緣”。這是傳統(tǒng)的行業(yè)規(guī)矩,塑造了一代代銅匠的忠誠(chéng)、仁義與敬業(yè),也是一種穩(wěn)定的文化秩序,是銅行胡同作為最小的“想象的共同體”的文化認(rèn)同根基,更是傳統(tǒng)道德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某種意義上,《銅行里》是胡同小歷史與民族大歷史的一次不期而遇的碰撞,也是傳統(tǒng)人文精神與現(xiàn)代文明意識(shí)的對(duì)話。
文學(xué)在虛實(shí)之間塑造著人們的記憶與想象,為讀者提供了在虛構(gòu)與現(xiàn)實(shí)之間參差對(duì)照、品讀城市的空間。比如,作家陸文夫的中篇小說(shuō)《美食家》中蘇州是否合乎真實(sh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當(dāng)書頁(yè)翻飛、口舌生津之時(shí),蘇州已經(jīng)以色香味的形式沁入了讀者的心脾。雖然銅器已經(jīng)逐漸退出了當(dāng)下的日常生活,但《銅行里》中那些關(guān)于銅器分類、制法、工藝、用途的細(xì)膩描寫,已轉(zhuǎn)化為情感記憶滲透在城市的文化肌理中,豐盈著城市的靈魂。琳瑯滿目的銅器是城市的美學(xué)肉身,那些縈繞在文本中的氤氳銅氣,從歷史深處發(fā)散出的灼灼銅光,猶如一個(gè)復(fù)古濾鏡,為這座硬朗的工業(yè)城市打上了懷舊的柔光。《銅行里》用銅器激活了沈陽(yáng)工業(yè)文化傳統(tǒng),也盤活了沈陽(yáng)地圖,從西瓦窯的古井開始,途經(jīng)八卦街的回形樓、北市場(chǎng)的春餅店、北塔的法輪寺,沿著四平街、艷粉街、小北關(guān)街,過(guò)德勝門、來(lái)穎胡同,最后回到沈陽(yáng)故宮北側(cè)那條“長(zhǎng)二百步,寬六步,北端接四平街,南端連著供奉關(guān)帝的中心廟”的銅行胡同。作者把這些古老的地標(biāo)和街道集合起來(lái),不動(dòng)聲色地安置在故事中,順便把沿途的歷史、風(fēng)景與記憶編織起來(lái),在銅行叮叮當(dāng)當(dāng)?shù)膭谧髦袉拘炎x者的記憶。讀者也跟隨書中的路標(biāo),躬身入局,漫步在這座城市的文學(xué)地圖中,感受北方一覽無(wú)余的豁達(dá)與剛烈。
《銅行里》敘事上借鑒了古典小說(shuō)的技法。小說(shuō)以“楔子”開篇,“楔子”只有短短三頁(yè),不僅快速交代了銅行胡同的歷史起源與傳承延續(xù),更以不容置疑的方式確立了銅行胡同的商業(yè)道德、精神信仰與倫理秩序。小說(shuō)后面的各章都是對(duì)“楔子”的闡釋與印證。正文部分以父子對(duì)話的形式展開,父親石國(guó)卿給兒子石洪祥講述與銅行胡同有關(guān)九十八個(gè)人的故事,構(gòu)成了小說(shuō)的主體框架。父親承擔(dān)了“講故事的人”的角色,兒子是“聽故事的人”。在本雅明看來(lái),“講故事是最古老的傳播方式”。他認(rèn)為,在席勒所言的“樸素的詩(shī)”的時(shí)代,講故事的人通過(guò)不斷的復(fù)述,呈現(xiàn)出自己所理解的世界,“講故事是把故事融入講故事人的生活之中,從而把故事當(dāng)作經(jīng)驗(yàn)傳遞給聽故事的人”。講述的故事既代表了講述者的時(shí)代想象,也滿足了接受者的心理期待,從而構(gòu)成一種敘事共同體,共同承載一個(gè)群體的情緒與記憶。因此,無(wú)論是“楔子”所確定的小說(shuō)主旨,還是一代代口口相傳的“具銅心、辨銅氣、結(jié)銅緣”,以及從九十八人的軟銅冊(cè)到湊齊一百人的銅匠浮雕墻過(guò)程中的增補(bǔ),一方面,在集體接力的傳承中,普通人的世俗經(jīng)驗(yàn)與道德諷喻被有效地固定下來(lái),普通人的故事被賦予本雅明意義上的“光暈”,進(jìn)入歷史敘事;另一方面,普通人獲得了講故事的權(quán)利,帶領(lǐng)聽故事的人和讀者一起,塑造歷史,也重審自身。
- 2022-10-31亙古放翁的隔世知音
- 2022-10-28《下莊村的道路》: 為“當(dāng)代愚公”毛相林畫像
- 2022-10-28為百年文學(xué)史中的“北京”留影——讀《散文中的北京》
- 2022-10-27紅軍長(zhǎng)征“走夜路有了‘燈籠’”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guó)甘肅網(wǎng)微信
中國(guó)甘肅網(wǎng)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xué)習(xí)強(qiáng)國(guó)
學(xué)習(xí)強(qiáng)國(guó) 今日頭條號(hào)
今日頭條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