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文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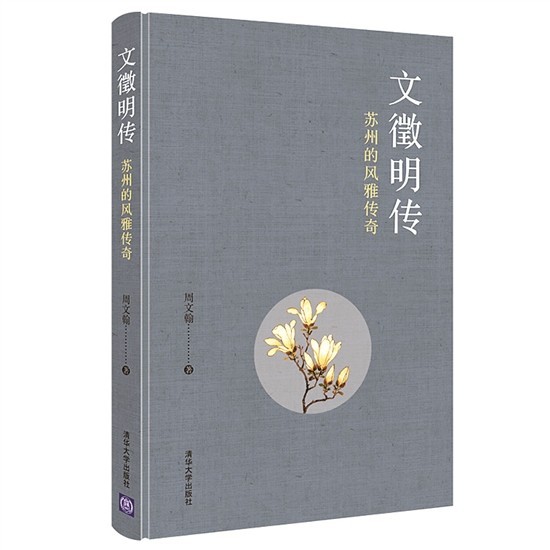

文/羊城晚報記者 吳小攀
古代文化名人傳記一直備受熱捧,一些不太受重視或有“歧見”的書畫藝術大家的傳記近些年來也開始走紅,作家、藝術評論家周文翰一直潛心于相關創作,繼出版文徵明、趙孟頫傳記后,黃公望、倪瓚、王羲之、蘇軾、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傳記也將陸續推出。關于古代藝術家傳記的寫作有何體會?對當下的美術創作有何觀感?日前周文翰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
文化上的“思鄉病”促成寫作
羊城晚報:為什么會選擇這些古代的藝術家寫傳記?
周文翰:二十年前我大學畢業,最開始關注的是當代藝術和創意文化。2002到2008年我在北京當記者,主要報道當代藝術和文化,之后辭職去印度、西班牙等地旅行,旅行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對古典藝術、對日常生活所見的動植物這些主題產生濃厚興趣,興趣轉移到藝術史、博物學上。
可能是在異國他鄉有了文化上的“思鄉病”,也可能是對當代藝術的“轉瞬即逝”“好奇求異”感到迷茫,我反而開始對似乎是“陳跡”的古典文化有了濃厚的興趣,從那時候起開始寫作《中國藝術收藏史》。在寫作中發現,趙孟頫、文徵明、王羲之等雖然名字為眾人所知,但是大家對他們的人生、性情并不了解,他們的形象是模模糊糊的,對今天的人來說,他們是“著名的空心人”。既然如此,我就決定自己來寫他們,這一寫就持續了十四年,對我來說,寫作古代藝術家傳記的最大動力就是希望能讓這些古人“活起來”。
羊城晚報:已經寫了哪些人?
周文翰:我喜歡同時寫好幾部書稿,有的寫得快些,有的寫得慢些,也有的寫著寫著就“爛尾”了,第一批寫的是文徵明、趙孟頫、蘇軾三個人,前兩本已經出版,后一本《孤星之旅:蘇東坡傳》年底應該能出來。第二批寫的是“揚州八怪”、王羲之,前者是因為我對揚州一直有些迷戀,想從揚州的城市變遷角度寫揚州八怪,后者是因為寫了前面三位書畫家,有一段時間對書法突然很感興趣,就追溯源頭,寫起了王羲之,明年應該能出來。還有幾本都已寫完初稿但還想打磨一下,有黃公望、倪瓚,李白、杜甫、白居易,基本上都是在寫一個人的過程中,突然因為某個細節、某句話對另一個人產生了興趣,轉而就寫其他人,如此就越寫越多。
羊城晚報:這些人有什么共同點?
周文翰:研究和寫作這些藝術家、文人的傳記之后,最大的感想是“龍有龍道,蛇有蛇道”,刺猬、狐貍各有歸宿,每個藝術家的天賦、性格、背景都不同,他們有各自的成長之旅,成名之路。總的來說,這些藝術家絕大多數都是士人、官員,這是他們的核心身份,書法、 繪畫是他們的“業余才藝”。而吳道子、黃公望兩個人身份特殊點,吳道子是畫師出身,最初的身份是比較低微的,黃公望則是吏員、道士,打交道的也主要是低層人士。
最困難的是“帶著同感理解古人”
羊城晚報:寫古人傳記要達到怎樣的效果,有沒有給自己設定目標?
周文翰:我寫傳記是希望寫出活的人,同時寫出真實的時代氛圍、文化生態,我自己覺得在史料辨析、整體信息的傳達上應該都達標了,但是在古代人物傳記的“體式”或者說寫作技巧方面還在持續探索。比如,第一本《文徵明傳:蘇州的風雅傳奇》努力想要掙脫“評傳體”,但難免還保留了許多“評論腔”;第二本《不浪漫:趙孟頫傳》的評論腔就少了很多,基本是按照傳主的視覺、聽覺展開敘述,在摸索如何處理史實方面的“硬信息”和個人感知的經驗“軟信息”的比率,即將要出的蘇東坡的傳記可能會更加平衡。
羊城晚報:寫古人最困難的是什么?如何把握虛構和非虛構的分寸?
周文翰:最困難的是“帶著同感理解古人”,即所謂“理解之同情”吧。今天的人因為看影視劇比較多,影視劇是快節奏、強沖突的模式,而實際上古代人對時間的感知、對空間的感知、禮俗細節等等都與當代人有巨大的差別,比如古代人騎馬、乘船,一天經常只能走四五十里,而今天的人乘坐飛機、高鐵、汽車,一天能走上千公里。我在寫作中是比較強調“視覺性”和“空間感”的,目前寫的藝術家傳記都是嚴格根據史料來寫的,沒有任何虛構的成分。
說到虛構,《吳道子傳》這本書最讓我為難,因為唐人關于吳道子的記述總共就一兩千字,而且幾乎都是關于他在寺觀的畫作的簡略記述,因此想寫出他的“嚴肅傳記”是不可能的,要寫他的傳記的話只能加入“虛構”才能勉強湊出他的“人生”及其畫面感,可是,如何“虛構”?如何把史料、信息與虛構結合?這讓我挺猶豫的,寫了近二十萬字的草稿但是一直拖延、猶豫,中間停下來又去寫了李白、杜甫,因為他們三人生活在同一個時代,而且李白和吳道子都是翰林待詔,肯定在辦公的院子、酒宴上寒暄過。
中國藝術“地位”隨中國發展“水漲船高”
羊城晚報:近些年來有些藝術史家如高居翰、巫鴻等人從海外的視角,撰寫了一些有關中國藝術史著作,您如何評價?
周文翰:他們因為是學者,基本是按照學術規范來寫作的,許多具體的觀點挺有意思和啟發。我不認為西方人解讀中國藝術就會“隔”,因為中國古代文化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了“專門知識”,無論中國人、外國人,想要嚴肅研究古代藝術都需要長期的學習和積累,都要慢慢摸索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寫作方法,所以好的研究者肯定是“爭奇斗艷”,無所謂“隔”不“隔”,最多是理解不同而已。
羊城晚報:包括畢加索、塞尚、凡·高、高更等人多少都受到中國傳統美術的影響,但之前似乎并沒有引起足夠關注,是不是需要更充分地評價中國美術在世界美術史中的地位?
周文翰:在我看來,這很大程度上不僅僅與作家、學者的寫作、倡導有關,其實與中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有關,比如現在很多歐美藝術家愿意承認中國經歷、中國藝術對他們的刺激或者影響,這是因為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文化的影響自然就大了許多。隨著國內大學的擴張和研究競爭的激烈化,對中國藝術的研究還處于增加的階段,我相信如果持續下去,包括與海外的出版界、新媒體增加交流的話,會促進外界或者說外國人對中國藝術的理解,如此中國藝術的“地位”自然會“水漲船高”,你本身成為一個強勢的存在,自然會吸引別人的關注、研究、傳播。
藝術價值“共識”隨著時代演變
羊城晚報:從古代藝術家的生平里,您認為最值得當下藝術家借鑒的是什么?
周文翰:古代和現代最大的不同是,書法、繪畫這類才藝是古代士人的業余技能,他們的主業其實是當官,其次是詩文,書法、繪畫是排在后面的;不像現在,書法家、畫家都是光明正大的職業,而且當代藝術家可以利用公共博物館、互聯網開放資源學習甚至開展商業,可以嘗試的藝術風格、商業渠道都比古代藝術家豐富得多,所以我覺得當代藝術家沒什么可羨慕古代的。能借鑒的,可能是他們的一些圖式、理論之類,但是在人生方面其實沒有什么可比性。趙孟頫、文徵明都是謹小慎微、溫和平潤之人,蘇軾既能寫文章,也會講段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苦難能出詩人,幸福也能出詩人,不是絕對的。
羊城晚報:您認為當下藝術家在繼承本土傳統與向西方學習之間,哪個更重要?
周文翰:我覺得21世紀的藝術家的基本境況是:一個人面對著數千年來的、全球的所有視覺文化遺產和圖像,眼花繚亂,這時候很難說是面向本土或西方學習什么,因為可供學習的知識、圖像實在太多太豐富了,最多挑選幾個細小的方向深入探究,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細分的愛好、方向,實際上一個人只能向幾個古人學習、致敬,類似一個個的小社群,不是以東西方劃分,而是以更細微的趣味劃分。在此中“平衡”對當代人來說難度太高,還不如癡迷一兩樣東西好。
羊城晚報:在這樣一個全民都畫的時代,如何判斷一幅畫的藝術價值?
周文翰:這是我在《中國藝術收藏史》中研究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一幅畫的藝術價值是各種利益、觀念的互動形成的“共識”,具體每一件作品的“共識”都有差別,有的市場價格的高低是主因,有的皇家收藏履歷是主因,有的創作者自帶“名人光環”是主因,各不相同,很難給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答案,而且這種“共識”也會隨著時代演變。
- 2022-11-07深港兩地開啟第二十三屆深圳讀書月文化交流之旅
- 2022-11-072022海峽兩岸青年閱讀季在廈門舉辦
- 2022-11-07烏茲別克斯坦國家圖書館“中國之窗”閱覽廳揭幕
- 2022-11-07擁抱時代生活 鑄就文學高峰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