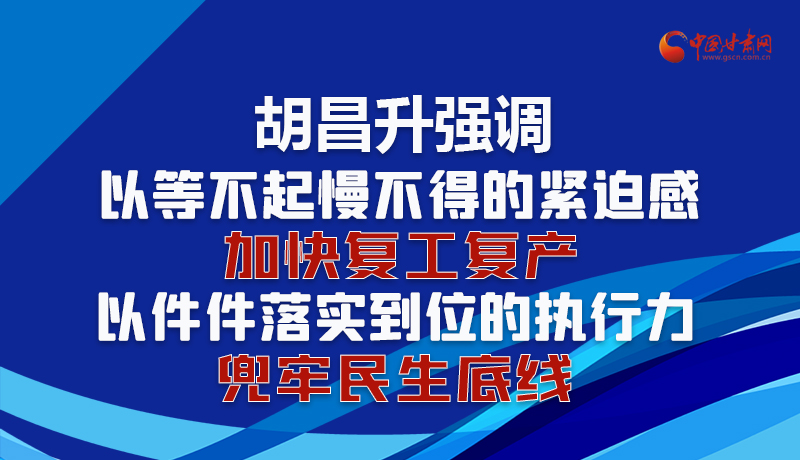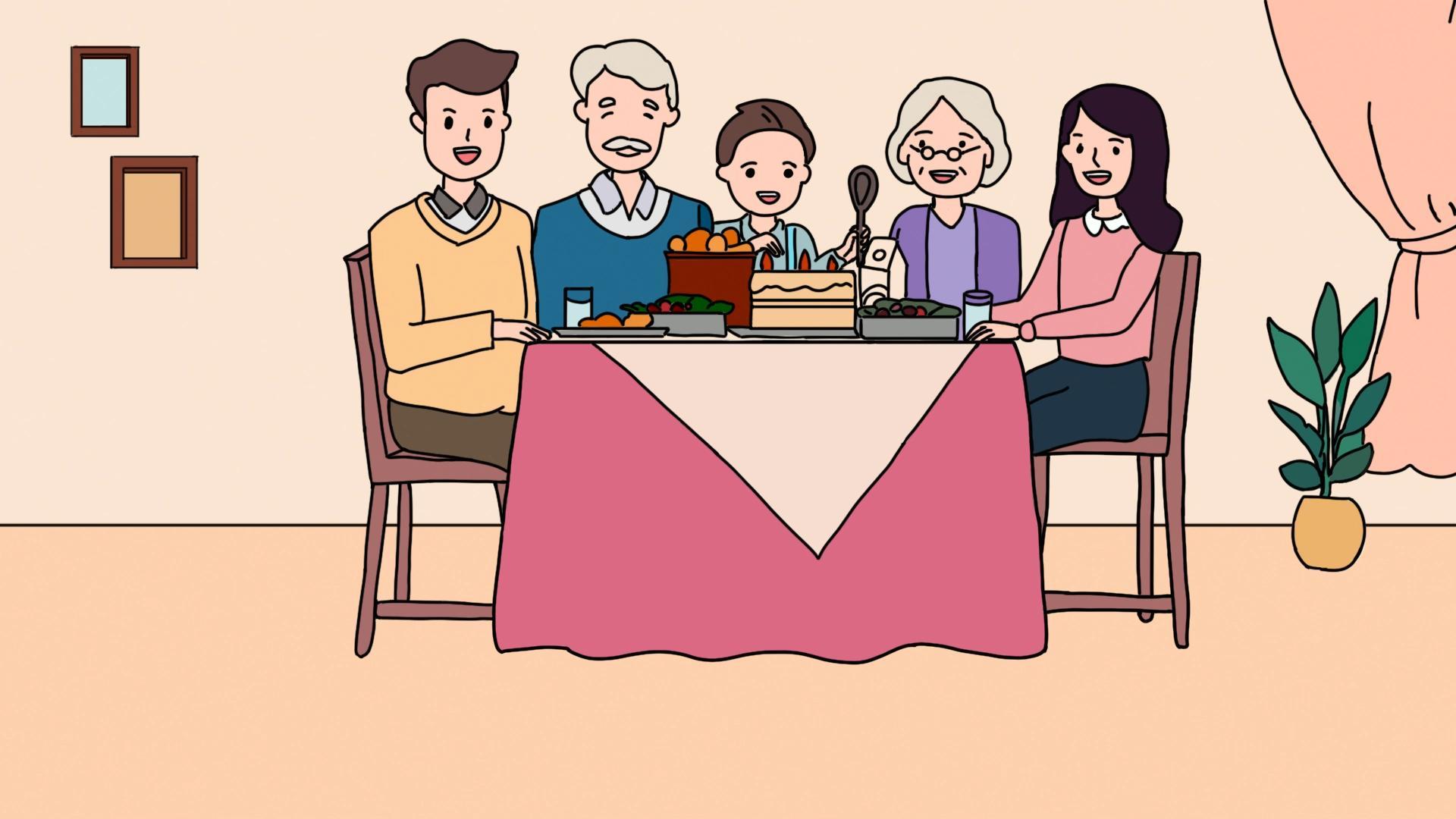《詩經》所載樂歌,本為兩周禮儀的用樂與歌舞的歌詞,要對其詩義進行清晰的解讀,需要回到歷史現場,結合兩周禮樂制度,從禮義、樂義對其施用場景進行還原,方才能夠理解詩之本義。受長期的經學闡釋遮蔽,《詩經》中諸多詩篇的禮義、樂義被曲解,這就需要跳出傳統的經學解讀,從文字訓詁、禮樂制度、歷史事件等角度對其進行詩義重詁。
《詩經》解讀的困境
《詩經》難解,一在于斷章取義,孔子所謂的“不學《詩》,無以言”,可知春秋學者稱引賦詩,各取所需而望文生義,使得詩之原初義漸遠而文本義得以強化。孟子時詩之原初義漸以失傳,其只能“以意逆志”推論之。荀子的引詩證言,將斷章取義從外交場合的交流意會轉化為學術論著中的引經據典,斷章所取之義,便脫離了詩作為樂歌、用于禮儀的原初意義,而成為僅剩下道德賦能、語言賦義的文本形態。其文本義隨引用者的理解而隨意游移。二在于漢儒經解。兩漢經學的最大功能,不是求其真論其實,而是借助前代經典形成一套理論體系,為漢王朝的國家治理提供學理支撐。以《禹貢》治河,借助歷史經驗管理水道;以《洪范》察變,形成五行學說確定天人秩序;以《春秋》決獄,建構歷史價值觀用以評騭行政得失,三者皆直面客觀現實而能夠引證。而以三百篇為諫書,在賦予了《詩》的政治經典性地位的同時,也使得《詩》失去了求真求實的必然性,與時俱進地跟著政治學說在不斷調整,從辨風知政、補察民情的王道之作被解讀為言頌美先王、諷刺昏庸的衽席之說。今傳毛詩的立意,便是尋求詩篇的施用功能,將之確定為美或刺,并將之系于時世,既作為解讀的條件,又為用詩者提供一個按圖索驥的內在依據,鄭箋、孔疏循毛詩而下,其不僅固化了漢儒的闡釋,而且以經學的形態強化了《詩經》解讀的穩定性。
宋儒最能體會漢儒借助經典穩定世道、引導人心的用意,但其不能不面對唐以詩賦取士、宋以策論科考的新需求。漢王朝奉若神明高高在上的經典文本,其知識體系及其學說已經在史學、子學、玄學、釋道的傳承之中被重構、被闡釋,漢儒在五經中寄托的政治理想、價值認同、制度建構以及文本闡釋已經無法面對近世的讀書人,更無力像漢代那樣作為經驗提供給帝國用于國家治理。宋代的疑經風氣,與其說是對漢儒解經的反思,毋寧說是宋儒對經學傳統的自救。他們是在維持經學地位的前提下,對漢儒的不合理的闡釋進行必要的補充、修改、發明或者完善。朱熹《詩集傳》中對漢儒曲解之詩有所解放,但對“鄭衛之詩”要比漢儒更加深惡痛絕。宋儒改良式的解經,是對漢儒經說的修訂,其所打開的門徑,卻成為明清懷疑、放棄《詩經》經解并自立新說的坦途。
這一坦途解放了《詩經》,使得原本被誤解被曲解的詩作,可以去除外部的捆綁而活潑存在;但卻無意中將之引向了望文生義的歧途,即不再關注時世背景、制度形態、禮樂用義而直接解讀,或徑將之作為民歌,或多言男歡女愛,或常為階級斗爭,《詩經》剛從經學清規戒律的桎梏中解脫出來,便又進入到隨心所欲的闡釋之中。董仲舒時代因“詩無達詁”而逐漸建立起來的經解,給《詩經》一個方向性、規定性的解讀,使得《詩經》成為一個超穩定的學理形態,給此后的詩學提供了詩學肌理和敘述樣板。但后經學時代,研究者或以經說為本,在傳統的說解之中顧盼自如,或棄經解于不顧,在文本表層感悟生發。此兩途,自宋儒以來便日漸分道揚鑣,至今仍為余風日熾,未能代雄。其關鍵在于歷代解《詩》皆從經入,學者不讀經說,常被疑為無學。經解歷經兩千年的千錘百煉,無數學者皓首窮經以為說解,其闡釋自洽,訓詁周圓,讀多了則習慣性順從。故研究《詩經》者離開經解便茫然若失憑據,閱讀《詩經》者則棄其舊說,以己度人,以今例古《詩經》注釋層出不窮,詩義闡釋更加莫衷一是。
要想在經學闡釋的道德賦義與斷章取義的文本直解中尋求到更為理性中和的研究之路,則必須回歸到《詩》所形成的歷史現場,從禮義、樂義、詩義、經義四個向度對《詩經》的篇章進行詳細考察,穿越歷代經解的迷障,以歷史考證的眼光審視存留于詩篇中的禮樂用義,結合文獻記述,對詩的文本進行盡可能質實的解讀。
《詩經》的禮義與樂義
禮義是對禮制、禮儀的用意進行描述。《禮記》言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便是解釋《儀禮》中禮制、禮儀中蘊含的諸多含義,并以《祭法》言祭祀方法、對象、場所等制度,以《祭義》言祭祀所體現的社會秩序、倫理賦義和道德附加。我們用禮義來觀察《詩經》相關詩篇所體現的禮制、禮儀用意,以明確詩作形成的歷史語境。三頌用于宗廟祭祀、二雅用于朝廷之禮,十五國風作為鄉樂,亦用于士大夫的日常禮儀,這些詩作在商周時期的施用場合及其施用方式,決定了其結構形態、表達視角與言說方式。將《詩經》中諸多詩篇置于具體的禮制中考察,考證其中所言的服制、乘輿、祭品、禮器、物候等方面所存留的制度細節,可以一斑窺豹地還原其施用的場合及其禮義,從而對詩作的生成語境進行更為明確的解讀,這是還原《詩經》所處禮樂制度的第一步,也是理清詩作原初意義的關鍵。其中,郊天祀地作為天子專用的祭祀,社祀、方祀、山川之祀作為諸侯和大夫以下階層最高的祭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祭祀禮俗,自上而下地存在于《詩經》時代,其祭禮、祭品、祭儀、祭器、祭法等制度描述存留于《詩經》文本,在與其他文本記述的比照之中,便能還原出諸多詩作的施用場合,從禮義的角度對詩旨進行明確的界定。
樂義是樂歌的施用場合、施用方式、演唱身份、表達指向。作為歌詩的三百篇,施用于周代宗廟、郊社、藉耕、舞雩、饗燕、婚媾、行役、兇荒等眾多場合。由于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左傳》常事不書,《儀禮》為士禮,《周官》《禮記》晚出,周禮制度不明,周禮用樂細節更乏詳載,鄭玄或言及樂義,則多用三禮之說,以言詩事,能明者詳加申說,不明者則失詁。宋戴埴曾言以言求《詩》不若以樂求《詩》,方能理清諸多困惑。周樂失傳,漢樂不興,遂使得漢儒解詩,忽略樂制、樂用、樂時、樂儀而只能就樂德言之,由于其解詩以求美、刺,樂德常被轉化為道德倫理,使得作為樂歌的樂義被徹底無視。社祀為漢儒所不明,社祀用樂則更乏詳解,即便《周禮》言用凱樂于社,《禮記》言用樂于山川社稷,《左傳》等載祓社歌舞之事,漢儒較少論及《詩經》社祀、方祀、山川之祀、行祀之歌的樂義。在土地之祀的禮制考證中,考察相關樂歌的生成機制,進而分析其施用的場合,再由此觀察其被固定化、程式化之后作為禮儀用樂的施用方式,不僅可以理解相關樂歌的題旨,而且能夠還原出社祀用樂的基本方式,從而對周樂諸多細節進行考訂。
《詩經》的詩義與經義
詩義是歌詩的文本義,這是我們考證詩作禮義、樂義賴以入手的有限文本。樂歌的簡明扼要且以抒情為主,如果不放在特定的制度語境、施用場合或者情感氛圍之中,我們很難判斷出其明確指向,就像現在的諸多經典歌曲本有著特定的創作用意、形成背景和施用場合,當抽取出來作為名曲演奏、作為聲歌傳唱、作為文本流傳時,我們便只能就其表層的言辭、聲情與樂感體察其義,而不太深究其原初之義。孔子的弦歌三百、孟子的以意逆志、荀子引詩證言、董仲舒的詩無達詁之說,以及此后漢儒采春秋雜說而注《詩》,便能看出作為禮儀用樂的詩、作為樂歌的詩,在失去禮義、樂義之后只以文本存在時,其便成為可以無窮闡釋的開放文本,形成了煩瑣而相互抵牾、周密卻支離破碎的說解。這就需要我們格外珍惜詩作文本中所殘留的禮制信息和樂用信息,對詩作的原初用意進行辨析,結合西周、春秋、戰國以及秦漢學者引詩、說詩、論詩時對詩文本的闡釋、理解和論述,觀察其與四家詩說特別是毛詩、鄭箋的差異之處,在細微的差異處觀察詩義的不同,盡最大可能地尋繹出原初詩義。這樣洞察幽微的辨析和考證,是穿越經解回歸歷史現場的時空之梭,能夠讓我們在經解之外形成更為穩妥的詩解,而避免望文生義的直覺賞鑒。
經義作為漢儒著力建構并得到歷代儒生補益的闡釋系統,是我們展開討論不得不面對的經典成說。其經典性體現在,我們所言及的禮制樂義,其或多或少皆有涉及;我們展開的考證,便有這樣那樣的訓詁,我們想要保持距離卻無法逃避,這就注定了我們有時采信其說,有時又辯駁其說,很容易讓讀者覺得我們是采用六經注我的方式,有選擇地利用經解。其成說在于,在經學一統的時代,所有的經學家常選擇信從經說的方式改良經說,傳統經說的漏洞被無數天才進行了補充,這使得經解的籬笆越扎越牢。20世紀以來的廢經之風,使得經解大廈不再熠熠生輝;但廢經所采用的文本直解而形成的淺顯,反而使得學者更愿意回望經解大廈的巍峨而心生傾慕,借助經解深厚學養,并再次滋生出諸多新的曲全之說,使得有些看似松動的結論再次被黏合,維持著經解的根正苗紅。我們研究的重心在于穿越經解而回歸到《詩經》時代,對作為樂歌的詩義、樂義和禮義進行回溯,其中為漢儒所闡明的制度、樂用及其詩篇,是我們討論的立足點。而漢儒所遮蔽、誤讀和忽略的詩義、樂義和禮義,則是我們研究著力之處。至少在這一階段研究,我們還是在遵從經典成說的基礎上,對相關樂歌作的生成機制盡可能真實地還原,從而對其詩義、樂義、禮義進行恰如其分的解讀。(曹勝高 陜西師范大學教授)
- 2022-12-13沈從文的史學觀與研究方法略論
- 2022-12-12第七屆上海國際詩歌節開幕
- 2022-12-12中華創世神話工程優秀成果在滬展出
- 2022-12-12承師之愿,十年翻譯《琵琶記》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