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作者:常懷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
20世紀20年代考古學傳入中國,100年后的今天,考古學在中國這般欣欣向榮,已經逐步全面介入中國歷史的研究,甚至有學者發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拓展史料,而不斷拓展史料的希望,在于考古學”的論斷。可以說,上古史的重建已經基本上依賴于考古發現與研究,甚至于戰國秦漢時期以降,對國家基層治理、家族關系等領域的研究,也逐漸向考古學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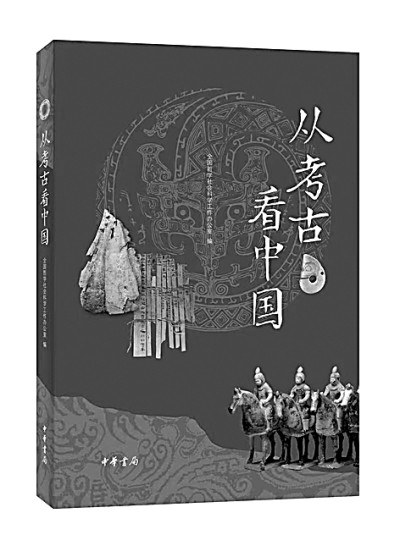
2002年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由綠松石片組成的龍形器。選自《從考古看中國》
學科范式轉變與問題意識提升,不是“地不愛寶”的直接后果,絕不應該以公眾驚詫程度進行衡量。對具有長期文獻史學傳統的中國歷史研究而言,考古學帶來的巨大沖擊是在兩個維度上展開的——其一是作為史料的考古發現對史料本身的補白;其二則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對古代中國和古代中國社會的“深描”視角的補充。
2022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選擇20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冷門絕學”項目的負責人,或以自身主持的項目為對象,或針對熱點考古新發現及問題,撰寫評述結集而成《從考古看中國》,對由考古新發現和出土文獻所反映的古代中國歷史圖景,進行了通俗性的解說。全書共20篇文字,按“多元一體”和“史料傳承”兩個部分排列。前者大體以考古發現與研究為主題,后者則聚焦于出土文獻或傳世文獻的再發現。縱觀全書篇章,可以說是中國史學界歷史研究問題意識轉換的縮影,從若干角度展現了考古學如何為古代社會進行補白與深描。
利用考古材料為古代社會補白的方面,該書通過對三星堆新發現的關注,對黃河中游地區以外良渚、海岱地區乃至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的描述,對商王朝海洋資源尤其是鹽業資源的開發等問題研究成果的綜述,展現考古學介入之后,中國上古史重建研究的現狀。如大眾所知,商代晚期以前的上古史往往摻雜有很多神話色彩,學術界也有人稱之為“原史時期”。對該階段的歷史重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向考古學傾斜,甚至于離開考古資料幾乎無法有新突破。與古史構建同時興起的,是對傳世文獻記載的中原王朝周邊地區文化與社會的再認識。
20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理論更新的速度加快,一個比較重要的特征是立說重心總體上從對政治史精英的關注,由中心轉向邊緣、由權威轉向群眾和社會生活。比如,對于資源的認識和社會組織的考察,原本不是傳統史學的主流話題。以《從考古看中國》書中對良渚文化和渤海南岸商周時期鹽業資源的開發為例來講,就體現了學科范式的變換。在良渚遺址古城、城外水系統和良渚城內多處高等級貴族墓葬發現之前,學術界對中國古代國家政體的形成時間、樣態和表現形式是無實據可依的。恰是考古工作證明,良渚社會是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并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也才真正將中國的國家起源和文明起源上推至距今5000年前后。

2002年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由綠松石片組成的龍形器。選自《從考古看中國》
同樣,對渤海南岸鹽業資源的考古探索,剛剛起步不到20年,這一發現不但印證了甲骨文卜辭中對于商王朝在濱海地區的分封和地方管控、田獵巡守,核心目的是鹽業資源的控制,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為什么在商王朝國力漸衰,在全國其他方向全面戰略收縮的態勢下,仍然堅持對東方的征伐和控制。正是以這樣小切口且專門的研究視角,揭示了早期王朝如何將疆域擴張到東部濱海地區,以食鹽資源為核心,大規模開發和利用海洋資源,發展海洋經濟和貿易。
如果說上述突破仍然只是考古學“正經補史”意味下的沖擊的話,對古代中國社會的“深描”所帶來的史學意義更加深遠。《從考古看中國》一書也有相應體現。
從研究程序來講,史料的出現與研究之間的節奏往往并不匹配,對古代社會的深入認知,往往滯后于史料的發現,而理論的凝練與提升更肯定是在若干認識和理解的沉潛之后方能產生,考古學亦是如此。所謂新發現,并不一定是剛剛被發現的材料,也包括過去曾被發掘而不被認為是“材料”的研究對象。而如何“認識材料”,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學者的眼光和研究的范式,而非依賴于材料本身。這種認知,不僅僅是要將考古學發現置于史學視角之下,也是在非史學語境下,借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視角,審視中國古代的社會組織形態和格局。
《從考古看中國》中對類似三星堆遺址這種從研究材料、研究對象到研究視角的全方位調整,不但是對既有舊研究范式與結構的倒置,也明確提醒學術界,當前范式的轉變,正是在以考古資料重建上古史框架。就三星堆的發現而言,新發現固然彰顯了早期巴蜀地區的特質,但從不斷發現尊、罍容器,還是新發現的人像高冠,都體現出了長江中游文化傳統、技術資源和意識形態對上游地區的輸入和影響。如果脫離了史前中國“多元一體”格局的總體性背景認知,可能對于類似三星堆、環洞庭湖地區和贛江地區的商代晚期青銅文明的認識只能聚焦在其異質性,而忽視了當時中國南方之間、商王朝與地方的技術、文化和資源的互動整合關系,甚至失去了作為東亞文明史的整體格局的宏大認知。

2002年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由綠松石片組成的龍形器。選自《從考古看中國》
出土文獻研究也是一樣。《從考古看中國》以個案說明,在脫離了金石學和純粹的文字考證后,帶有年代“分期”、對象與歸屬意義的出土文獻,發揮出了更大的史學價值。當前的研究,已經呈現出關注文本寫作背景、對象,文本性質和時代規律,甚至于私人書寫和公私紀事敘述差異、地域知識與思想差異的情況,對晚周以降的寫本文書和傳抄古文的文獻淵源、流傳序列有了格局性的觀察視角側重轉移,改變了出土文獻的“史學取向”。其中,考古學所提供的年代學方法、出土背景的判斷和辨識,是視角變化的基礎。
對于考古發現、歷史記載和文本書寫過程的追溯及其所反映的古代中國的面相,是當下史學研究方向凝練的縮影。《從考古看中國》雖然是若干個案的總結,但仍然反映了通過國家社科基金的組織與規劃,使得如何通過考古學拓展歷史研究的疆界,如何通過考古學認識真實的古代中國,乃至通過考古學喚起民眾的文化基因回溯熱情,去重新審視中國。雖然未來史學巨大成就的發展道路和方向有諸多不可預測之處,但作為“小眾”學科的考古學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真實的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地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作出更加突出的貢獻,更進一步補白復雜的古代社會,同時以實證深描璀璨的古代文明。
《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29日 15版)
- 2022-12-28被詩注視的歷程——品讀《越過山頂的太陽》
- 2022-12-28教育理念深藏于故事背后——評“石榴籽繪本叢書”
- 2022-12-28貫通歷史與現實的青年信仰讀本——評《跨越百年的信仰對話》
- 2022-12-27【書評】好家風的熏陶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