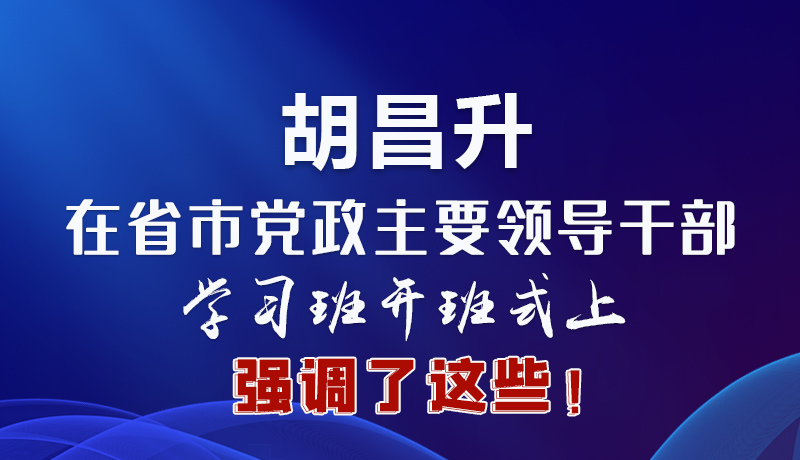“現實與傳奇:王安憶(左)余華(右)對談”線上直播吸引了約40萬人在線觀看,點贊數近140萬次。
(主辦方供圖)
記者 許旸
“一個作家和文學能保持純粹的關系,且自始至終存在,那這個純粹的名字就叫王安憶。”63歲的余華扭頭望向身邊的王安憶。兩位文壇“頂流”滬上對談“現實與傳奇”,持續在朋友圈刷屏。昨天開場前半小時,華東師范大學思群堂已座無虛席。
其中不少學子連夜通宵排隊“才搶到票”,還有讀者玩梗建起了“余華老師追星失敗群”。華東師大教授羅崗在臺上主持時,聽同學提及“入場票在某二手網站炒到千余甚至近萬元”。主辦方開通數個視頻號同步直播,數據顯示,光是華東師大官方號就吸引了約40萬人在線觀看,點贊量近140萬次。
久違的洶涌文學熱情,令王安憶余華好像“穿越”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麗娃河畔是許多人心中的文學據點。余華笑談當年因《收獲》改稿來上海,經常“蹭”格非宿舍,和蘇童、程永新一見面狂聊文學,聊餓了晚上爬鐵門出去找夜宵吃。“那是段美好的經歷。如今身處技術高度迭代的時代,時髦新奇的東西未必長久,笨拙的、樸素的,把大部頭好書,放在膝蓋上翻閱,可能更持久且不被取代。”
能在小說中找到恒定的人物關系,“作家是有出息的”
如何理解文學中的現實?王安憶自稱寫實主義者,需要從現實生活中攫取材料。因此她最初對先鋒文學敘事方法持有警惕。“一是懷疑持久性,一是懷疑可讀性,先鋒文學所表現的世界和我們的常識是有距離的,除非像馬爾克斯重新創造一個常識,好像又沒到那個程度。”
不過,看到余華后來的寫作,她評價余華是“這批先鋒作家里唯一清醒的、自覺的、一下子就找到小說倫理的作家。余華能夠從陷阱里跳出來,服從了現實生活的邏輯,但又能從現實邏輯里脫身,而大部分人是不能脫身的。”在王安憶看來,“余華給人的印象是找爸爸的男孩子,很多小說是寫父子關系。一個作家如果能找到恒定的人物關系,找準自己的‘核’,就很有出息。”她認為余華、蘇童、遲子建等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好作家都找準了“核”,“當時思潮涌動,他們視野開放,生活也沒被格式化。作品里一顆顆種子的內核,支撐著文學小苗慢慢長成大樹。”
余華也談到,文學無論寫實還是荒誕,假如沒有現實基礎,會像斷了線的風箏飄走、被人遺忘,“現實是文學的基礎也是出發的地方。作家總要去現實里提取素材,但提取出素材之后處理的方式不同。”他舉了魯迅《風波》和澳大利亞作家理查德·弗蘭納根《河流引路人之死》來解釋現實提取“夠與不夠”。“《風波》以絕佳洞察力捕捉到辮子這一意象,后者故事則完全打碎,用細節吸引人。”
而他自己的文學之路也經歷過巨大轉折——有次在機場,王安憶說了句“余華你現在的小說讓我看到人了”,這讓余華感觸很深:“安憶說話很樸素,但總打中目標,而且是10環。”寫先鋒小說和《在細雨中呼喊》《活著》以后的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過去作家是小說人物的主宰,決定他們的命運;后來寫長篇發現人物有自己的命運,寫作者要跟著他們的邏輯走。“如果說以前的作品里的‘人’是以符號的形象出現,后來,‘人’是以人的形象站住了。”
王安憶筆端同樣流淌著綿密不絕的生活之流,瑣細無比、貌似尋常的衣食住行,構成了生命的底色。“我可能沒有莫言那種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他是天才,但也不妨礙寫出糟糕的東西,不過還可以寫更好的東西。我們更多是靠后天努力,精打細算抓取生活里每一份材料。”她說。
《長恨歌》囿于“表面的傳奇”,應對日常有莫大的尊敬
“年輕的時候會追求表面的傳奇,包括《長恨歌》也是如此。等到慢慢成熟后再看,追求的傳奇就褪色了。但如果不是有傳奇性吸引的話,作家何必要去寫枯乏的日常生活呢?或許每個小說家都夢想著寫出傳奇,寫平民英雄。”王安憶認為,虛構性敘事在全球都是很難的,如今出現大量非虛構,是因為非虛構本身的真實性容易說服人,另一方面,“現在獲取材料的途徑變多了,但也帶來一個問題,很多人關注后,是不是一定程度上湮沒了傳奇性。這種情況下,小說家最初的出發點還是看題材能不能吸引自己,看它是不是有價值。目前又有了一種要回到日常生活的寫作風潮,這種寫作對日常有莫大的尊敬與肯定。”
最近王安憶在讀美國作家加·澤文的小說《明日傳奇》,聚焦電子游戲,“寫游戲的制作與營銷,說到底還是人與人的關系。貌似傳奇的東西表面之下,其實還是普通的日常生活。”
從日常到傳奇,究竟有多遠?距離余華《活著》單行本第一版面世已有30年,如果說《活著》是寫實主義敘述,上一部長篇《文城》則借助了傳奇小說敘述方式,更具有戲劇性。
“年輕時讀詹姆斯·喬伊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和大仲馬《基督山伯爵》時,就生出了用傳奇因素和大量對話來完成小說的想法,《文城》由此誕生。”在余華看來,日常生活中確實充滿傳奇性,但還有一種傳奇性是被時間拉長后顯示出來的,比如《史記》中的刺客故事就是拉長了時間段的傳奇,“但我不明白為什么那幫人老去編荊軻,其實刺客故事還有豫讓和聶政,后者快刀斬亂麻,前者是鈍刀割肉,都有書寫想象的空間。”
AI“完美卻平庸”,文學在挑戰乏味的世界
ChatGPT4.0引發文學界對人工智能的探討熱潮,王安憶的疑惑在于,AI通過搜索組合大量文字資料進行的模式化寫作是否涉及抄襲?她談到AlphaGo與圍棋選手對弈,人工智能可以和人有交集,與人邂逅;但提高效率的同時,圍棋愛好者們也失去了復盤的樂趣。“寫作本身是充滿樂趣的,就這個過程它不能替代我。我也懷疑人工智能不能做到,因為生活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ChatGPT寫小說的話,大概能寫出中庸而非個性的小說,也許它能寫得看似完美,但本質還是平庸。只有優點是多么乏味,文學應當挑戰乏味的世界。”在余華看來,文學作品的優點和缺點是并存的,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有敗筆的,ChatGPT沒有缺點,反過來也沒有優點。
比如卡夫卡《變形記》,結尾處理粗糙了些,“卡夫卡有疏忽,人腦會犯錯誤,這也是人腦可貴的地方,因為人不按常理出牌,我認為AI至少目前對我和安憶不構成威脅。”余華分享使用國內人工智能軟件的經歷,“文學是什么?文學有什么意義?結果顯示搜索出現故障。可能這就是最好的回答,因為這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你可以有一個答案,也可以有一萬個回答。”
- 2023-03-16作家范穩:“我在滇藏結合部,看到和諧共生的樣板”
- 2023-01-30鄉村少年成為著名作家的背后:寫作是一種補償行為
- 2023-01-29魯敏:以時間為筆,繪金色河流
- 2023-01-05莫言 還有一個書法夢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