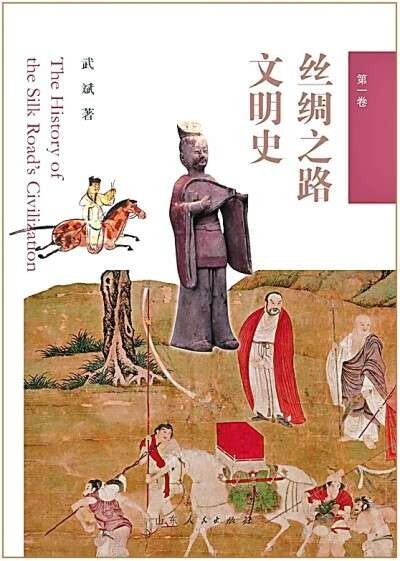
《絲綢之路文明史》 武斌 著 山東人民出版社
【讀書者說】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十年來,“一帶一路”建設有效推進,取得沉甸甸的成就,造福了絲路沿線國家的廣大人民。
60年前,法國歷史學家布爾努瓦這樣描述絲綢之路:“研究絲路史,幾乎可以說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歐亞大陸,也涉及北非和東非。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瓷器和茶葉的外銷,那么它還可以包括美洲大陸。在時間上,它已持續了近25個世紀。”她的代表性著作《絲綢之路》在法國漢學家戴密微的推動下于1963年出版,戴氏親自為其作序,后被翻譯成九種語言,其影響力至今不衰。布爾努瓦這種說法的意義在于,她以一種全球史的眼光看待絲綢之路研究,把絲綢之路上的種種文化現象,看成人類“共同的遺產”加以珍惜。無獨有偶,布爾努瓦的著作出版一個甲子之后,歷史學者武斌教授的《絲綢之路文明史》作為一種遙遠的東方回應,將這種全球共同體的眼光發揚光大,再次譜寫了絲綢之路上文明交流與傳承的樂章。
絲綢之路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
絲綢之路,很早以前有許多不同的叫法,例如“瓷器之路”“皮貨之路”“彩陶之路”“玉石之路”“青銅之路”等等。但流傳至今,為什么“絲綢之路”成為一個共識?
最近的一項研究成果,可能對我們有所啟發。西方學者馬蒂亞斯·莫頓在美國《絲綢之路》雜志第17期(2019年)發表了《“絲綢之路”一詞確為李希霍芬首創嗎?》一文,文中雖然充分肯定了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對“絲綢之路”概念的清晰定義、理論闡發以及將其普及到英法世界的重要意義與歷史影響,但是也抽絲剝繭地論證了在此之前50年里這一提法的濫觴史,這里有各種身份的學者,特別是西方人文地理學奠基人之一李特爾,在其多卷本《地理學與自然和人類歷史》第二版(1822—1859年間)中,不止一處使用“賽里斯之路”或相似表達。他指出,賽里斯之路,即是被譽為“通向中國的偉大貿易通道”。而在1838年(早于李希霍芬39年),李特爾首次使用了“絲綢之路”一詞。因此這一概念的出現,非一人之功,應注意到它的“群體”智慧。
在概括上述要點的同時,我們也想對莫頓這篇論文的閃光點加以延伸。這就是,19世紀以來,如果說法國學者從語言文獻學的角度關注中國,將中國經典作品持續介紹到歐洲,那么對日耳曼語系的學術圈而言,他們將“絲綢之路”概念作為對想象中全球共同體象征的一種解讀,將中國推送給了歐洲。作為桑蠶原產地的中國,隨著“絲綢之路”的概念被歐洲廣泛關注。首先是李特爾,他不同意18世紀德國學者認為蠶與養蠶業都屬于伊朗北部的吉蘭本土傳承的觀點,指出養蠶業最有可能發源于中國,并進行了地理傳播學的研究。接著是李希霍芬,在1868—1872年間對中國進行了七次地質地理考察,足跡遍布當時18個行省中的13個,對山脈、氣候、人口、經濟、交通、礦產等進行了深入探查,中國的桑蠶養殖業和農業在其著作中屢屢被提到。他的五卷本傳世巨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是對“絲路”概念的背書。因此李氏所提出的“絲綢之路”概念,建立在對中國充分實地考察的基礎之上,語境是“中國”。
由此而言,從全球史的角度看,“絲綢之路”概念在19世紀之后成為世界對中國關注的一種象征,并非偶然,它凸顯了當時世界對中國的認知,有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隱含其中。正如武斌教授所言,“絲綢之路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
絲綢之路上豐富的文化大戲精彩紛呈
唐代詩人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讓中國人對絲綢之路充滿了想象。在中國食物中,來源于絲路的,在唐代已經司空見慣,胡桃、胡麻、胡椒、西瓜……如若深考,從“食物”到“物什”,就要讀西方漢學家勞費爾的《中國伊朗篇》和薛愛華的《撒馬爾罕的金桃——唐朝的舶來品研究》等著作。在后一本書的《導論》前,作者引用了英國19世紀女詩人克里斯蒂娜·羅塞蒂的詩:
美妙的無花果,在口中咀嚼,金盤里堆著冰涼的西瓜,大得沒法抱;鮮嫩的桃子帶著茸茸的細毛,沒有籽的——那是透明的葡萄……這一切,你可曾想到?
絲路是一條傳遞物產的路,7—9世紀的唐人品嘗到西域帶來的甜美瓜果。在1000年之后,還是引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神奇遐想。這種文化現象,歸功于絲路的開拓者,也歸功于對絲路史進行記錄與研究的中外史地學家。在這方面,由于《史記》之《大宛列傳》、《漢書》之《西域列傳》《張騫列傳》的記錄,中國史學家可能要拔得頭籌。歐洲到了19世紀,德國可以說是現代人文地理學的領頭羊,前面提到的李特爾和李希霍芬,都是重要代表人物,他們開啟了現代地理學對絲綢之路的研究。20世紀對絲綢之路的研究進一步發展,已經明確了除經由中亞綠洲絲路之外,還有通過北亞的草原絲路以及迂回于南亞的南海絲路。在武斌教授的《絲綢之路文明史》中,又強調了“東方絲綢之路”。
有物、有路,自然就有人。有人,自然就有事件的發生。在這條路上到底有什么樣的人?經歷了什么樣的事?有人將這些人概括為使者、僧侶、戰士、旅行者和商人,例如張騫、法顯、玄奘、鑒真、耶律楚材、馬可·波羅……另外還有新羅人、粟特人和東羅馬帝國的使者。
武斌教授指出:“絲綢之路是文明交流之路,是文明對話之路。在幾千年的絲綢之路上,有民族的大遷徙,物種的大交換,產品的大流通,技術的大轉移,宗教的大傳播,藝術的大交流,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壯、豐富多彩的文化大戲。”
什么是文明史?學術界有各種討論。放眼幾千年在這里出現的物、路、人、事,構成了廣義的文明史,是一部文明史的大書。武斌教授的這部著作,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地理空間和歷史發展,有機地熔于一爐,是一種合理的理解與表達。
美美與共 天下大同
對精神層面的關注,是《絲綢之路文明史》的一個特點。絲路在歷史上早期的文化交流,一般是從衣食住行的生活習俗發生。司馬遷在《史記》中講戰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故事,在漢代是有現實意義的,表現了在漢民族多元一體的發展過程中一位史學家對“通古今之變”的理解。
與絲路相關,真正在觀念形態上中外文化碰撞,是兩漢之際佛教的傳入。西域的龜茲和于闐,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站,當時佛典以口授方式傳入中國。從明帝遣使出使西域,到后來撰寫《佛國記》的東晉僧人法顯和撰寫《大唐西域記》的唐代僧人玄奘,中外文化對話有序開展。佛教進入中國,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大事,絲綢之路所孕育的中印兩個古老民族的對話,通過佛教這種形式,對后來中國哲學的基礎理念、思維方式、民族心理,影響都是巨大的。在中國文化史上,儒學與佛學的對話和融合,是文化交流的一個成功范例。
絲路上各種文化碰撞,禮儀之爭不斷。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中國觀念形態的主流文化——儒家經典,開始被歐洲人重視和研究,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小學》等的拉丁文譯著在歐洲出現了。
在精神層面,絲綢之路上有著不同文化之間的求道、傳道與問道,其中所蘊含的豐富內容和歷史經驗,仍是這條對話之路上的豐厚寶藏。
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之際,山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絲綢之路文明史》,讓我們從歷史經驗中思考當下與未來,內心不免有所觸動。
400年前,明代畢生致力于科學技術研究并為17世紀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的徐光啟,通過和利瑪竇一起翻譯《幾何原本》的實踐,將心得上疏給打算借鑒西洋天算修歷的崇禎皇帝:“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與此同時,中國的四書五經被一字一句地翻譯成拉丁文。絲綢之路上的各種踏實努力,證明了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的道理。只有堅定不同文明平等對話與取長補短的信念,人類“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愿景才會得以實現。
(作者:任大援,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 2023-08-14講述中國地質人奮斗歷程 《青松成林——中國地質四十年》新書發布
- 2023-08-14她跟著沈從文走上紡織考古之路 《大國霓裳》書寫華夏錦繡
- 2023-08-14【新華書單第47期】趣味讀書|8本腦洞大開的書,在游戲中品味閱讀之樂
- 2023-08-14金沖及自傳首發:一代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