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體武譯《我獨(dú)自一人面對(duì)嚴(yán)寒——曼德?tīng)柺┧吩?shī)歌全集》書(sh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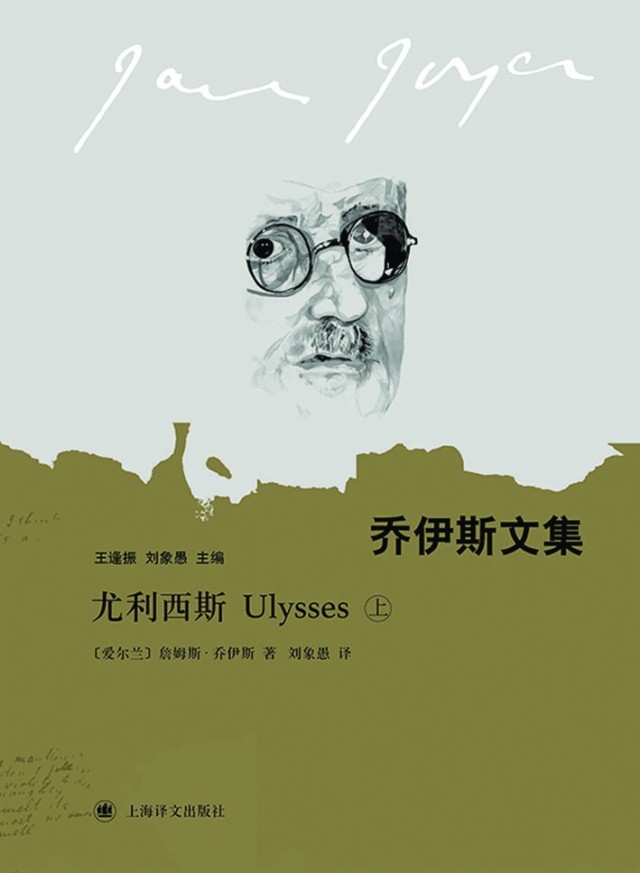
劉象愚譯《尤利西斯》書(shū)影。(均出版方供圖)
■本報(bào)記者 姜方
面對(duì)一本大部頭外國(guó)名著,你是愿意翻開(kāi)細(xì)讀,還是選擇直接刷一條五分鐘快速解讀的短視頻?有了人工智能翻譯軟件后,作為一名翻譯工作者還有什么“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在昨天由上海譯文出版社主辦的第二屆“譯文雙年選”主題沙龍上,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李敬澤領(lǐng)銜的文壇譯界“全明星”們,紛紛對(duì)當(dāng)下翻譯乃至經(jīng)典閱讀所面臨的種種困惑予以高度關(guān)注。
大量文學(xué)經(jīng)典被搬上銀幕或熒屏,而全媒體時(shí)代“幾分鐘帶您閱讀XXX世界名著”之類的短視頻,愈發(fā)讓很多人難以耐下心來(lái)去細(xì)品譯作中的文字。與此同時(shí),隨著人工智能翻譯軟件的廣泛運(yùn)用,不少年輕譯者開(kāi)始依賴科技產(chǎn)生的“便捷”與“效率”,大量“正確但平庸”的翻譯遮蔽了譯者個(gè)性化、充滿靈氣的譯筆。面對(duì)全媒體和數(shù)字科技帶來(lái)的種種變化,專家學(xué)者們認(rèn)為更加需要為深度閱讀和優(yōu)秀翻譯正名,正如李敬澤所言:每一個(gè)譯本自有價(jià)值,因?yàn)榫驮谶@個(gè)譯本上,漢語(yǔ)的鋒刃,漢語(yǔ)新的可能性又得到一次磨礪,又得到了一次閃亮。
全媒體時(shí)代,文學(xué)翻譯正面臨不可逆的改變
這個(gè)時(shí)代,觀看影視劇幾乎已成為閱讀經(jīng)典的“平替”,而這“終究是退而求其次的辦法”。作家、華東師范大學(xué)教授毛尖語(yǔ)出驚人。大學(xué)開(kāi)設(shè)的英美文學(xué)課程上,她建議學(xué)生閱讀簡(jiǎn)·奧斯汀的小說(shuō)《傲慢與偏見(jiàn)》,令她哭笑不得的是,不少學(xué)生以看過(guò)同名電影而等同于“讀過(guò)”原著。“有的學(xué)生看的是1995年BBC電視劇版,也行吧,至少這個(gè)影視改編版本還不賴。”以此自我安慰的毛尖言語(yǔ)間透著無(wú)奈。她直言,有時(shí)一些熱門影視作品會(huì)引用莎士比亞《理查三世》《李爾王》的臺(tái)詞,還能“引領(lǐng)對(duì)此有興趣的學(xué)生去讀點(diǎn)莎翁原著,也算是好的現(xiàn)象”。
“今天我們?cè)谶@里所談?wù)摰奈膶W(xué),指的是那些充分經(jīng)典化、秩序化,有來(lái)路、有去處,一碼一碼白話文的文學(xué)。然而在短視頻時(shí)代、多媒體的時(shí)代,人們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變了。”在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李敬澤認(rèn)為經(jīng)典的、傳統(tǒng)的形式,可能有朝一日會(huì)變得面目全非。“怎么能夠15分鐘就講完《紅樓夢(mèng)》呢?后來(lái)有人告訴我說(shuō),不僅15分鐘能講完,8分鐘、5分鐘也能講完,這也不是我能接受的。”但他又覺(jué)得,“這里面可能包含著新的秩序結(jié)構(gòu),這個(gè)時(shí)候很多人就是需要這樣的方式,當(dāng)然現(xiàn)在的方式可能是粗糙的。”但是李敬澤相信并期待著,這個(gè)時(shí)代或下個(gè)時(shí)代里能出現(xiàn)“絕頂聰明的人”,“把當(dāng)下這些散亂的、沒(méi)有充分自覺(jué)性的形式,錘煉出一個(gè)屬于全新的、有利的,甚至具有未來(lái)經(jīng)典性的形式”。
文學(xué)翻譯作品的接受方式正在發(fā)生變化。而對(duì)于譯者來(lái)說(shuō),因?yàn)槿斯ぶ悄芊g軟件的發(fā)展,作品的翻譯過(guò)程和效果也引發(fā)了業(yè)內(nèi)的不同看法。“比如DeepL號(hào)稱是全世界最準(zhǔn)確的翻譯工具,但是根據(jù)我的使用體驗(yàn),通過(guò)軟件翻譯的句子往往正確但平庸而無(wú)趣,它在用詞的選擇上也非常機(jī)械化和單一,更別提對(duì)一些成語(yǔ)、習(xí)語(yǔ)的生動(dòng)表達(dá)了。”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南京編譯中心主任陸大鵬表示,很多翻譯工作者通過(guò)長(zhǎng)時(shí)間的大量閱讀和翻譯,積累起對(duì)譯文的鑒賞力,然而越來(lái)越多年輕人不愿意自己花力氣翻譯,而是選擇“偷懶”、依賴翻譯工具。“長(zhǎng)此以往,譯者將會(huì)喪失感知美好文字的慧眼,也許未來(lái)會(huì)出現(xiàn)大量通過(guò)軟件翻譯而來(lái)的平庸文字,這才是令人擔(dān)心的。”
當(dāng)下我們能從閱讀經(jīng)典文學(xué)翻譯作品中獲得什么
對(duì)中文寫(xiě)作者來(lái)說(shuō),文學(xué)翻譯作品的學(xué)習(xí)必不可少。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南京大學(xué)教授畢飛宇說(shuō)自己的寫(xiě)作動(dòng)力“絕大部分要?dú)w功于翻譯”,“我作為寫(xiě)作者,沒(méi)有把大量的時(shí)間放在翻譯文學(xué)的閱讀,這是不可想象的。”他對(duì)文學(xué)翻譯作品不僅重視而且十分“講究”,“閱讀經(jīng)典的外文小說(shuō),我認(rèn)為最起碼要看兩個(gè)譯本”。他尤其享受閱讀不同譯本的過(guò)程,“哪怕是遇到了一些構(gòu)成障礙的地方,也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愉悅”。
畢飛宇以法國(guó)作家福樓拜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包法利夫人》為例,翻譯界泰斗許淵沖先生的譯本中有一句“面對(duì)小把戲的時(shí)候”,按照通常的理解,小把戲指一種手段。“根據(jù)語(yǔ)境,文中此處明明是在描寫(xiě)孩子,為什么要寫(xiě)小把戲呢?”在閱讀時(shí)感到疑惑的畢飛宇,后來(lái)了解到許淵沖先生是江西人,“江西人把孩子說(shuō)成小把戲,文中寫(xiě)‘面對(duì)小把戲的時(shí)候’,其實(shí)指的就是面對(duì)小孩子”。正是在許淵沖的這個(gè)譯本里,畢飛宇感受到了中國(guó)方言的特別之處,“這是一個(gè)非常微不足道的點(diǎn),但又讓我在剎那間獲得了特別開(kāi)心的閱讀體驗(yàn)”。
畢飛宇的“講究”,其實(shí)蘊(yùn)藏了由經(jīng)典作品重譯版本之間比較閱讀而產(chǎn)生的豐富意義。而在上海翻譯家協(xi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復(fù)旦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言文學(xué)學(xué)院德文系教授魏育青看來(lái),“一種譯本無(wú)法體現(xiàn)原著全部的角度,一個(gè)譯者也不可能讓譯作像畢加索的立體主義畫(huà)作一樣,完全鋪平了呈現(xiàn)在大家眼前,而重譯的意義就在這里”。魏育青以德國(guó)大文豪歌德創(chuàng)作的悲劇《浮士德》為例,郭沫若去世之前的很長(zhǎng)時(shí)間里沒(méi)有其他公開(kāi)的譯本。“等到上世紀(jì)70年代末80年代初,僅在上海就一下子出現(xiàn)了五六個(gè)《浮士德》的譯本。如錢春綺的譯本對(duì)《浮士德》復(fù)雜的詩(shī)體結(jié)構(gòu)是亦步亦趨呈現(xiàn)的,而有的翻譯家則是用散文體翻譯的。”如果有心的讀者能品讀各種不同的譯本,將有助于看清《浮士德》這部杰作的全貌。
“如果我家里掛著一幅畫(huà),我希望知道它是誰(shuí)畫(huà)的——來(lái)自一個(gè)具體的人,而不是一件機(jī)器。同樣,當(dāng)我閱讀一部文學(xué)作品,我希望它背后有一個(gè)確切的作者,如果是翻譯作品,我希望背后也有一個(gè)確切的譯者。”李敬澤毫不諱言,當(dāng)下譯者的水平確實(shí)有高有低。“水平低的時(shí)候,我心里會(huì)嘀咕,這譯的啥?水平還不如我!水平高的時(shí)候,我會(huì)沉迷。”但無(wú)論譯者水平如何,歸根結(jié)底,譯者和讀者通過(guò)文學(xué)翻譯作品,構(gòu)建起了人與人的關(guān)系、心與心的聯(lián)結(jié),一種建立在文字之上甚至能夠觸及靈魂的情感體驗(yàn)。
昨天,沙龍上頒出了第二屆“譯文雙年選”獲獎(jiǎng)作品。本屆共有17部作品入圍,語(yǔ)種包括英、法、日、俄、德、意等六種語(yǔ)言。長(zhǎng)篇小說(shuō)《海邊》《尤利西斯》《血清素》《如何帶著三文魚(yú)旅行》,詩(shī)集《我獨(dú)自一人面對(duì)嚴(yán)寒——曼德?tīng)柺┧吩?shī)歌全集》,書(shū)信集《赫爾曼·黑塞與托馬斯·曼書(shū)信集》《親愛(ài)的邦尼,親愛(ài)的沃洛佳:納博科夫—威爾遜通信集,1940—1971》,以及非虛構(gòu)作品《尋味東西:扶霞美食隨筆集》入圍決選。最終,獲獎(jiǎng)作品為鄭體武先生翻譯的《我獨(dú)自一人面對(duì)嚴(yán)寒——曼德?tīng)柺┧吩?shī)歌全集》和劉象愚先生翻譯的《尤利西斯》。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guó)甘肅網(wǎng)微信
中國(guó)甘肅網(wǎng)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xué)習(xí)強(qiáng)國(guó)
學(xué)習(xí)強(qiáng)國(guó) 今日頭條號(hào)
今日頭條號(hà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