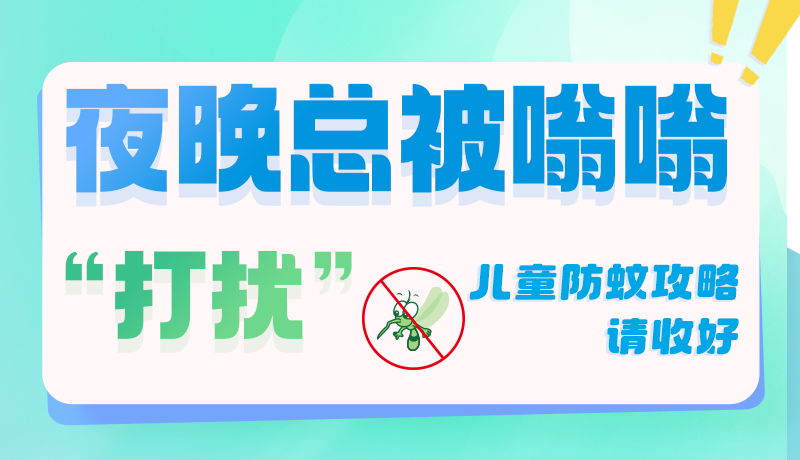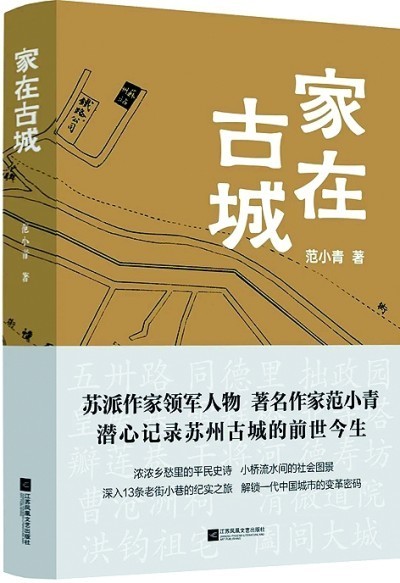
【文學里念故鄉】
故鄉是文學的土壤,文學是長在故鄉的樹。
我的文學之樹,枝枝葉葉皆有情,這個情,就是對于故鄉的感情。
我的祖籍是江蘇的南通市,我出生在上海的松江區,與蘇州都沒有什么關系,但是我始終認為我是一個正宗的蘇州人。
因為從三歲開始,我的根就扎在了蘇州。我也曾經離開過蘇州,比如在南京工作過,但是在那樣的歲月里,不僅家始終在蘇州,心中的牽掛也是無時不在。我曾經寫過一篇散文《南來北往都是客》,比較了南京和蘇州兩座城市的方方面面,雖然最后得出“蘇州人,南京人,都是這個世界的客人”這樣的結論,但是對于故鄉蘇州的偏愛之心,呼之欲出,太過顯露,我甚至大肆地挑剔南京的飲食,認為南京除了一只鴨子,其他基本無甚可吃。
其實不只是南京,我對于蘇州以外的美味佳肴,基本不能接受,何況,又何止是吃。諸多如此的執念,早已經深入骨髓,浸入血脈,改不了,擺不脫,就它了。
我喜歡蘇州。
幾十年來我一直這么說,現在仍然這么說。蘇州松弛又機敏,蘇州淡定卻不“躺平”,蘇州從容不迫、寬厚待人,又勤奮努力、爭取進步。這就是蘇州文化的雙面繡。
因為愛,所以要去了解;因為了解,所以更愛。
蘇州文化是江南文化的典范,頗具代表性,它源遠流長,有著特殊性格,是獨一無二的:它不是爆發性的,而是彌漫著的,是綿長的,而且是有生長性、不斷前行的。最重要就是它的普遍性,或者說是滲透性,它滲透在蘇州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每一個人都可以從最普通的地方感受到蘇州文化的影響。無論是達官貴人、才子佳人,還是普通百姓,無不與蘇州文化融為一體。
蘇州文化,既是高雅的,又是接地氣、有煙火氣的。時時處處,蘇州文化都在啟示你,給你靈感。
蘇州有山,但是山不高,最高的穹隆山只有三百多米,且十分的秀氣;蘇州有水,但是蘇州的水并不壯闊,是小橋流水。這樣的山水養育的蘇州人,性格是溫和的,溫和而又堅韌,靜水深流,看起來柔弱,其實決不懦弱,是有力量的。在生活中,蘇州不把精力浪費在無謂之爭上。蘇州的環境寬松、寬厚。在這樣的環境中,蘇州人勤懇地勞動,無論是“蘇州園林甲天下”“蘇州紅欄三百橋”,還是今天的蘇州經濟社會的發展樣貌,都是蘇州人辛苦創造出來的。這些都是我的故鄉溫和而努力的性格,對于我做人和為文有著重要影響。
就說說我們從小居住的蘇州住宅對于一個人生活和成長的作用吧。
進門之前先抬頭看看門上的匾,匾上的字,比如“厚德載物”,人的品德如大地般厚實,可以承載萬物,一個有道德的人,像大地般寬廣。每天進進出出,頭頂上就是這四個字,會不會受到熏陶?肯定會的,多年下來,一輩子過來,你的道德文章就和別人不一樣了。
再比如“勤儉治家”,想必每天看到這四個字的人家,不大可能天天豪奢享樂。再比如“耕讀傳家”,這些人家的孩子,應該既會讀書,又會做人做事。
良好家風,就在我家鄉的街巷里,這樣平平常常地展開著。說它平常,是因為到處都是,抬頭可見,隨時可遇,十分普及。
每天頭頂著這樣的意思,老話說,“頭頂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想必潛移默化地影響生活在街巷里的每一個人。
還沒有進門就已經感受到文化的影響了,再看看這匾上的字體、書法,要不就是厚實有力,要不就是剛勁挺拔,要不就是淡雅清新,這都是書法作品中的上品,是書法藝術的結晶,絕不會馬馬虎虎、潦潦草草,沒有一點功夫的人,可不敢隨便將自己的字放到人家的頭頂上去。
走進去,看那些磚雕門樓、木刻,多么的精湛,多么的精雕細刻,這都是工匠精神的高度呈現,除了工藝驚為天作,內容上也大多是古代傳統的、向善向上的傳說故事,大多是有教化作用的內容。這又是一種文化的教益。
然后舊廳堂門前兩側的對聯,比如“讀書滿座風云氣,良友一堂富貴春”,或者“勁松迎客人同壽,清風滿堂氣自高”,這些內容,對自家、對客人的心情和態度,都是既積極又坦然淡雅的。
天井不在乎大小,在乎內容,梅蘭竹菊,所謂的梅妻鶴子,恬淡、隱逸,超然物外。
現在,你們也許不同意了,如果江南人都躲在自己的街巷里、老宅里,這么淡然,那么無所謂,“閑飲窗前三杯酒,笑看堂外一樹花”,這人生態度豈不是很消極?就不要進取了?這么沒有追求了?
其實不然,老宅里這一切文化的體現和象征,看起來是淡然的,其實是有追求的,是有很多很大的追求。只是江南人的追求,江南人的努力,是低調的,不張揚的,是悄悄進行的。若不然,江南怎么會成為狀元大戶?
等等,現在你可能又有意見了,這說的都是大戶人家的宅子。其實不然,在江南的街巷,即便是普通百姓的宅子,也都有著自己的文化特色。
比如那許多沿河的平房,開門就是小巷生活,后門后窗是小河文化。行船、買菜,生動、舒展,和現在雷同刻板的高樓住房不一樣,是生動新鮮的,是自然清新、接地氣有人氣的生活。
故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俗就成了我們人生的基礎,也成為我們寫作的依托。從故鄉的人到小說中的人物,從故鄉的風俗到小說的風情,無不深深地烙著故鄉的痕印,無不來自故鄉的饋贈。“陸蘇州”陸文夫先生說過:“小說小說,小處說說。”這也是符合蘇州性格的。故鄉的文化還告訴我,在個人的東西中,必定有歷史和時代的宏大,而宏大的東西,也必定體現在某個具體的人和事上。
從一開始,我就是講著蘇州故事進場的,從此以后,一直盤旋不離。盡管近年我的小說中較少出現鮮明的地域色彩和人物符號,但是我作品的內在靈魂一定是蘇州的。
說一個蘇州故事,我的一個中篇小說《嫁入豪門》。
大戶人家后來日漸衰落。在“我”走進這些老宅的時候,它們已經面目全非了。
但是,宅子變了,遵守的東西沒有變;物質毀了,精神依然在。這是一個老宅里小茶幾的故事,“我”是故事的敘述者,但不是主角,故事圍繞“我”婆家的一只雞翅木小茶幾展開,寫了幾十年來小茶幾的命運,其實也是人的命運,是人的精神走向。
“我”嫁到宋家以后知道了雞翅木茶幾是一件值錢的東西,許多年來心里總是放不下它,一心想把它變成“實用”的東西,但是我的愿望始終沒有實現。
“我”曾經和“老宋”、和“老宋”的母親聊天,坐在陰濕的老屋里,面前的小天井零亂而又寧靜,堆滿了雜物卻沒有一點燥氣。他們對一去不復返的從前生活沒有更多的感嘆,他們對老宅外喧囂繁華的世界也沒有過多想法,他們只是一如既往地守候著自己的那一份日子,延續著家族留傳下來的某些生活習慣和思維模式。
小茶幾只是老宅中一件很細小的物品,是小到可以忽略的。它既是物質,又不是物質。當它被當作物質的時候,它經常易主,命運一波三折,可以被搬來搬去,可以被人長年覬覦,一生惦記,它曾經去過馮爸爸那里,又去過古董店,最后到了小一輩的新房里,也許它還會更換更多的地方和主人。而當它呈現出非物質性的時候,它是永存不變、巋然不動的,無論將它搬到哪里,無論它的主人更換成誰,它的非物質性永遠籠罩和彌漫在時空里,誰也看不見、摸不著,卻有著無限的能量。
這是蘇州文化對蘇州人的影響,也是蘇州文化對蘇州文學作品的影響,它不是沒有欲望,也不是沒有動搖,但是終究會堅守著該堅守的東西,終究相信有一種力量永遠都在。
《嫁入豪門》是蘇式的,小說的畫面是蘇式的,“他們家的天井真是很小,院子的墻壁斑斑點點,有發霉的青苔,還有一些不知什么枯藤爬在上面,只有一棵芭蕉,雖然不大,卻是長得郁郁蔥蔥的。他們家的屋子也很小,三間屋子都很擁擠,里邊堆滿了烏七八糟的舊家具破爛貨,也不知道是些什么東西,他們家的人就在那些東西的夾縫中鉆來鉆去,而且他們的動作很輕盈,幅度又小,都是無聲無息的……”
小說的人物是蘇式的,“我刷了牙,把牙刷朝杯里一插,他看了看,就把它倒過來重新插到杯里。我看不明白,說,你干什么?他又慢條斯理地說,小馮,牙刷用過了,要頭朝上擱在杯里。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牙刷,說,為什么?他說,牙刷頭朝下,就會一直沾著水,容易腐爛,容易生菌。我說,把茶杯里的水倒干了,牙刷就浸不到水了。他說,倒得再干,也總會有一點水積在杯底。我說,這是你們大戶人家的講究?他說,無論是什么人家,都應該這樣的。等我洗過臉,掛了毛巾,他又過來了,我趕緊看看我的毛巾,我那是隨手掛的,等于扔上去,當然是歪歪扯扯。他看了后,就動手把毛巾的兩條邊對齊了,然后退一步看了看,又再對了一下,那真是整整齊齊了。我說,怎么,兩邊不對齊容易腐爛嗎?他說,不是的,兩邊不對齊,看起來不整潔”。
小說的細節是蘇式的,小說的對話也是蘇式的。在這里,蘇式無處不在。蘇式,是一種情緒,是一種生活形態。而在小說作品中,蘇式又是寫作的一個訣竅,是解決問題的一把鑰匙。
由一個承前啟后、中間時段的人物,牽連起蘇州大戶人家的命運,“我”,既往前走,又往后看,“我”的眼睛和腳,走過了這一段歷史,也走進了歷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之中。
我們不能擺脫物質、丟棄物質,但是我們又不甘心被物質所束縛。于是,我們困惑,我們迷茫——這就是小說中的“我”。
將這樣的困惑,這樣的迷茫,在文學作品中呈現出來,這是我們當今寫作的價值體現。而它的精神實質,既是蘇式的,又是現代的,這就是蘇州文化的生長性。
最后抄錄我在長篇非虛構作品《家在古城》中寫下的一段話,作為結尾:
“這一次的采訪和寫作,我最大的收獲就是知道了自己的無知和淺薄,在蘇州古城面前,我要再用一遍我已經用過數次的話:它們所容涵的博大精深,恐怕是我窮一輩子努力也不能望其項背的。
于是,在我的文章里,我在每一個章節,每一個段落,每一行,甚至每一個句子里,都埋下了煙花,如果有人愿意,或者我自己愿意,點燃這些煙花的引索,它們將綻放出無數絢麗無比的畫面。”
(作者:范小青,系江蘇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 2023-09-04《詩經》記錄的先秦愛情與民俗
- 2023-09-04繚綾何所似
- 2023-09-04評兒童小說《完美一跳》:有質感的成長書寫
- 2023-09-04研討阿乙《未婚妻》 重啟“文學京彩季”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