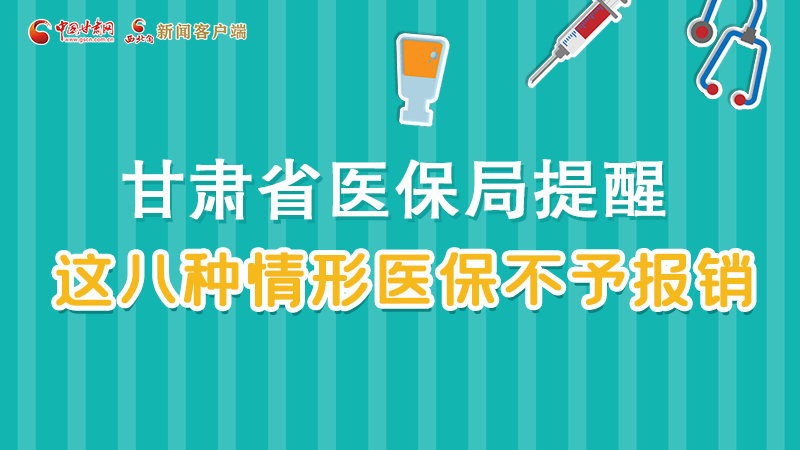浙江文藝出版社可以文化供圖
編者按
十月金秋,四川文學也迎來豐收季。今年以來,四川作家新作不斷:阿來推出新詩集《從梭磨河出發》,熊焱新詩集《我的心是下墜的塵埃》出版,盧一萍憑新長篇《少水魚》完成“新寓言”四部曲……在2023天府書展上,四川作家的諸多新作也引來眾多關注。這些新作,能看出作家怎樣的文學追求?抒寫了什么對生活與命運的感悟?反映了怎樣的時代變遷?本期川觀書評推出特別報道“四川作家出新作”,敬請垂注。
“現在,我要獨自一人,任群山的波濤把我充滿,我的足踝,我的象牙色的足踝是盤虬的老樹根了……”很多人都讀過阿來的小說,那么,關于他的詩呢?
繼8月19日,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阿來與《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評論家黃德海在上海一起分享自己的新詩集《從梭磨河出發》后,10月15日,“我的心房是一個巨大的蜂巢——阿來詩集《從梭磨河出發》分享會”在2023天府書展分展場阿來書房舉行,阿來,著名作家、詩人葉舟以及作家梁平向讀者分享了詩歌文字本真的生命力。
兩次分享會上,阿來坦言,詩歌是我文學道路的起點,“我沒有出版過好多部詩集。此前僅有《梭磨河》《阿來的詩》等。《從梭磨河出發》這本詩歌集見證了我從1982年到1989年,剛進入文學書寫世界的一些記錄和痕跡。”
壹
收錄阿來詩歌數量最多 帶來深邃的閱讀體驗
《從梭磨河出發》收錄了包括《風暴遠去》《這時是夜》《群山,或者關于我自己的頌詞》《靈魂之舞》等風格鮮明、意象高雅的作品。這些詩歌通過優美的語言和流暢的敘事展現了遼闊寂靜的高原生活,以質樸真摯的筆觸抒發了阿來對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壤以及大自然的敬畏與熱愛。
該書是迄今為止收錄詩歌數量最多的阿來詩集,其中第一輯的內容是阿來1991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個人詩集《梭磨河》,第二輯與第三輯選自2016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阿來的詩》,在此基礎上第四輯增加收錄了阿來早年發表在地方雜志、民族詩選等讀物上的作品。
正如阿來所言,他的文學創作之路由詩歌開始,詩歌為其后來的小說創作鋪了道路,這也是阿來的小說在當代文學中獨具語言和哲思魅力的緣由之一。川西涉藏地區一直是阿來作品靈感的來源,也是他在創作中一直努力尋找的答案。他以詩歌的形式,將高原上的故事娓娓道來,奔跑的白馬與牦牛,游弋的天鵝,生長著的野櫻桃,充滿著原始的生命張力,帶給讀者獨特深邃的閱讀體驗。
貳
一個作家的文學回憶錄 在梭磨河回溯青春詩意
“梭磨河/梭磨河/我拆讀你輾轉而來的信札。”阿來說,之所以詩集會以“梭磨河”命名,是因為這條河流就是自己家鄉的一條河流。從地理上講,梭磨河是大渡河上游的一條支流,大渡河一路奔流,翻越群山峽谷,最后在樂山大佛腳下融入岷江,與岷江一起匯入長江。
從梭磨河出發,阿來在詩里多次提及自己出生、成長的村莊與河流,他也曾經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創作之路就是從家鄉、從故土開始的。“它是我文學道路的起點,是我的青春期。這些是我1982年到1989年的作品,那時我剛開始寫作,30歲后,我的寫作興趣有所轉移,就沒有再寫過詩,但這一份接近模糊的記憶被重新打撈上來,我還是很感動的。”阿來回憶,“那個時候我身邊有一群不同專業的年輕教師,他們都在寫詩,也經常拿出來朗讀并且互相評判。因為我當時閱讀的都是普希金和惠特曼之流,于是‘口出狂言’說他們寫得不好,但他們不服氣,我就和他們打賭寫了兩首詩,確實寫得還不錯,那時同事們都很單純、可愛,我最開始寫的幾首詩都是他們幫我發表的。”
提及阿來的詩歌,葉舟說,這部詩集就像是阿來的第一部文學回憶錄,是他寫作生涯的回憶。如今,翻開《從梭磨河出發》,詩里充滿具體的生物意象,狼、野牛、紅馬、頭羊、牦牛、白馬等,象征著頑強鮮活的生命力,具象的物種特征和抽象的感官體驗結合在一起,將詩歌的精神指向純凈、原始、與自然融為一體的自在世界。在這里,阿來的青春時光和廣袤的世界徐徐展開。
梁平回憶,自己和阿來都是上世紀80年代同時期出道,那時候兩人都還屬于青年詩人,“彼時阿來寫的詩歌不多,但是每一首都會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草原、牦牛、馬匹等很多元素都在阿來的詩歌里出現。”他介紹,那時《星星》詩刊有一個很重要的欄目,每一期都會在國內挑選一批創作者照片發在上面,“我和阿來最早的同框,就是在《星星》詩刊。”梁平打趣,自己第一次看見和阿來的同框照,就覺得這個人“有點帥,有點不安分,藏著很多野心。”
在詩歌里,讀者也確實能看見這樣的文學野心。在成都的分享會上,阿來深情誦讀了自己的《群山,或者關于我自己的頌辭》。在他看來,這首詩歌就藏著他的“野心”。他介紹,此前他寫詩歌,也會寫自己的苦悶、青春,“但后來,我覺得自己還是要和更大的世界聯系起來,讓自己和群山、地理等廣闊的世界連接。一個寫作者應該有讓自己廣大的野心。就如這首詩歌,歌頌群山就是歌頌我自己,歌頌我自己就是歌頌群山。”
如今,再翻開這本詩歌集,阿來坦言,自己有一些感動,因為從梭磨河的詩意里看見自己的青春,看見流逝的歲月。
叁
表達從詩歌開始 形成了獨具個性的“風騷”
“我的表達是從詩歌開始;我的閱讀,我從文字中得到的感動也是從詩歌開始。”回憶當年寫詩的興起,阿來直言。
阿來寫詩的時代,也是程永新沉浸式感受過詩歌引發狂熱追捧的時代。他說:“那時候整個社會的形態都在發生變化,也是詩歌興盛的年代,朦朧詩基本上人人會朗誦。我們學校的禮堂每隔一段時間都會舉行詩會。當有同學寫出好詩的時候,全校都會轟動。在那個詩歌的黃金年代,我也讀了很多詩歌,一直認為詩歌是離哲學最近的文學樣式,詩歌也是我們對世界的態度。”程永新稱阿來為“文學偶像”,他認為,阿來的小說語言非常漂亮,正是和早年的詩歌創作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他的詩歌有著惠特曼的氣質,小說的語言也非常準確。”
黃德海更是在《從梭磨河出發》中找回了程永新所提及的那種感覺,“我一下子回到了當時詩歌熱的年代。阿來詩中的意象可以和我們共振,抒情詩就是一種共振的傳統。”黃德海更是用“風騷”一詞來形容阿來的詩,“阿來用他自己所有的作品,形成了獨特的風騷風格。”
“阿來的詩歌也是獨特的。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詩歌運動正盛。”梁平說,因為居住地等多方面的原因,阿來并沒有參與當時的詩歌浪潮,也沒有和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發生太多的聯系,“正是因為沒有發生這種聯系,所以他的寫作,才獨樹一幟,有自己的特色。”
談到《從梭磨河出發》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詩,梁平認為:“詩集中有兩組詩特別需要引起注意——《群山,或者關于我自己的頌辭》《三十周歲時漫游若爾蓋大草原》。這兩組詩串起了阿來詩歌寫作的能力,‘群山’這組詩語言的氣息和情感的四溢以及對意象的處理得到了聶魯達和惠特曼的真傳,但阿來并沒有簡單地模仿這兩位詩人,他注入了民族的血脈和漢語的隱秘力量,想了解阿來詩歌的氣象,就必須要讀這組詩;閱讀《三十周歲時漫游若爾蓋大草原》,我們看到了阿來對民族身份的認同和對這片大地的認同,可以看到他和這個世界的聯系。即使后來阿來沒有寫詩,他的詩情也融入了之后的作品。”
肆
河流流淌 少年之“鹽”扎根結晶
阿來所有的作品都離不開這些根植于詩歌中的文學基因,這是他透過無法割舍的故鄉的群山、草原、河流、牧場、村莊,用高原居民最頑強而純粹的果敢與堅韌在詩歌中構筑的精神家園。《從梭磨河出發》讓人們看見阿來文學創作的根和構筑的自然精神殿堂。
葉舟用“鹽”與“河流”來總結自己對阿來詩歌的感受。“我聽見遠方的海洋中鹽正在生長”,葉舟說,這句源于阿來的詩歌,就像是《從梭磨河出發》的一個核心詞,“讀到這句詩詞,我才第一次知道鹽也是有根的。”從這個角度出發,葉舟認為,阿來的詩歌就像在回憶一個少年之“鹽”的成長,講述它是如何提煉、如何結晶,它變得越來越晶瑩透亮。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少年的詩情是怎么慢慢結成“鹽”的。
此外,葉舟認為,故鄉的梭磨河水在文字的血液中不息流淌,流向阿來的精神原鄉。阿來在他的詩中將自己完全融入這片充滿生機和驚喜的大地,帶給讀者獨特深邃的閱讀體驗。葉舟表示:“我們看到的是從梭磨河出發,它是整個長江的上游,但它也是一個少年記憶的上游,阿來在向我們展示他的文學來路。所以我猜想這是阿來文學回憶錄的第一部,以后也許會有第二部。”
葉舟認為時間可以塑造一個人,一個人同樣也可以賦予時間意義,閱讀這本詩集,再回頭看現在的阿來,感覺一個人的成長就像一匹馬在奔跑。
伍
詩情從未泯滅 寫作走向更廣義的詩
30歲時,阿來的寫作從詩歌轉向了小說,第一部長篇小說就是茅獎作品《塵埃落定》。“我的詩歌其實是一個游戲,但我沒想到這個游戲把我帶到了一個嚴肅的世界,那就是文學。我們在年輕時摸索不同的方向,這也是自己人生的可能性。在當時寫詩的時候我也在寫中短篇小說。1989年,我出版了兩本書,一本是詩集《梭磨河》,一本是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舊年的血跡》。”
激發最初創作沖動的梭磨河,成就了阿來。而阿來當時并不自知,他甚至有過迷惘。“我就是喝梭磨河的水長大的,我就在那片有雪山、草地、森林的地方長大,這個地方也是我的出發點。但我那時候產生了巨大的困惑,我到底是不是作家?然后我覺得我和這片土地和自然有一種互相感知的關系,我決定這輩子要嚴肅對待,于是我有4年一個字沒寫,1994年我才開始寫《塵埃落定》。”
程永新說,很多作家成名以后早期的作品是不愿意提的,而阿來愿意把他的來路告訴讀者,這是一種勇敢和自信的表現。對此,阿來是認可的,所以當可以文化決定推出詩集《從梭磨河出發》時,他還有些小激動。在上海的分享會上,阿來不斷拿起詩集,翻一翻,放下;再拿起,翻一翻。應觀眾要求,他更用四川話和普通話朗誦了兩首詩《撫摸蔚藍面龐》《如何面對一片荒原》,阿來感言:“在我心中,詩情并未泯滅。我只是把詩情轉移了。我從來不敢忘記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說過這樣的話,詩比歷史更接近于哲學,更嚴肅。我要把我的寫作帶向更廣義的詩。這些努力,我感覺我的讀者都有所理解。”
- 2023-11-01【空哥談宋】那些年,他們38歲
- 2023-10-31互聯網時代,感受閱讀的意義
- 2023-10-31《天龍八部》手稿首次公開亮相
- 2023-10-31上海書城煥新歸來 “以書為城”點亮燈火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