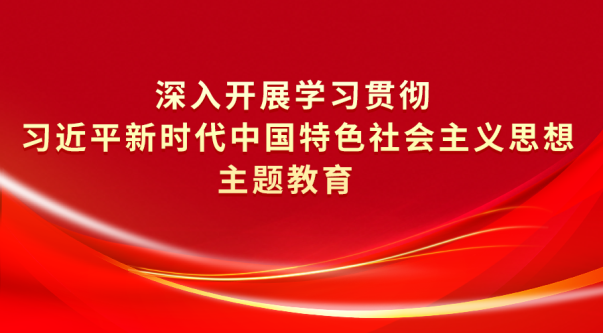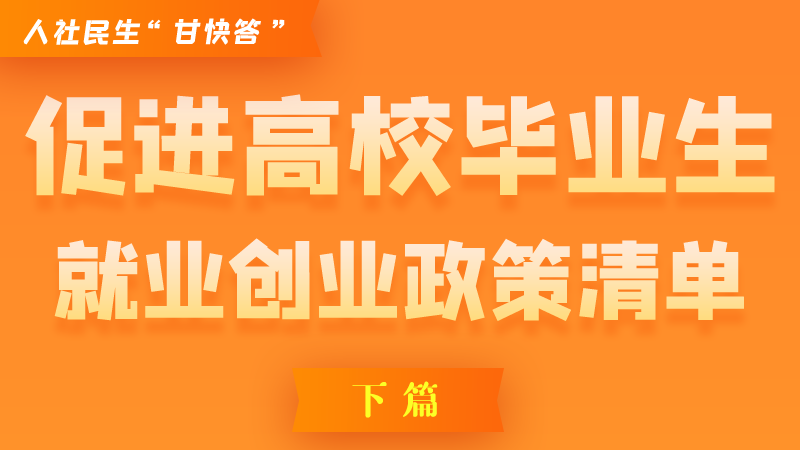作者:王暉(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作為進藏20余次的作家,徐劍與西藏這片神奇土地有著不解之緣。對于他來說,西藏不是單純的地域版圖或旅游目的地,而是他生命歷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創作的一個重要源泉。他的《東方哈達》《經幡》《金青稞》《雪域飛虹》等作品,傾心書寫青藏鐵路、青藏聯網工程、藏區精準扶貧、西藏歷史與文化等內容,共同構成鐫刻著作家靈魂、情感與心血的“西藏敘事”。
報告文學《西藏媽媽》(入選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發布的“中國好書”2023年9月推薦書目),是徐劍“西藏敘事”的最新篇章。在作品里,徐劍既堅守他一系列西藏題材報告文學的基本風格,也呈現出新的氣象、追求新的表達。這部“為新時代新西藏的慈善公益而歌”的作品,不乏徐劍報告文學一以貫之的瑰麗絢爛、高歌深情,以及“千年一夢桃花落”的詩意流淌與詩情綻放。從立意、結構再到語言,這些特質浸潤其間。與《東方哈達》《雪域飛虹》等書寫重大工程壯闊、恢宏主旨有所不同的是,《西藏媽媽》是再現普通人日常生活與家庭氣息的“西藏敘事”,充溢著樸實、溫馨、舒朗和慰藉的治愈系風格。作品形象地表達出新時代西藏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民辦實事、辦好事,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如作者所言:“一代贊普的夢想,經過了一千三百年的歷史時空,唯有在新中國,在一代共產黨人的手中,才變成現實。”
2013年,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頒發《關于全面推進五保集中供養和孤兒集中收養工作的意見》,提出3年內在全區實現有意愿集中供養的五保對象在縣以上供養機構100%集中供養、孤兒在政府主辦的地(市)以上兒童福利院100%集中收養的民生保障模式。也就是說,孤兒被集中收養在地市級兒童福利院,五保戶則被集中供養在縣級福利院,簡稱“雙集中”,實現少有所托、老有所養。其中,在兒童福利院,負責管理教育這些孩子的工作人員大多是女性,一個“媽媽”照顧4個至10個孩子,共同居家生活。作者在一個偶然的時機獲知這個群體的動人事跡,決定要像這些愛心媽媽全心愛護孩子的執念一樣,為西藏寫一部新作品。他秉持報告文學的行走方式,由昌都兒童福利院開始,足跡遍布西藏大部分地區,傾情描述拉薩、日喀則、昌都、林芝、那曲等地市的兒童福利院里上百名愛心媽媽的感人故事。作品以兒童福利院空間為聚焦點,以“媽媽”為人物再現的核心點,以“媽媽”對福利院孩子的用心關愛為共情點,講述愛心媽媽們的身世、言行、作為和境界。她們或為未婚女、未生娘,或為終身未嫁女,但大都集溫馨、樂觀、責任和大愛于一身。作品對這些各具特點的人物形象進行了精彩描述,她們有著“拉薩河一道浪花”似的清純微笑,有著像天上月亮一樣的美麗容顏,有著像太陽一樣博大的胸襟和熱忱,有著良善的品格、悲憫的情懷和高貴的風采,有著豐盈而圓滿、溫柔而博大的精神世界。大量來自生活原態的對話、細節和場面描述的文字,簡潔而深情,使得全書舉重若輕、神采飄逸。在專注于愛心媽媽與孩子之間故事的同時,《西藏媽媽》還具有闊大的敘事開合度,通過對福利院這一特定空間與“西藏媽媽”這一特定人物群體的敘寫,拓展至當下社會普遍面臨的婚姻與家庭、就業與扶貧、青少年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等廣闊領域,進一步強化了作品內蘊的深度和廣度,從而讓作品所帶來的治愈性效應超越了單一的情感慰藉,抵達具有現實意義和哲理意味的思想高度。
好的題材與深刻的思想,需要有好的形式來呈現,所謂“藝術的文告”大抵如此。在當代報告文學作家行列里,徐劍有著突出的才情和清晰的文體意識。他傾心或醉心于報告文學的藝術營構,并勇于超越自我。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鮮明個性和“徽章”,令人印象深刻。譬如,敘寫青藏鐵路的《東方哈達》以上行與下行列車式交錯敘述結構,鏈接歷史與現實;《金青稞》以“他”視角的轉換與交錯,展現時空交織中的西藏今昔;《雪域飛虹》以“正負極篇”折射青藏電力聯網的壯舉等。在《西藏媽媽》中,作者精于藝術營構的用心亦是隨處可見。作品以第三人稱敘述孩子與愛心媽媽及相關人物的故事。在大多數章節里穿插作者的田野調查、采訪紀實,以第一人稱“我”呈現非敘事話語,作用在于抒發情感、表明態度等。兩者的相互交融,既是推進故事、速寫人物的需要,也強化了報告文學作為非虛構文體的鮮明印記,還使得結構更加自由、靈動,語言也更富于藝術之美。作者努力將對“西藏媽媽”的敘述與自身的西藏情結貫通起來,形成不同于一般旁觀者式的采訪與書寫。通過類似“有我之境”式的共情傾訴,作品內容的真實感、切近感得以凸顯。無論話語還是結構,《西藏媽媽》都傾向于將舒緩、動情的治愈性元素植入其間,以此強化藝術探索的獨特性。
《西藏媽媽》就如一個象征,有力拓展了作者“西藏敘事”的思想內蘊和情感邊界。徐劍在青年時期就與西藏結緣,并在后來歲月里以20余次的頻率與西藏親密接觸,西藏成為他的第二故鄉,也是精神原鄉。因此,“西藏媽媽”也許正是作者深藏內心的真情呼喚,是他個人與西藏之間的一次心靈交流。另外,對于當下西藏題材的報告文學書寫而言,這部作品可以提供新的理念和新的啟示。推而廣之,對于報告文學創作如何突破既有模式、開辟新的發展空間這個關鍵問題而言,《西藏媽媽》是一次貼地的實踐,也是一份重要的參考,還是一張用心的答卷。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22日 14版)
- 2023-11-23圖畫書《鄂倫春的熊》:一個鄂倫春小女孩的森林之旅
- 2023-11-23《如何是好》:不越藩籬 何以變好
- 2023-11-23論小說對《滕王閣序》的經典型塑
- 2023-11-23麥場上的遺穗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