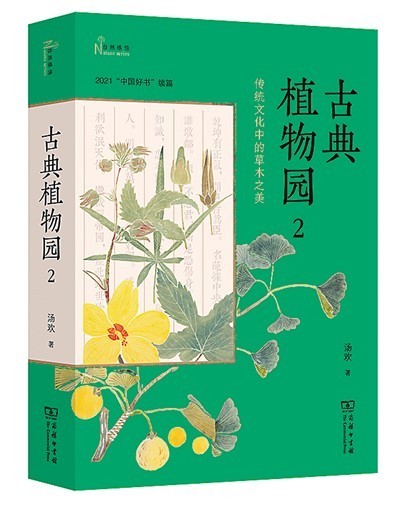
生長于草木繁茂的鄉(xiāng)間,我自幼對身邊的一花一木感到好奇,囿于條件有限,彼時尚不知那些自由絢爛的野花野草叫什么名字。大學(xué)上《詩經(jīng)》課,接觸到細井徇《詩經(jīng)名物圖解》,看到那些精美的插圖,才真正認識了荇菜、飛蓬、游龍(紅蓼),然后再讀“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山有喬松,隰有游龍”“自伯之東,首如飛蓬”,這些植物立即浮現(xiàn)眼前。2000多年前,先民怎樣發(fā)現(xiàn)它們,為何將它們寫入詩中?經(jīng)過漫長的歷史流轉(zhuǎn),它們又寄托了后人怎樣的情感,發(fā)生過哪些有趣或感人的故事?
在好奇心的驅(qū)使下,我開始以具體的植物為對象,去探尋它們背后的歷史文化。翻閱古籍中與植物相關(guān)的各類文獻時,我越發(fā)覺得,植物是打通古今、連接中西的載體,我們身邊尋常可見的一草一木,背后都可能蘊含著無比厚重的歷史文化。
自古以來,植物就是衣食、醫(yī)藥之源,是先民賴以生存的物質(zhì)基礎(chǔ);與此同時,山中喬木、河畔青草、空谷幽蘭,亦是先民寄情寓興的重要載體。牡丹象征富貴,蘭花是君子,梅花有傲骨,折柳贈遠別,紅豆寄相思,它們出現(xiàn)于文學(xué)、繪畫之中,是融在國人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如果植物會說話,講起自己在歷史長河中的種種遭逢和際遇,可供言說的很多:從本草、農(nóng)學(xué)、園藝,到經(jīng)學(xué)、文學(xué)、民俗、掌故,乃至東西文明交流、歷史地理氣候……可以說,由草木匯集起來的,是一個豐富駁雜、有趣有料、詩意盎然的世界。
自然界的花草樹木那么美,與它們相關(guān)的詩文典故那么美,畫家筆下的花卉、博物插畫和本草圖譜也是那么美,如此多美麗的事物涌現(xiàn)在我面前,除了將它們寫下來,我想不到別的辦法來表達內(nèi)心的感動。“寫作是內(nèi)心的需要”,我在中文系課堂上聽到的這句話,貫穿了兩本《古典植物園》寫作的心路歷程。
因此,《古典植物園》并不是什么植物都寫。美國小說家卡佛說,每個作家都應(yīng)該寫自己熟悉的、能感動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寫“應(yīng)該感動”他的東西。我在選取所要寫的植物時,就遵循了這一原則。
寫哪種植物往往緣于一種契機,或一種緣分。這個契機可能是讀書時遇到了問題,有了問題意識,才有了尋找答案的動力。例如,《詩經(jīng)·鄭風(fēng)·溱洧》里的“勺藥”究竟是不是芍藥?“蜀葵”是因為產(chǎn)自巴蜀而得名嗎?木蘭就是玉蘭嗎?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正是寫作的過程。
這個契機也可能是日常生活或旅行途中的發(fā)現(xiàn)。一年冬天在北京的早市上,我見到了慈姑和荸薺,聯(lián)想到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和小說,覺得有必要好好認識一下這兩種植物。之后重讀汪先生的文章,竟然有意外的發(fā)現(xiàn)。又一年夏天去襄陽,在護城河的橋頭被兩棵巨大的夾竹桃所震驚,于是就想了解一下這種植物的前世今生。
另外還有一種契機,是某個時刻遇到了這種植物,而它勾起了我的過往回憶,植物背后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例如《古典植物園》中的葎草、金銀花、茉莉、水杉,是分別寫給我的父親、母親、中學(xué)好友,以及紀念我外婆的。在寫這樣的文章時,情感自然流露,寫起來最為順暢。
《古典植物園》無意向讀者做百科全書式的介紹。若是一味羅列文獻、面面俱到,與古代類書又有何異?因此,有了寫作的契機之后,扎進書堆,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找到有用的資料,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這項工作有時無比繁瑣,如果遇到植物名實不符需加考辨,寫作難度則會更大。
困難雖有,但在經(jīng)史子集和東西文化之間尋找答案、挖掘故事,很像探險。因為你不知道會遇到怎樣的文獻資料,不知道會有怎樣令人心神蕩漾的意外發(fā)現(xiàn)。
以《古典植物園2》為例,從杏花寫到巴旦杏,才知道梵·高那幅著名的《杏花》是巴旦杏花,與我們江南春雨中的杏花并非一物;在了解荸薺的外形、生存環(huán)境和文化特質(zhì)后,對《受戒》這篇小說的鑒賞又多了一個視角;寫冰雪中盛開的款冬,經(jīng)由“僧房逢著款冬花”這首詩,對晚唐詩人賈島有了顛覆性的認識;由蜀葵寫到向日葵,得知它在傳入我國之初曾因形如蜂房而被嫌惡;而探索鳳仙花、散沫花這兩種可供染色的指甲花,就像在古印度、波斯以及中原文化之間暢意神游……
每到這個時候,我都會真心認同南美作家馬爾克斯的這番話:“有時候,一切障礙會一掃而光,一切矛盾會迎刃而解,會發(fā)生過去夢想不到的許多事情。這時候,你才會感到,寫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能夠帶給你“探險”般的樂趣,讓你遇見更多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這可能是兩部《古典植物園》與其他植物文化類圖書最大的不同。
(作者系植物科普作家)
- 2024-01-19《紙上起風(fēng)雷:中國文人1900—1949》新書首發(fā)式在京舉行
- 2024-01-19國際視野下的敦煌學(xué)研究——讀《尋夢與歸來——敦煌寶藏離合史》
- 2024-01-19《中共中央國務(wù)院關(guān)于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shè)的意見》單行本出版
- 2024-01-19《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十卷本)出版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xué)習(xí)強國
學(xué)習(xí)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