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錦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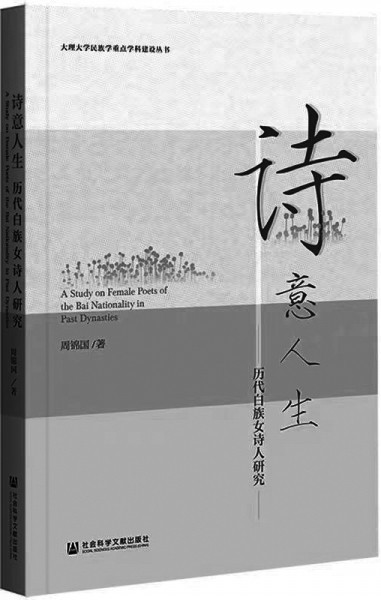
閱讀提示
《詩意人生:歷代白族女詩人研究》聚焦從元代到民國大理地區的23位白族女詩人及其作品,解碼在特定歷史時期白族女詩人群體的構成、創作成因、主題演進、創作特色、審美價值與社會意義,是一部詩學視野下白族知識女性的精神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該著作既體現了女性詩學研究的理論創新,也彰顯了白族女詩人之于民族文化記憶的構建意義。
■ 陳輝 田泥
在古代文學史上,詩歌向來就被看作是男性的舞臺,少有如李清照等這樣能突破性別偏見藩籬的女詩人,進入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學史敘述之中。這就導致,知識女性在克服傳統社會種種困難之后,她們的文學表達依然難以被注意、記錄、保存和流傳,后世女性文學研究者們往往需要從眾多史料之中去鉤沉、裁選、考訂出一些“只言片語”,以此打開被深鎖在歷史空間中被忽視和低估的女性集體記憶,來感知作為人類世界一半女性的心靈、情感和思想世界。此種困難可想而知。周錦國的《詩意人生:歷代白族女詩人研究》則是一部專門對大理地區少數民族女詩人研究的成果,該書將“女性詩人”這一視點放在邊疆少數民族,聚焦有史料所載的23位白族女詩人及其作品,解碼在不同歷史時期白族女詩人群體的構成、創作成因、主題演進、創作特色、審美價值與社會意涵,是一部詩學視野下白族知識女性的精神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一部白族女詩人的精神文化史
本書作者在分析、考釋白族女詩人群體精神文化構成因素時,首先對她們所處時代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與狀況進行了深入考察,以人系史,揭示出了影響她們詩詞創作上的主要外在因素。白族深受儒家漢文化的影響,在不同歷史時期與漢文化之間經常有著很密切的互動和融合,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白族女詩人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從南詔大理國時期到元朝,再到明清時,儒家文化的道德體系和規范,逐漸成了白族知識分子們的主流,直到清末民初新式教育的建立和新思想的涌入才發生變化。
這一漸進的過程體現在女詩人詩歌里就形成了一種“過渡—成熟—再過渡”的總體藝術特征,主題和審美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在早期高夫人、阿蓋等人的詩歌內容里,白族地區的風物、歷史和語言占有著較大比例,呈現出一種過渡時期文化交融的特色;及至明清時期在周馥、蘇竹窗等人的詩中,這種過渡色彩就已經褪去,白族的文化歷史傳統和漢文化歷史傳統在詩歌表達上已然變得渾融和成熟,并有著大量的儒家漢文化因素和價值觀念,儒家文化占據了主體;而到了清末民初,跟隨儒家文化的際遇,在白族婦女們的詩上又體現出了過渡時期的特征:既有著如楊熊氏、楊周氏、蔡呂氏等為堅守忠貞而殉節的絕命之語、李培蓮溫柔敦厚的儒家風格之言,又有著如章青昔《五月農人》等充滿強烈反思意味和平等觀念的現代之思。
當然,除了漢文化浸染這個社會文化因素以外,內在家庭動因如家學淵源、家庭角色分工等,也是影響白族女詩人藝術創作的重要因素。絕大多數白族女詩人或學詩于家中長輩,或學詩于丈夫,亦或本身就生長于教育世家。豐富的家庭文化資源是她們得以寫詩的文化基礎,但對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的認同,也使得她們的詩通常囿于家庭之內。夫妻唱和詩、愛情詩、思夫詩、家庭日常生活感事詩、寫景詠物詩、教育詩等占據了她們詩歌的絕大部分,只有周馥、袁漱芳、李培蓮等少數幾人展現了對歷史、社會政治現實的紀事、思考和詠嘆,但這些作品在她們的詩作中也并不占多數。
順著這樣的精神文化構成的邏輯追索,作者對白族女詩人及文本所呈現出的精神質素,進行更為縱深地解析與判斷。采取的策略就是將白族女詩人的詩歌創作,納入中國古代女性文學中加以觀照,盡管還沒有提供更具翔實的詩作文本比照分析,所涉及的文本細讀與意義挖掘還顯粗糙,但也大致闡明了白族女詩人在詩歌創作上與中原地區女詩人之間的共性與個性,展示了她們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和地位。
白族知識女性內在精神空間的構筑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白族女性,其詩作在思想內容、情感體驗和精神表達上與中原地區女詩人的作品有著許多共通之處。我國古代女詩人在詩詞創作上所表現出的跨時代共同主題,諸如閨中相思、棄婦憂愁、感物傷懷等,在白族女詩人中多有體現,她們同樣以家庭生活為核心,敘述對外出丈夫的思念以及家庭生活情景。例如蘇竹窗的《聽砧》:“秋氣肅然重,鄰砧入聽才。夜隨涼月靜,聲帶暗霜來。乍斷知無力,連敲覺有哀。感余難遽寐,半晌倚妝臺。”此詩描繪了因聽見石砧上敲打聲所引起的孤寂悲涼,寫得極為精妙和富有表現力,已然具有大家風范。一同宣揚儒家婦道規范的詩亦有不少,如周馥的《課二女迎壽、雙岫》:“女終伏于人,坐繡平心性。一月四十五,日輪牽得定。”此詩既是教育女性應當品德順從、吃苦耐勞的典型,也蘊含著詩人夫子自道之感。
此外,非功利性的個人情懷抒寫,在特定歷史時期書寫家國時事與抒發家國情懷,也是她們的共同之處。不同于男性寫詩往往帶有交流或傳世的意味,女性詩歌的欣賞對象通常只限于家人和少數幾位好友,這使得她們的詩作更多的是個人情懷的真切抒發,顯得更自然,更有詩意特征。而在社會動蕩、轉折之時,她們當中富有卓識者,也能寫出具有深切家國情懷的作品,表達自身的憂國之情與社會之思。像李培蓮的《春光》一詩:“迭遭烽火后,無復錦官城。草木千叢繞,春光百戰經。村煙皆斷絕,華屋長榛荊。一片荒涼景,何時見太平?”于寫景之中寓以社會現實,表達出對社會時事的關切和對太平盛世的企盼,即是此中佳品。
但大理畢竟處于邊疆,白族自身也有著豐富的文化歷史和習俗風物,其位置也與佛教文化區相接壤并有著深厚的當地佛教底蘊,故其文化上雖然以儒家文化為主,但也呈現出多種文化相交融的色彩,反映在女性的詩作中則體現出了獨特的價值和興味。首先是對大理自然、風物等的生動表現,如蘇竹窗對大理定西嶺的描寫,起句“佳氣莽無邊,橫來半壁天”(《登樓望白崖定西嶺諸山》)就展示了此山雄壯的氣勢,而另一句“馬背千盤路,林梢百丈泉”就充分突出了大理山形特色,頗具地域色彩。其次是不乏當地佛教教義的思考,如周馥的《雨銅觀音殿示同游諸娣侄》中“都是空三法,最難滅一嗔”等句,以詩的語言將自己對佛義的參悟道出,盡顯高妙。最后是在日常世俗空間中審美特性上更加“堅韌”,白族女詩人雖然也經常表現閨中相思、棄婦憂愁,也會感物傷懷,但很少具有“閨怨”氣、“柔弱”氣,尤其與江南女性詩人相比,更顯邊疆少數民族女性的堅韌和剛毅,“瘦”“病”“愁”等古代女性文學常用詞在她們的詩作中幾乎難以見到,周馥《紫笈夫子就館中甸話別》:“唐破吐蕃地,夫君又遠征。鐵橋江漭蕩,石鼓雪崢嶸。翁歿新阡表,姑衰宿疾縈。家貧無一可,辛苦硯田耕。”一詩就是很好的例證,此詩敘寫在丈夫即將再次踏上遠行之路之時,盡管家中依然貧困,公公新近離世,婆婆又疾病纏身,但她不僅沒有抱怨,反而展現出驚人的理解和包容,以無畏的勇氣面對生活的艱辛,生動顯示了邊疆白族女性的剛強品質。
我們也不難發現,白族女詩人全部都使用漢文創作,在詩歌中經常出現對中華民族歷史和古典文化的引用與借鑒,通過詩歌表達對中華民族共同歷史的認同和記憶,如袁漱芳《春燕》一詩中有“白玉樓高身可寄,烏衣國遠夢能通。上林如許春光好,待爾飛鳴御花中”,就連著化用了“白玉樓”“烏衣國”“上林苑”三個中華歷史典故來表達自身的思想感情,充滿了歷史記憶和文化韻味。可見,白族女詩人不僅展示了自然生態、家庭文化、生命經驗與心靈世界,也傳承了傳統文化,構筑了女性集體記憶和大理邊地的文化景觀,這對中華多民族文化融合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母體文化的重建,同樣具有非凡的價值與意義。
總體來看,這部詩學視野下的白族知識女性的精神文化史的搭建,其本身所提供的歷史經驗也表明,本書作者其實就是沿用了經典的文學史寫法與框架,然后把文本及史料裝載,加以對邊地白族女詩人與中原女詩人詩作的風格等比較和總結,側重于把白族女詩人與民族文化、中華母體文化關聯重點梳理。而對于白族女詩人所表達的傳統性別文化結構對白族女性鉗制與束縛以及她們自我內在精神空間的構筑等,該書并不作為重點聚焦與挖掘。諸如野史中對高夫人唯一詩作遺存的肆意增改,從而將高夫人弱化為男性詩人筆下的“怨婦”等事件以及數量上不少的因固守忠貞而“殉節”的女性絕命詩、決絕詩的存在,作者在談論這些絕命詩、決絕詩時,對她們的歷史處境與生命遭際抱以理解和深切的同情,也側面指認了深受傳統封建文化思想控制的白族女詩人的“殉節詩”本身就是對歷史發出的控訴。
白族女詩人所書寫的對身體、身份與精神多重禁錮的抵抗之聲以及形塑的自我形象與文化載體之詩作,都成就了看似不具有現代性別主體想象,卻有著可信的女性存在的歷史史實與文化鏡像。因此,盡管作者并沒有完全從性別文化視角說明:白族女詩人所有的歷史情感與精神處境是疊合在男權中心文化場域之中的,混雜著一些對傳統封建文化秩序的認同與妥協。但作者進行史海鉤沉,讓女詩人群像浮出地表,這就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與理論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 2024-03-18《喚醒:從人類、后人類到超人》:未來的人類如何生活?
- 2024-03-18國內首家地圖主題特色書店青年之家揭牌
- 2024-03-14離白塔最近的書店開門迎客
- 2024-03-12從舞蹈史的角度研究古代文明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