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細節的魅力和張力】
作者:楊遙(山西省作協副主席)
很多年前,女兒大概四歲,我領著她買童書,在街上看到一位穿著灰色僧袍的尼姑,她驚奇地說:“世界上真的有尼姑呀!”兩三歲的時候,她就問過類似的問題,比如“世界上真的有蝙蝠嗎”。在兒童的認知范圍內,有些東西必須親眼見到,才認為是真的。后來,我把這兩個細節寫進小說《放生》的第一段,因為這些細節有趣,還暗含了一種對世界的疑問與好奇。
細節來源于生活。大約十年前,我和妻子、女兒在鄉下老家過完春節,要坐綠皮火車回省城太原。想著春運期間客流量大,就提前趕到火車站。恰巧遇到我兒時的伙伴和他的妻子。他們帶著一個特別大的行李箱,要前往省城趕廟會。我們聊了大概有半小時,來了另一位同鄉,也要上太原。這時伙伴跟他的妻子說:“有人幫我把行李箱弄到火車上去了,你回吧。”我驚訝地說:“還以為你老婆要陪你去太原,弄箱子的話我可以幫忙,為啥要讓你老婆一直等?”伙伴說:“你是城里人了,哪好意思麻煩你。”我又問他:“你的票有沒有座位?如果沒有,可以和我們擠一擠,我們有三張票。”他說:“不和你們去一起擠,說不到一塊兒。”當時悲哀涌上來,我馬上想到魯迅的《故鄉》。這位伙伴是我曾經很好的朋友,為我打過架,現在隔閡竟然這么大。我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好的小說細節,把它深深記在腦海里,后來找到一個合適的機緣,寫入小說《把自己折疊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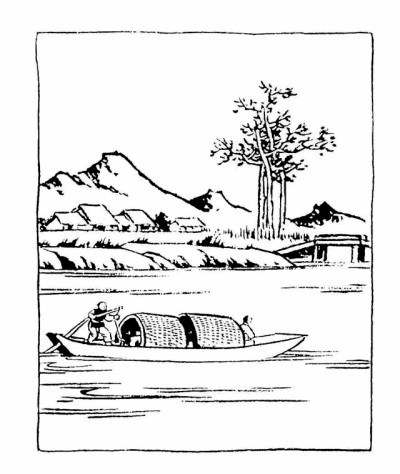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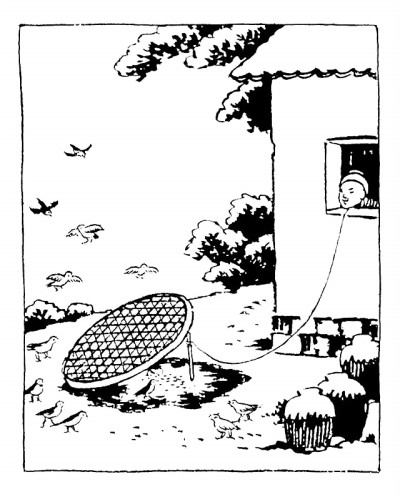
魯迅《故鄉》 豐子愷繪
相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在老區武鄉縣,我采訪從事微商的人,居然有不少是五六十歲的中老年人,其中最大的一位已經七十多歲。我們開始采訪的時候,這些農民紛紛打開手機,要直播采訪過程。這還是我們印象中的農民嗎?我還了解到一些非常生動的細節,比如讓孩子給自己買智能手機學習拼音、把小米賣到非洲等。如果不是深入生活,根本不可能了解這些事情。在臨縣,我采訪一位80后駐村第一書記,她講鄉親們每天用當地的傘頭秧歌夸獎她,我問她手機里有沒有這些歌曲,她說保存著一部分,打開讓我聽。聽著這些曲調不算優美但很真誠、熱情的歌,我剎那間被震撼了。我覺得這就是小說中的細節。后來我把這些細節寫進作品《父親和我的時代》《大地》之中。
好作品中的細節,大多描寫的是熟悉的生活。像魯迅寫的多是水鄉紹興的生活,沈從文寫的是邊城湘西的生活,張愛玲寫的則是十里洋場上海的生活。對細節的把握,考量的是作家對生活的熟悉程度,也考驗著讀者。
一個作家如何選擇和書寫細節?首先必須準確。美國詩人龐德說過:“寫作的道德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它的表達在根本上是否準確。”我讀許多小說,時間一長,會忘掉情節,甚至是主人公的名字,但能清晰地記得其中的一些細節。我常常折服于優秀作家對日常生活中細節的準確把握和扎實表達,他們目光如炬、不耍花招,像技藝高超的漁夫,一叉下去就是一條魚,魚身上水淋淋的,散發出腥氣,還在掙扎,但已經被捕獲了。
許多人描寫細節喜歡用大量的形容詞和花哨的比喻,看上去很美,讓人感覺作者有才華,卻華而不實、詞不達意,有一種無力的感覺。也有人描寫的是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我們翻開許多雜志一眼就能看到,這樣的細節準確但無聊、無神。好作家不這樣寫細節,他們描述的細節往往是真實的細節,生活中確實存在,還能打動你。一般作家就捕捉不到,因為它們太平常、太普通了,看上去不夠美,也不夠感人。但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細節,小說的現場感才更強,讓讀者感覺寫什么都像是真的。這類細節,是優秀小說的基礎,使小說具有了真實性。
在我的閱讀經歷中,通過描寫那些最尋常的物事打動我的,是托爾斯泰和喬伊斯,他們的準確是其他作家難以比擬的。讀《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有這種奇妙的感受。《戰爭與和平》反映的是從1805年到1820年間的重大歷史事件,年代已經頗為久遠了,講述的故事也發生在異域,但絲毫沒有讓我產生隔膜,反而讓我從中找到我和我生活中熟悉的朋友,他們的許多舉止行為習慣,包括對人生取舍的態度有著驚人的相似。《安娜·卡列尼娜》中許多對日常生活的描寫,使我不得不與自己的日常經驗聯系起來。納博科夫在《俄羅斯文學講稿》中寫道:“一些上了年歲的俄羅斯人在晚茶桌上談到托爾斯泰筆下的人物時,就好像這些人物是真實存在的,會拿這些人物和自己身邊的朋友作比較,能夠清清楚楚看在眼里的人物,就好像與他們跳過舞,或在共進晚餐。”其實,不只是上了年歲的俄羅斯人,年輕的中國人、世界上許多人恐怕都有這種感覺。
愛爾蘭作家喬伊斯也有這種能力。他的《尤利西斯》總是將敘述打斷,停下來描寫。這些描寫瑣碎到生活的每個細節,但因為精準,這些瑣碎沒有讓人感覺乏味,反而妙趣橫生。如描寫布魯姆早上起來準備早飯時,描寫了炙羊腰、熟豬血、鍋糊等七種氣味兒,讓整個早晨生動鮮活起來。尤其是描寫布魯姆妻子起床時,“她那半臥的身子上升起一股熱氣,在空氣中和她斟茶的香味兒混在一起”。讓人覺得自己就在布魯姆的家里,親眼所見,親耳所聞。
細節除了要書寫準確,還要具有意義。魯迅的《故鄉》開始就是一段描寫景物的細節:“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這段自然環境描寫渲染了一種悲涼的氣氛。根據史料研究和小說分析,“我”這次回鄉是要變賣家產,去尋找一種別樣的生活。舊中國農村日益破敗的狀況,“我”的心境,從這幾句話中就能略窺一二。《孔乙己》中寫道:“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臟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寥寥幾筆,家境敗落、生存窘迫、受人欺辱卻又放不下架子的落魄讀書人形象躍然紙上,為后來孔乙己被打,用手走路,再后來消失埋下伏筆,前后呼應。
張楚剛剛發表的長篇小說《云落圖》中,出現一個短暫人物“睜眼瞎”。她發現萬櫻懷孕之后,認為掌握住了她的把柄,不斷要挾她,問她要東西。張楚用方言敘述睜眼瞎問萬櫻要東西的過程,又具體描寫了睜眼瞎從萬櫻家翻找東西的細節,寫得非常生動,讓這個在小說中沒有出現幾次的人物有了辨識度,被讀者記住:
睜眼瞎是講究人,沒空手來,拎了捆嫩生生的小白菜,還有兩塊鹵水豆腐。萬櫻啥話沒說,先將剩下的雞肉端給她。睜眼瞎煞是為難:“妹呀,忒涼,吃了胃疼,不吃呢,又顯得我挑三揀四,哎,做人咋那難?”嘚啵間已將雞翅根啃完,又挑了雞肝慢慢嚼品,邊嚼邊叮囑:“日后燉雞肉,可少放些十三香,多放些桂圓。”等兩只肥雞爪也啃得不剩半星皮肉,萬櫻將她拽到嗡嗡作響的冰箱前,抻開門,說:“想拿啥就拿啥吧。”睜眼瞎摘下黑框眼鏡擦了擦眼角說:“大妹子,你對我真心實意地好,當姐的可咋報答你?”萬櫻說:“我還有些雜七雜八的小玩意,稀罕了你可勁挑。”睜眼瞎說:“大妹子啊,別急,我先驗驗這冰箱,別落下貴重東西。嗯,我記得還有盤南美冰蝦。”
好作家描述的細節除了來源于真實生活,還有一種是在生活的基礎上通過想象來呈現。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三部曲寫的內容都是假的,《不存在的騎士》中的騎士沒有身體,《樹上的男爵》中的男爵永遠待在樹上不下來,《分成兩半的子爵》中的子爵被打成兩半活了下來,一半代表善良,一半代表邪惡。卡爾維諾通過想象,卻真實地描寫出這三類特殊人的生活,給人真實的感覺,讓人更多地思考小說中蘊含的深刻意義。這種“真實”不是表面上的真實,它脫離了大眾的思維定式,脫離了普通的常識范圍,但符合深層次的邏輯,某種意義上更加真實。在邏輯基礎上想象的細節,可以讓小說長出翅膀,從而抵達更遠的地方。
《光明日報》(2024年03月27日 14版)
- 2024-03-25在夜歸的路上看過星星 在擁擠的人潮守望麥田
- 2024-03-22彭學明長篇小說《爹》:為湘西人物風土立傳
- 2024-03-21從城市人文普及類圖書和講座里“讀懂上海”——翻開這部超級大書,“閱讀”在不斷升級
- 2023-12-08此心安處即是家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