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疆千里光像磁石一樣吸引著野生動物。選自《野草:野性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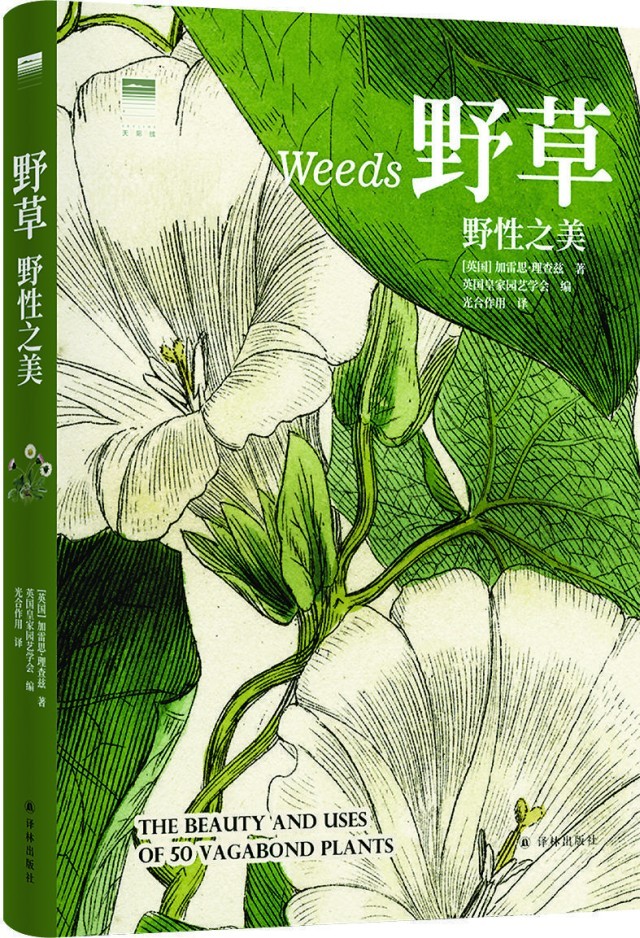
《野草:野性之美》 [英]加雷思·理查茲 著 光合作用 譯 譯林出版社出版

《與花方作譜——宋代植物譜錄循跡》 [日]久保輝幸 著 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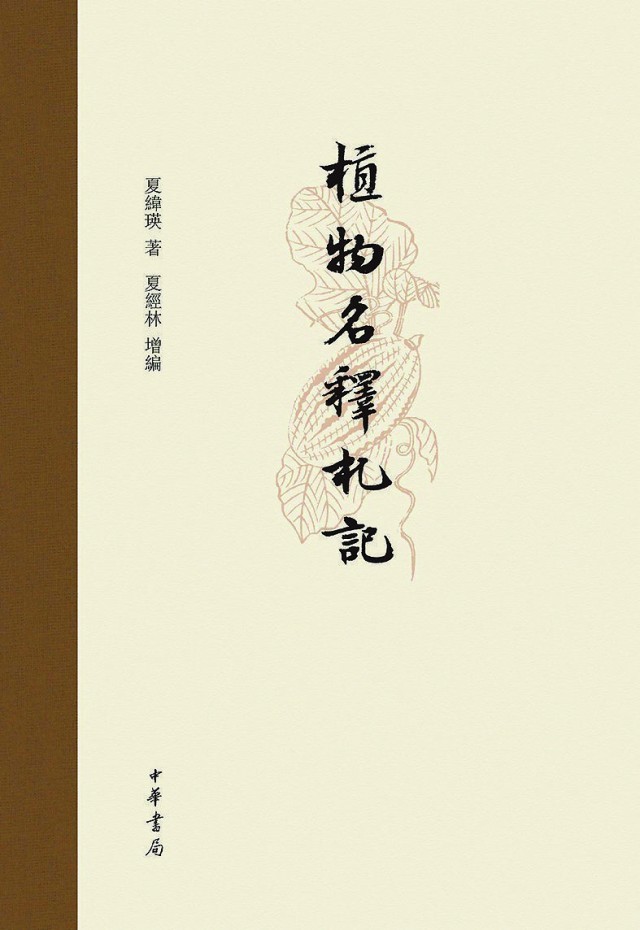
《植物名釋札記》 夏緯瑛 夏經林 著 中華書局出版

《香港方物志》 葉靈鳳 著 余婉霖 繪 商務印書館出版

《游隼》 [英]J.A.貝克 著 李斯本 譯 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
■李濤
辛稼軒晚年有一闋《賀新郎》云:“惠子焉知濠梁樂,望桐江、千丈高臺好。煙雨外,幾魚鳥。”人就是這般,老去方知萬事空,富春江上,雨霧釣臺,魚鳥之戀是多么的美好啊。而春天,翻閱一些博物學的閑書,也是一件或許無用,卻很美好的事。
從無用的雜草里找出有用的性質來
近期出版的《野草:野性之美》是其中之一。50種世界各地的野草,風吹哪頁讀哪頁,先撿那些熟悉的名字看:牛蒡、雛菊、大葉醉魚草、苦苣菜、原拉拉藤、藍鈴花、野芝麻、虎杖、婆婆納、野豌豆,手繪博物畫插圖有130余張之多,文字倒是簡略,對需要了解更多野草知識的讀者,略有不滿足,不要緊,英國博物學家理查德·梅比有一本妙不可言的《雜草的故事》,前幾年有了中文版,你可以找來讀。
這兩種關于雜草的書都來自英國,我們中國也有一本小書不可忽略,即周建人著《田野的雜草》,這是三聯(lián)書店1949年6月出版的,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之一種,小32開,只有70頁。全書分為“引言”“春季常見的雜草”“野草的生命”“夏季常見的雜草”“花的構造及與外界的關系”“到了秋天”“在冬季里”“結束的幾句話”八個部分。作者的用意,“是拿自生在田邊、路旁、河畔等處,平時看作不大有用處的草類來講,使讀者對于那些草認識得更明白些……可能會從無用的雜草里找出有用的性質來呢”。
寒齋所藏為1950年4月第三版,已經印到一萬冊。這本小書后來似乎未再版,十年前偶然發(fā)現(xiàn)被收入《花鳥蟲魚及其他——周建人科學小品選讀》一書,書中還有周氏其他40余篇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他在博物學方面的成就。
中國古代的博物學著作極為豐富,盡管與后來誕生于西方的博物學不完全一致,但自有其體系。大名鼎鼎的《本草綱目》,其內容涉及了文學、歷史、天文、地理、地質、生物、化學等多學科知識,可謂是一部博物學著作。博物學(natural history)是敘述自然即動物、植物和礦物的種類、分布、性質和生態(tài)等的最古學科之一,博物學家是“對博通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的專家的尊稱”。在我看來,他們不僅博學,更是一些勇敢的人,他們生產出無數今天已成為常識、甚至婦孺皆知的知識,然而,這一行當在今天卻似已步入黃昏。
既可格物致知,也可托物言志
無用的博物學,因了一些有眼光的出版家的推動,不時出現(xiàn)在新書訊息中,梭羅的《野果》、澀澤龍彥的《花逍遙》、卡拉納皮的《本草:李時珍與近代早期中國博物學的轉向》、范發(fā)迪的《知識帝國: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諸書,令讀者愛不釋手。
去年讀到兩種新書《植物名釋札記》《與花方作譜——宋代植物譜錄循跡》,一本討論中國植物通俗名稱的來龍去脈,一本深入厘清有宋一代植物譜錄的發(fā)展脈絡,都是極具學術價值的著作。前者為已故的夏緯瑛先生耗盡畢生心血完成,在中國典籍中,植物的同物異名、同名異物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夏先生認為:“一個植物名稱本身,就反映著在那個歷史時期我們先人對這種植物的認識程度。”數十年中,他遍翻古籍,行萬里路,直到晚年因雙目失明,無法繼續(xù)。比如“牡丹”,他注意到,歷來醫(yī)書均未釋名,他通過辨析指出,“‘牡丹’者,以其根皮之赤丹而為名,‘牡’字無義。”值得一提的是,夏先生的植物名稱辨析,不唯從語言學出發(fā),是在大量的植物調查基礎上進行的,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與《植物名釋札記》筆記式行文風格不同,《與花方作譜——宋代植物譜錄循跡》是一部厚重的專著,作者久保輝幸是在中國工作的一位日本學者,他注意到植物譜錄這一類專著在宋代的大量出現(xiàn),但已有的一些研究多停留于古代科技成就方面,他的研究更多關注這些譜錄的作者的人生經歷與時代背景,闡明這一類出版物的興盛與當時社會的關系,讀來饒有興味。據作者的調查,宋代花譜中,有牡丹譜15部、芍藥譜四部、菊花譜八部、梅花譜四部、蘭花譜和海棠譜各二部、玉蕊花譜和瓊花譜各一部,以及綜合性花譜四部,此外尚有經濟植物譜錄26部,但動物譜錄僅有區(qū)區(qū)四部。在對這些譜錄進行文獻學考察后,作者發(fā)現(xiàn),北宋時期作者的思維明顯帶有“格物致知”的學術精神,而南宋時期作者則更傾向于以種植行為表現(xiàn)其隱遁的生活態(tài)度。這一點,美國漢學家艾朗諾《美的焦慮:北宋士大夫的審美思想與追求》一書中“牡丹的誘惑:有關植物的寫作以及花卉的美”一章亦有相關論述,盡管二者的研究取向不同,但可以參照閱讀。
博物學給予一個普通讀者的幫助與欣喜
以上中日學者的兩本著作,都是需要潛心多年,甚至需要一種不計實用的態(tài)度方可成就,其成果亦可資學術領域之外的普通植物愛好者閱讀,但現(xiàn)實中,常有一種跨界的博物學寫作者,他們的著作另有其有趣之處,比如葉靈鳳。
葉靈鳳的《香港方物志》1958年在香港中華書局初版,收入作者在1953年間陸續(xù)在香港《大公報》發(fā)表的112篇短文。葉氏在“前記”中說:
我將當地的鳥獸魚蟲和若干掌故風俗,運用自己的一點貧弱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民俗學知識,將它們與祖國方面和這有關的種種配合起來。
翻看目錄,“香港的香”“一月的野花”“新蟬第一聲”“海參的故事”“香港的野鳥”“香港的蜘蛛”“水仙花的傳奇”,看了這些標題就明了書的內容。查《葉靈鳳日記》:
1952年12月25日 約了高雄夫婦及《大公報》的劉芃如夫婦來吃晚飯……芃如約為《大公報》的副刊“大公園”寫一關于香港草木蟲魚的連載。
1953年1月21日 自元旦起,開始在《大公報》的“大公園”寫《太平山方物志》,記本港的鳥獸蟲魚和人情風俗,每天約一千字。
1953年1月23日 寫《太平山方物志》,自今年元旦開始,每天寫一篇,已寫了二十多篇了。只是這題目是不能長期寫下去的。
1953年2月3日 寫《太平山方物志》。就要過舊歷年了,又要準備一些過年風俗的資料。
據《葉靈鳳日記》可知,《香港方物志》中的短文,最初發(fā)表時總題為《太平山方物志》,署名“南村”。葉靈鳳當時每日要寫4000字,有時一天寫了6000字,其中就包括了這《太平山方物志》,因此他曾擔心不能持續(xù),不僅是精力,更多的是博物學材料的儲備。多年前讀過香港南粵出版社所出葉靈鳳《花木蟲魚叢談》,驚訝于這位當年“創(chuàng)造社小伙計”的知識淵博,讀了《香港方物志》則又對其背井離鄉(xiāng)后的生活多了些了解。在日記中,他曾慨嘆某一類文章“寫得太多了,也覺得索然無趣”。但稿費一到,女兒已等著要上街買新大衣了。賣文為生之不易,于此可見矣。無用的博物學,卻可為潦倒文人之生計。
“今年立春早,不僅紅棉開了,就是杜鵑也開了。”葉靈鳳在日記中寫道。很快,幾乎同樣的句子出現(xiàn)在他的《英雄樹木棉》一文中。每天不是爬格子就是匆匆往來于報館與寓所,葉氏的生活遠不如那些著名的博物學家輕松自在。
英國人約翰·亞歷克·貝克,是我們不太熟悉的一位作家,他一生只寫作了兩本書,其中一本名為《游隼》,幾年前介紹到中國,數次重印。據說作者一生都生活在英格蘭東部一個鄉(xiāng)下小鎮(zhèn),本書是他十年間追尋游隼的筆記,他的原則是:
我嘗試將一切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保存下來:鳥、觀測者,以及這片我們賴以生存的地方。我描述的每一件事都發(fā)生在觀測當下,但我并不認為忠實的觀察和記錄就足夠了。觀測者的情感與行為也同樣是重要的數據,我必如實記載。
作者的筆觸精致而寧靜、有詩意。
四野寂靜無聲,迷霧之中,萬物朦朧而神秘。一陣冷風吹過,云層堆疊了整片天空。麻雀躥過落葉的樹籬,沙沙窸窣,如小雨紛紛。歐烏鶇叫嚷起來。寒鴉和烏鴉站在樹枝上窺探下方。我知道,游隼就在這片田野中,但我就是找不到他。
他觀察游隼的追逐、捕殺、進食、休憩,沉迷期間,物我兩忘。研究者指出,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英國,農藥的大量使用使得游隼的數量急劇減少,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是游隼乃至人類自身的挽歌。
我注意到近年國內也有作者將注意力集中到類似的領域,盡管在當下大學的學科分類中,沒有博物學的位置,但“博物”一詞卻日漸傳播開來。我本人的專業(yè)離博物學很遠,關于這個話題,理應由更有資格的專家來討論,我只是從博物學的邊上,分享一些它給予我這樣的一個普通讀者的欣喜與愜意。
- 2024-04-09詩文評論集《仿佛若有光》出版
- 2024-04-02想要的,就大聲說出來
- 2024-04-01《高中階段學校學生軍事訓練》出版
- 2024-04-01《李鵬文集》(上下卷)正式出版發(fā)行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