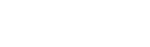“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唐代 孟郊 《游子吟》);“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漢樂府《孔雀東南飛》)……古代文學作品中有關“女紅”的描述可謂十分豐富,這一針一線無不體現著母親的慈愛與女性的賢惠。
數千年的農耕文明造就了“男耕女織”的社會形態,從養蠶栽棉到紡紗織布、從穿針引線到縫衣制服……“女紅”并非簡單的針線活兒,其從“衣披天下”而生,是生存基本之需,推動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女紅”不僅用以完成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同時也成為古代女性情感表達的方式。
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的這件國家一級文物——錦緣絹繡草編盒是1800年前河西走廊一位漢代女性的針黹盒。它的出土成為我們了解漢代女紅、紡織業最直觀的實證。
女紅是古代女子“四德”之一
女紅,也稱為女事,舊時指女子所做的針線、紡織、刺繡、縫紉等工作。在中國古代社會,傳統禮儀要求女性具有“德、言、容、工”四種德行,而女紅正是四德的表現之一。紡紗織布、縫補漿洗、針織刺繡成為女性成長中必學本領。幾千年來,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出土實物,女紅都淋漓盡致地向我們展示了女子的蕙質蘭心。
女紅需要一雙巧手。《紅樓夢》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補雀金裘”一節,強撐病體為寶玉通宵達旦修補雀金裘氅衣的晴雯算是巧中之最。“晴雯先將里子拆開,用茶杯口大的一個竹弓釘牢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得散松松的。然后用針紉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然后依本衣之紋來回織補……”“剛剛補完,晴雯又用小牙刷慢慢地剔出絨毛來。”
這件寶玉剛從賈母處得來的雀金裘,就被手爐炭火迸了一個指頂大的燒眼。這可不是一件平常的衣裳,據說是“拿孔雀金線織的”,以黃金制金線,捻入孔雀羽毛。且不論面料有多么珍稀,織補難度之高可以想見。晴雯憑一雙巧手,便讓這件珍稀的雀金裘完美如初。
又是竹弓,又是金刀,又是小牙刷,腦補一番,應該還有頂針、線板、針錐、尺子等諸多活計。這些針頭線腦,恐怕還需要一個存放它們的工具箱,那就是“針黹盒”。針黹盒除了存放針線工具以外,還可存放一些料頭、花邊、繩線之類,方便女子做針線時使用。
晴雯的針黹盒想必盒體精致,工具豐富。而這件國家一級文物錦緣絹繡草編盒的主人,她也會是如晴雯一般心靈手巧的女紅高手嗎?
武威出土國寶“漢代針線盒”
這件錦緣絹繡草編盒出自武威磨嘴子22號夫婦合葬墓,出土時位于棺蓋之上,內裝木線軸、繞板、銅針筒、針、玉飾品、刺繡品等10件。
這些實物不禁令人猜想,此盒應為墓主人生前心愛之物,哪怕死后也要隨葬身邊,并可預見這位漢代女子確是一位熱愛女紅的女性,沒準還是一位女紅高手。自古以來,女紅高手層出不窮。據說三國時期的吳王趙夫人有“三絕”——機絕、針絕、絲絕。可在指間以彩絲織成龍鳳之錦是為機絕;能用針線在方帛之上繡出五岳列國地圖是為針絕;又以膠續絲發作羅絲輕幔是為絲絕。錦緣絹繡草編盒的主人是否也有自己的絕活,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卻可從她的針黹盒及其內的工具和料頭一看端倪。
針黹盒,含底和蓋兩個部分。盒,長33厘米,寬18.5厘米,高17.5厘米,蓋高19.5厘米。蓋,長33.5厘米,寬19厘米,高18.5厘米。盒以葦編作胎,整體用絹和錦等絲織物裱包。葦編胎堅固密實,底與蓋套無縫隙。看這草胎,就知道它的主人葦草編織的手藝不凡,但若僅以草編盒示人,萬萬體現不出它的精致及主人的手藝。我們猜想絹錦裱包,除了讓這個針黹盒更加美觀以外,或許還有個非常實用的功能,那就是避免細針滑落。因為無論多么密實的草編盒,難免有縫隙。
沿、棱以棕色織錦縫成寬邊。錦紋顯白色帶鉤紋樣,此紋又稱“銅爐紋”,正向與倒向的銅爐紋交錯排列。
盒蓋以紅絹的刺繡為中心,四周鑲金邊。絹上以鎖繡而成云狀紋。刺繡的繡線為藍、白、綠三色,線性纖細,繡技精良,正所謂“錦上添花”。
漢代彌漫升仙長生的思想,體現在器物的裝飾上,經常有羽人、云起、珍禽異獸等祥瑞圖案。因此,漢代的絲織品上經常出現云氣、動物的紋樣。長沙馬王堆、新疆樓蘭等地出土的織錦上都有類似的紋樣。不難看出漢代中原的絲織品、審美也影響到了河西地區。
此盒出土時,內裝的木線軸呈簪狀,一端有六輪繞線螺圈,打磨得非常精致、光亮,可以看出是它的主人長期使用之物。另一纏線板用松木板制作,兩端弧圓而略寬,中部纏繞紅色絲線。絲線色彩艷麗、光澤如新,不免讓人產生錯覺,這是離我們那么遙遠的漢代的針黹嗎?
為河西段紡織技術提供了實證
除了木纏線板、木線軸,針黹盒內還有一些絳帶,類似于花邊、料頭編織的繩之類。它的紋樣及紡織技法,都為研究漢代絲綢之路河西段紡織技術提供了實證。
漢代絲綢之路開通,隨著貿易交流的逐漸展開,大量絲綢輸出,西方各國特別是羅馬上層社會對此趨之若鶩,使得世界上刮起了一股中國絲綢風。作為中國絲綢中最為華麗的兩種裝飾技法,織錦與刺繡是中國傳統織繡文化里的兩項瑰寶,而此針黹盒最重要的價值就在于它的裱包,集織錦與刺繡于一身,使我們對漢代織錦工藝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
這件針黹盒之所以引人注意,只因現代喜愛女紅者不在少數,很多年輕女性自幼頗愛女紅,雖非古代女子擁有一手絕活,卻也有一顆熱愛女紅的心。
現代慢生活美學興起,各種曾因工業時代消亡的女性藝術逐漸復興。現代女性雖不必拘泥于女德對自身的要求,卻可以通過各種現代化的手段將女紅作為休閑娛樂、緩解壓力、修身養性的方式。現代女紅不僅是一種個性的表達,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錦緣絹繡草編盒無疑是當代人與這位漢代女子關于女紅的一次穿越時空的神交。
- 2022-07-08蘭州鼓子《時代楷模治沙六老漢》入選文學獎提名
- 2022-07-08第五屆甘肅民間文藝百合花獎·學術著作獎擬獲獎名單揭曉
- 2022-07-08第二十八屆蘭洽會主賓國馬來西亞國家館開館
- 2022-07-08馬來西亞 熱帶雨林的問候——第二十八屆蘭洽會主賓國馬來西亞國家館巡禮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