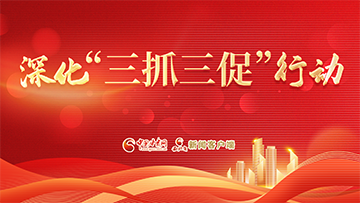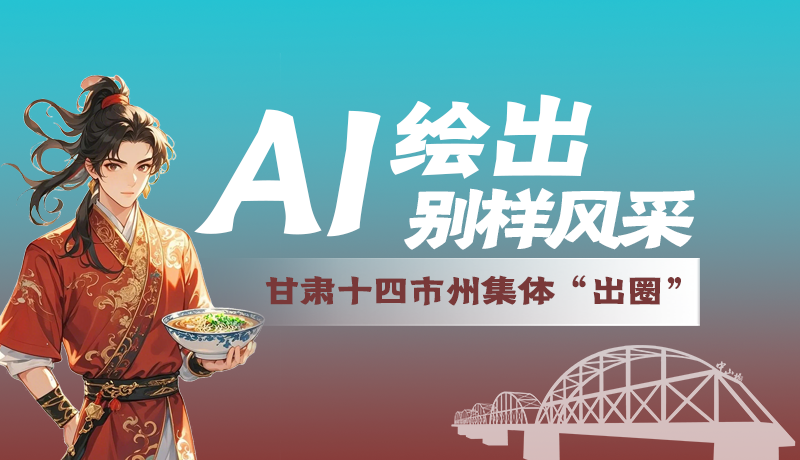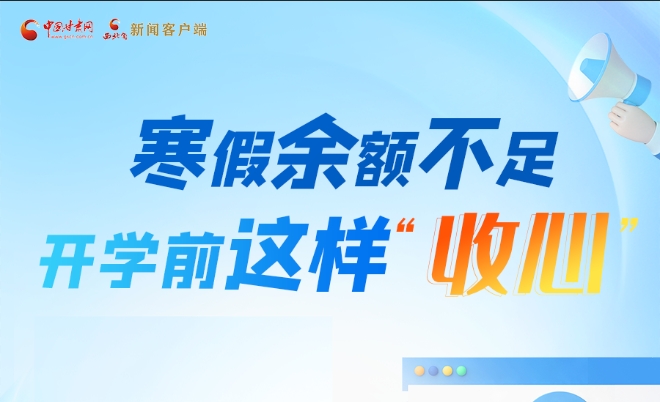原標(biāo)題:“如果再做一次選擇,我還是會來瑪曲草原”——追記“草原曼巴”王萬青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謝志娟 雷媛
引子:
人的一生,會面對無數(shù)次大大小小的選擇。但人生的關(guān)鍵選擇,屈指可數(shù)。
“草原曼巴”王萬青的一生有三次關(guān)鍵選擇:
第一次:從上海第一醫(yī)學(xué)院(今復(fù)旦大學(xué)上海醫(yī)學(xué)院)畢業(yè)后,去哪里?
第二次:那時正當(dāng)年,是回到上海工作還是繼續(xù)留在草原?
第三次:離世后,“回”上海還是長眠瑪曲?
面對三次重大選擇,王萬青給出了同一個答案:瑪曲草原。
三九寒天時,我們來到海拔3500米的瑪曲草原,沿著王萬青當(dāng)年的足跡,追尋他何以難舍這片草原的答案。
山川連綿,草原靜謐;成群的牛羊悠閑覓食,蜿蜒的河水緩緩流淌……
日月不語,日月不老;日月最是無情,也最是有情。晨起暮落、暮起晨落,陪伴王萬青在此度過56個春秋。
瑪曲,藏語意為“黃河”。曼巴,藏語意為“醫(yī)生”。瑪曲草原上的“王曼巴”2024年10月14日辭世離去。遵照他的生前遺愿,他的骨灰撒在了瑪曲草原上。
“如果再做一次選擇,我還是會來瑪曲草原。”這位生前被牧民群眾深深愛戴、離世后被牧民群眾深深惦念的“草原曼巴”不止一次這樣說。
草原是家啊!青春在這里,事業(yè)在這里;愛情在這里,兒孫在這里……縱使滬音未改、鄉(xiāng)情難卻,可是56年里,無數(shù)次縱馬馳騁救牧民于危急、無數(shù)次出入帳篷送醫(yī)問藥、無數(shù)次困苦艱難中救死扶傷……對這片土地的情感早已融入血脈,那些澄澈的眼神、那些比劃的手勢、那些塞進(jìn)懷里的糌粑牛肉,是一顆顆晶瑩心靈的無盡情誼,是草原賦予的珍貴饋贈。
草原是家啊!如果再做一次選擇,如果再做無數(shù)次選擇,那也只有一個答案:瑪曲草原!
“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艱苦的地方去。”
地處甘、青、川三省交界處的瑪曲縣,是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南部的一個純牧業(yè)縣,海拔3300米-4806米。
如今從蘭州出發(fā)前往瑪曲,需六七個小時,一路坦途。但即使如此,第一次前去的人仍有許多顧慮:會很冷嗎?會有高原反應(yīng)嗎?會有語言溝通不暢的問題嗎?
20世紀(jì)60年代,交通條件無法與今日相比,當(dāng)時從蘭州到甘南州州府所在地合作市需要兩天,從合作市到瑪曲縣還需兩天。
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在1968年12月,被就讀于上海第一醫(yī)學(xué)院醫(yī)學(xué)系的王萬青看到了,他鄭重地填下了畢業(yè)分配第一志愿——甘南藏族自治州。這個地名,是他從地圖上看到的。打開中國地圖,以指尖為指引,從東海之濱一路向西向北2000多公里,一路從2米多的海拔高度行至3000多米的海拔高度,甘南?甘南!一定夠遠(yuǎn)夠艱難吧。
“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艱苦的地方去。”這是王萬青當(dāng)時在畢業(yè)分配志愿表上寫下的一行字。
24歲的王萬青隨后被分配到甘南州工作,半年的集中培訓(xùn)后,他選擇了甘南州最偏遠(yuǎn)最艱苦的瑪曲縣,緊接著又選擇了距離縣城50多公里且不通公路的阿萬倉鄉(xiāng)。
鄉(xiāng)衛(wèi)生院的條件是有限的:一間診室,一間倉庫兼藥房,除了簡單的藥箱,幾乎沒有其他的醫(yī)療設(shè)備。生活環(huán)境也是在上海時無法想象的:透風(fēng)的土坯房、微弱的煤油燈光,沒有電沒有自來水,燒火做飯取暖要燒牛糞……
“在這里能干什么呢?”一腔熱血的王萬青,心里也曾有那么一瞬的涼。
“要經(jīng)得起考驗,挺過來就好。”遠(yuǎn)超想象的艱苦環(huán)境和落后條件,沒能阻擋年輕心靈立志扎根草原的勇氣。
立志容易,堅持不易。
最大的攔路虎是語言。阿萬倉鄉(xiāng)絕大部分是藏族群眾,想要在當(dāng)?shù)厣睿槟撩袢罕娍床。瑢W(xué)說藏語成為當(dāng)務(wù)之急。他抓緊一切時間學(xué)藏語,最先學(xué)的是看病常用語言,如:吃藥、一天幾次、一次幾片、哪里疼、哪里不舒服等。
有一天鄉(xiāng)衛(wèi)生院來了兩位牧民,一人騎著一匹馬,還牽著一匹馬,他們想要請“王曼馬”出診。而這是王萬青到阿萬倉鄉(xiāng)衛(wèi)生院10天后的第一次出診。
在去牧民家的途中馬匹受驚,王萬青被掀下馬背,整個人被摔得躺在地上半天動彈不得,眼鏡也摔飛了。見此情形,兩位牧民也嚇壞了,以為他給摔死了。在草原,發(fā)生過墜馬死亡的意外。
過了好一會兒,王萬青才醒過來,經(jīng)他自己診斷,是右肘關(guān)節(jié)脫臼。盡管胳膊劇痛,但他不同意牧民送他回去的提議,他覺得半途回去一定會成為草原上的笑話,那太丟臉,再說病人還盼著大夫。忍著痛,他指導(dǎo)牧民幫自己接回脫臼的手臂,找了根繩子固定住傷臂后,上馬繼續(xù)前行。
牧民家的帳篷里,病了數(shù)天的兩位病人正眼巴巴地等著醫(yī)生的到來。一位老漢是燒傷,一位婦女是急性扁桃體發(fā)炎正在高燒。等診治完兩位病人,天也黑了,當(dāng)晚王萬青就住在牧民家的帳篷里。
實際上,摔傷比王萬青預(yù)想的要嚴(yán)重,在被瑪曲縣醫(yī)院確診為骨折后,他請假去了上海進(jìn)行醫(yī)治。可即使如此,仍是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jī),那條手臂從此留下后遺癥——手彎到一定程度或者是位置沒擺好就轉(zhuǎn)不過來。
兩個月后,當(dāng)王萬青從上海返回瑪曲草原時,人們有點驚奇,“‘大個子’回來了,算定他一定一去不回的呀!”身高超過1米8的王萬青,有時被牧民群眾稱為“大個子”。是的,他又回到草原了,特意帶著從上海一所中醫(yī)門診收集的中醫(yī)傷科方子和一臺半導(dǎo)體收音機(jī)。
“我有心志是在草原干事業(yè),不可自食其言。”王萬青自己創(chuàng)作的素描連環(huán)畫——《我在黃河第一彎》中的這句話,回答了他為什么再度選擇回到瑪曲草原。
王萬青在150幅素描作品《我在黃河第一彎》中描繪了自己在阿萬倉鄉(xiāng)20余年的草原人生:
——風(fēng)雨無阻,騎馬走遍全鄉(xiāng),完成了阿萬倉鄉(xiāng)全鄉(xiāng)人畜共患的布氏桿菌病普查;
——給牧民孩子逐個實施計劃免疫,背著X光機(jī)、心電圖機(jī),去牧民家里逐一進(jìn)行健康體檢,帶著顯微鏡做糞便寄生蟲檢查;
——為3000余人建立了門診病歷,使阿萬倉鄉(xiāng)全鄉(xiāng)90%藏族群眾有了健康檔案;
——20世紀(jì)80年代,主刀成功搶救了一名腹部外傷、腸壞死、休克的10歲藏族兒童,這至今在瑪曲鄉(xiāng)下仍屬唯一;
……
1969年至1990年,王萬青在阿萬倉鄉(xiāng)衛(wèi)生院工作期間,每年接診病人3500余人次,20多年累計接診7萬余人次。1990年,王萬青從阿萬倉鄉(xiāng)衛(wèi)生院調(diào)入瑪曲縣醫(yī)院工作,2003年退休。
事實上,他在瑪曲工作的幾十年間,不止一次有離開草原回到上海的機(jī)會。
王萬青與好友彭裕文當(dāng)年先后分配至甘肅工作,彭裕文曾在一篇回憶王萬青的文章中這樣記述:
“1978年,我報名了第一批研究生錄取考試,王萬青也報名了。他做了很多準(zhǔn)備,看了好多書,他準(zhǔn)備考上海第一醫(yī)學(xué)院,他想要回來繼續(xù)讀書,因為他愛上醫(yī),上海還有他的親人!但他發(fā)現(xiàn)他的藏族姑娘、他的夫人在悄悄地哭泣。他又想到:我的愛人在這里,我的孩子在這里。我愛他們,我也愛甘南草原。牧民群眾需要我!于是,他想通了,決定不考研究生了,他永遠(yuǎn)留在了甘南的草原上。”
當(dāng)年,與王萬青同時來到甘南大草原的大學(xué)生還有許多,隨著時間的流逝,有的通過考大學(xué)、讀研究生離開了,有的想方設(shè)法調(diào)走了,有的索性早早病退回去了,但當(dāng)初被人們認(rèn)為是“飛鴿牌”的王萬青卻永遠(yuǎn)地留了下來,更把自己的一身本領(lǐng)都奉獻(xiàn)給了瑪曲的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
“‘王曼巴’是阿萬倉的好女婿。”
在瑪曲草原上至今流傳著“草原曼巴”救人的故事……
1984年9月的一天,一名10歲藏族孩童在放牧?xí)r,被牛角挑穿了肚子。第二天傍晚,孩子被送到阿萬倉鄉(xiāng)衛(wèi)生院時,病情危重,需要手術(shù),鄉(xiāng)衛(wèi)生院沒有手術(shù)條件,但轉(zhuǎn)院要翻海拔4000米的大山,還要過七道沒橋的河。走100多里路,又沒有汽車……毫無疑問,孩子還沒送到縣醫(yī)院,就會死在路上。
“不能見死不救,只要有一絲希望就不能放棄。征得家長和鄉(xiāng)領(lǐng)導(dǎo)同意后,我立即動員全院作術(shù)前準(zhǔn)備,當(dāng)時全院連我和妻子總共4個人。兩張辦公桌是手術(shù)臺,一個電燈泡加兩個手電筒是無影燈,又啟動了剛配備上的小發(fā)電機(jī)。我是主刀,又兼麻醉。大家一夜忙碌,成功切除壞死腸管84厘米,救活了小南美。”在《我在黃河第一彎》中,王萬青以5幅畫記錄下了《搶救小南美》的驚心動魄。那個被救的孩童叫南美,后來長大的南美還時常帶著妻兒來看望救命恩人“王曼巴”。
小南美得救了,草原也震動了。瑪曲草原上,此前沒有人敢做這樣復(fù)雜的外科手術(shù)。
“看病就找‘王曼巴’。”奔馬馳騁的口口相傳間、救死扶傷的治療過程中,這種信任越來越廣泛,王萬青成了牧民最信賴的“草原曼巴”。
“在阿萬倉,很多人都認(rèn)識‘王曼巴’。”2025年1月14日下午,在阿萬倉鎮(zhèn)道爾加村,67歲的才得合回憶起與王萬青的交往,話匣子打開了:才得合10多歲時,一起放牧的伙伴有一次突然肚子疼,他帶著伙伴趕緊去找王萬青,“看病我們都找‘王曼巴’”。王萬青曾經(jīng)在各隊找人學(xué)醫(yī),才得合的妹妹就是其中之一,王萬青教會她打針。現(xiàn)在,才得合的一個孩子也學(xué)了醫(yī)。一直以來,在才得合心中,曼巴(醫(yī)生)治病救人,是個好職業(yè)。
“‘王曼巴’是我們阿萬倉的女婿。”才得合和王萬青的妻子凱嫪同為道爾加村人,才得合說在村民心中“王曼巴”是阿萬倉的好女婿。
回憶起王萬青,貢賽村的旦考也豎起大拇指連連說“好”,“他人好、人品很好、醫(yī)術(shù)好!”在旦考的記憶里,“王曼巴”是沒有下班時間的,牧民隨時去找他看病或請他出診。即使正在吃飯,他也立刻放下飯碗;即使天在下雨,他也立刻披上雨衣騎馬趕去牧民家里;即使是在晚上,他也毫不猶豫馬上出發(fā),看完病天太晚了,就在牧民家的帳篷里住下……60歲的旦考清楚記得一幕幕,他指著自己的右臂,“‘王曼巴’騎馬到我家?guī)づ窭锝o我種過痘。”
旦考的家人也都找王萬青看過病。“我弟弟的孩子生病了,錢不夠,‘王曼巴’自掏腰包幫他。”而這樣的事,旦考還聽到過多次。
50多年前,瑪曲草原上,牧民逐草而居,居住分散,看病比較困難。一次,旦考的父親生病了,因為看病不方便就一直拖著,可十多天了也不見好,就去鄉(xiāng)衛(wèi)生院把“王曼巴”接到家里。“當(dāng)時,家里離鄉(xiāng)衛(wèi)生院有四五十公里,‘王曼巴’騎馬趕來,一下馬就看病,之后給我父親打了針,一兩天后我父親就站起來了。很神奇!他醫(yī)術(shù)高明。”
道爾加村三隊的道日巴今年75歲了,他記得自己第一次在醫(yī)院見到王萬青,是因為妻子生病了,“她的病被‘王曼巴’看好了。”道日巴說,他還記得“王曼巴”剛到阿萬倉不久,就在各個生產(chǎn)隊里找助手,然后教他們學(xué)醫(yī)。“后來,那些人都成了草原上很好的‘曼巴’,為群眾服務(wù)。他是很好的共產(chǎn)黨員,人品好。”道日巴聽到王萬青去世的消息后,心里很難過。
“他的醫(yī)術(shù)當(dāng)時在甘南州數(shù)一數(shù)二!”
建于1956年的瑪曲縣人民醫(yī)院,是全縣唯一一所集預(yù)防、醫(yī)療、保健、急救、康復(fù)為一體的綜合性醫(yī)院。
1990年,46歲的王萬青從阿萬倉鄉(xiāng)衛(wèi)生院調(diào)入這里工作,直至2003年退休。
現(xiàn)任瑪曲縣人民醫(yī)院黨支部書記白壽山直言,王萬青在縣衛(wèi)生院工作10多年,是醫(yī)院發(fā)展的一位引領(lǐng)人和開拓者,“他視病人如親人,把醫(yī)院當(dāng)成家,業(yè)務(wù)上追求精益求精;技術(shù)上,從不藏著掖著,把自己的醫(yī)學(xué)技術(shù)傳授給后輩。這種無私的精神,體現(xiàn)出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精神,更為醫(yī)院人才隊伍的建設(shè)打了一個很好的基礎(chǔ)。”白壽山曾多次去過王萬青的家,每次去,已退休在家的王萬青關(guān)心的仍是醫(yī)院的未來發(fā)展、人才培養(yǎng)。
50歲的祁武志現(xiàn)任瑪曲縣人民醫(yī)院副院長。1995年,當(dāng)他從甘肅省衛(wèi)生學(xué)校口腔醫(yī)學(xué)專業(yè)畢業(yè)后進(jìn)入縣醫(yī)院時,王萬青是醫(yī)院最大科室——外科的主任。祁武志和王萬青合作過上百臺手術(shù),當(dāng)時縣醫(yī)院專業(yè)的外科大夫不多,只要王萬青上手術(shù),他就會喊著祁武志他們這些其他科室的醫(yī)生,一起上手術(shù),請他們當(dāng)助理或是做幫手,目的是讓年輕大夫多學(xué)點。祁武志記得清楚,第一次和王萬青上手術(shù),是幫著“拉鉤”。和王萬青共事的七八年間,祁武志印象最深的一點就是王萬青一直要求醫(yī)生,特別是像他們這些基層醫(yī)生“多學(xué)習(xí),要有全科素質(zhì)。他不止一次對我說多學(xué)點,多進(jìn)修。”正是這樣點點滴滴的言傳身教,口腔科的祁武志漸漸成長為全院業(yè)務(wù)骨干。
祁武志說王萬青自己就一直堅持學(xué)習(xí),還讓在上海工作的同學(xué)不間斷地給他寄醫(yī)學(xué)書籍,“堅持學(xué)習(xí)不但使他在醫(yī)學(xué)的發(fā)展中沒有落伍,而且每年都有論文發(fā)表,更可貴的是他還攻克了不少疑難雜癥。”
祁武志記得,大概是1998年左右,縣醫(yī)院遇到了一個因意外墜樓導(dǎo)致腦外傷出血的病例,當(dāng)時醫(yī)院還沒有CT,診斷困難,而且之前醫(yī)院也沒有做過這種手術(shù)。手術(shù)最后是王萬青做的他根據(jù)多年的臨床經(jīng)驗做出診斷并實施了手術(shù),病人最后痊愈。
和祁武志有相同感受的,還有醫(yī)務(wù)科科長姚春林,“和王主任共事的四五年,是自己職業(yè)生涯的一個重要時段。”1993年從甘南衛(wèi)校畢業(yè)后,姚春林先是在曼日瑪鄉(xiāng)衛(wèi)生院工作,6年后調(diào)入瑪曲縣人民醫(yī)院。和祁武志他們一樣,一旦王萬青上手術(shù),姚春林也會被叫去當(dāng)助手。姚春林在曼日瑪鄉(xiāng)衛(wèi)生院時學(xué)過麻醉,他在縣醫(yī)院第一次上王萬青的手術(shù),承擔(dān)的就是麻醉師之責(zé)。“第一次和從小就知道大名的人合作手術(shù),除了緊張,還是緊張,擔(dān)心麻醉打不上。”30多年后回憶往事,姚春林依然記得自己當(dāng)時的緊張。
下了手術(shù)臺,王萬青很認(rèn)真地對姚春林說:“其實我在手術(shù)臺上就看出了你很緊張,不過今天你做得非常好。大家是相互配合一起工作,不要緊張。”“自那以后,我們順利合作了上百臺手術(shù)。他的醫(yī)術(shù)當(dāng)時在甘南州都是數(shù)一數(shù)二!”
剛進(jìn)縣醫(yī)院時,姚春林還有些怕上王萬青的手術(shù)。“如果第二天有手術(shù),前一天他就要求大家熟悉手術(shù)過程,比如解剖層次等,到第二天的手術(shù)臺上,他會現(xiàn)場提問。如果答不上來,他會批評。等到下了手術(shù)臺,他會給參與手術(shù)的年輕醫(yī)生們一一講解每個步驟。”姚春林說這種教授方式學(xué)起技術(shù)來特別快,自己在這種手把手的教學(xué)中受益匪淺。“王主任剛退休的幾年,我們遇到疑難雜癥就跑去找他。他家住得近,手術(shù)遇到難關(guān),就趕緊叫王主任來,難度大的,他就親自上手術(shù)臺,要么就在一旁指導(dǎo),告訴我們遇到這種情況應(yīng)該如何處理,等等”。
無論是在學(xué)校還是在醫(yī)院,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在草原;無論環(huán)境如何改變,無論年齡如何增長,一生都在學(xué)習(xí)的王萬青,是一位名副其實掌握大內(nèi)科和大外科知識技能的“全科醫(yī)生”,在臨床上是位多面手,在醫(yī)療設(shè)備嚴(yán)重不足的條件下,他以精湛的醫(yī)術(shù)和高度的責(zé)任心,成功救治過眾多生命垂危的患者。
作為瑪曲草原上的一名基層醫(yī)生,王萬青還在某些醫(yī)學(xué)課題方面有所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新。他自費購買了一套俄文原版的《醫(yī)學(xué)百科全書》,工作之余,刻苦攻讀,并翻譯醫(yī)學(xué)資料10萬余字,他還在國家級和地方各級醫(yī)學(xué)雜志上發(fā)表《阿萬倉鄉(xiāng)牧民發(fā)病情況分析》《瑪曲高原新生兒肺炎氧氣治療的重要性》《瑪曲縣醫(yī)院十年外科住院病歷分析》等20余篇科研論文,部分論文獲獎后引起業(yè)界廣泛關(guān)注。
“父親生前有兩大愿望……”
20世紀(jì)70年代的B超機(jī),老式的心電圖機(jī)、呼吸機(jī)、麻醉機(jī)……在今日的阿萬倉中心衛(wèi)生院,有個小小的陳列室,擺放著的一件件陳舊的醫(yī)療儀器,都是王萬青曾經(jīng)用過的。
在阿萬倉中心衛(wèi)生院、瑪曲縣人民醫(yī)院,新入職醫(yī)護(hù)人員的第一課,就是學(xué)習(xí)王萬青醫(yī)生的事跡,學(xué)習(xí)他愛崗敬業(yè)、執(zhí)著追求的精神。
王萬青走了,但他的故事和精神風(fēng)范卻留在了瑪曲大草原,激勵著一代代后來者。
40多年前,王萬青在阿萬倉為幾千名牧民建立了病例檔案。現(xiàn)在,阿萬倉中心衛(wèi)生院院長其軍才讓帶領(lǐng)醫(yī)護(hù)人員建立的病例檔案,涵蓋了阿萬倉鎮(zhèn)所轄的5個行政村。
1977年出生的其軍才讓,也是一位在醫(yī)療衛(wèi)生戰(zhàn)線上工作了20多年的基層醫(yī)務(wù)工作者,他曾在瑪曲縣的木西合鄉(xiāng)工作多年。其軍才讓1999年參加工作時,從鄉(xiāng)里到縣城坐汽車還要用上9個小時;2010年,鄉(xiāng)里才有光伏發(fā)電,“可以想象王萬青他們那個時候的環(huán)境條件有多艱苦。”甘南草原上長大的孩子,都知道王萬青的名字,在其軍才讓心中,王萬青是一盞明燈,“一個上海人在這里一輩子,真是了不起!”
當(dāng)被問到在基層這么多年的感觸時,其軍才讓說:“這里需要我們,我也愿意留在這里,為基層群眾服務(wù),很值!”
最好的傳承是踐行。
53歲的王團(tuán)勝追隨父親王萬青的腳步,放棄了留在大城市的機(jī)會,毅然回到瑪曲大草原,成為一名基層醫(yī)務(wù)工作者,一干就是30多年。王團(tuán)勝的小兒子現(xiàn)在是一名天津醫(yī)科大學(xué)的在讀定向生,畢業(yè)后同樣要回瑪曲草原工作。“我父親生前因為孫子是定向生而特別欣慰。他說這下好了,我的那么多書,可有去處了。”
選擇學(xué)醫(yī),王團(tuán)勝直言是受父親的影響。作為家里四兄妹中的長子,王團(tuán)勝從小就是父親的小幫手,跟著父親騎馬去草原深處為牧民打預(yù)防針,父親一邊打一邊給他教。王團(tuán)勝上甘肅省衛(wèi)生學(xué)校期間的一個暑假,人剛一到家,就被父親叫去衛(wèi)生院為鄉(xiāng)里正在開展的結(jié)核病檢查幫忙。畢業(yè)后進(jìn)入縣醫(yī)院放射科工作,只要父親有手術(shù),王團(tuán)勝和其他科室的年輕大夫一樣,也被叫去當(dāng)助手。
“我還因為外科病例寫得不好,挨過他的打。他嫌我寫得邏輯有問題、表述用詞不合適、標(biāo)點符號有錯誤。”當(dāng)王團(tuán)勝娓娓講述這些往事時,那位嚴(yán)父似乎就在他的面前一一指出問題,日常點滴,皆似山似海。
王團(tuán)勝評價父親寫的病例:“感覺很舒服,特別是病程記錄,詳實完整,實事求是,沒有先入為主。”在父親的嚴(yán)格教導(dǎo)下,王團(tuán)勝寫的病例,還有他同為醫(yī)生的妻子寫的病例,進(jìn)步巨大。
熟悉王萬青的醫(yī)生都知道,他生前在工作中很注重醫(yī)學(xué)基本功訓(xùn)練和實踐,王團(tuán)勝也深受影響。“他很反感僅僅靠數(shù)據(jù)靠設(shè)備看病,他一直認(rèn)為醫(yī)生一定要用基本方法為病人作檢查,并與病人多交流溝通。” 王萬青說父親求學(xué)時,父親的大學(xué)老師特別強(qiáng)調(diào):基本知識、基本理論、基本技術(shù),“這讓父親受益一生。”
作為一位父親,王萬青在兒子王團(tuán)勝心中的形象則要生動有趣得多。王萬青有雙翻毛皮鞋,穿了很多年,鞋子又掉皮又脫色,很不好看。有一天,王團(tuán)勝兄妹發(fā)現(xiàn)父親的翻毛皮鞋突然變樣了,原來是王萬青把那些掉皮脫色的地方用黑墨水給涂了,他本人覺得那樣會好看些,但王團(tuán)勝兄妹覺得“鞋子更難看了”。
生活中的王萬青,多才多藝,會畫畫、會吹笛子、會吹簫,還會唱不少俄語歌曲。重要場合會穿上自己心愛的風(fēng)衣,說藏語時總是夾雜著上海口音……上海生長的王萬青,并沒有抹去故鄉(xiāng)的全部印跡,只是半個多世紀(jì)的草原生活,早已讓他與這片草原緊緊相連,從骨子里成了一名草原漢子——草原就是他的家,草原人民就是他的親人,珍愛民族團(tuán)結(jié),守護(hù)牧民健康,這是他用一生的時光,書寫下的一份和草原的情感堅守。
王團(tuán)勝的腦海里,總有一些畫面會浮現(xiàn):父親一人在屋里或是在草坡上,吹著笛子或是輕聲歌唱,笛聲悠揚、歌聲婉轉(zhuǎn)……
“父親生前有兩大愿望:草原同胞的衛(wèi)生健康工作任重而道遠(yuǎn),希望后輩能有人代代學(xué)醫(yī)薪火相傳,心系杏林,懸壺濟(jì)世,是其一;希望子孫后代能在維護(hù)民族團(tuán)結(jié)進(jìn)步方面繼承發(fā)展,為其二。”王團(tuán)勝說他們將傳承父親遺志,“這是父親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
時常有人問王團(tuán)勝,他的名字是不是就是團(tuán)結(jié)勝利的意思。王團(tuán)勝說名字是父親取的,在瑪曲草原,父親遇到了愛情,和他心愛的藏族姑娘相伴了半個世紀(jì)。和父親一樣,王團(tuán)勝也在草原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侶,一位藏族醫(yī)生。
王萬青在《我在黃河第一彎》中特別記錄了一個讓他“差點哭出來”的小故事。故事發(fā)生在1970年的早春,彼時草原仍是寒冬時節(jié),王萬青隨工作組下生產(chǎn)隊工作,不料得了重感冒。“渾身難受,幾天一口飯沒吃,心情也很不好,孤獨一人昏睡在冰冷的牛毛帳篷里。一位藏族大媽踏著冰雪,一步一滑地送來一碗熱粥。我看看碗,看看大媽,差點哭出來,那年頭物資緊缺,大米是很金貴的。此事我終生難忘。”
王萬青與瑪曲草原彼此相伴的56年里,來自身邊的無數(shù)溫暖,正如那碗熱粥,溫暖著他的心,讓這片廣袤的草原成為他永遠(yuǎn)的家。
- 2025-02-21【甘快看】甘肅山丹的“異鄉(xiāng)人”路易·艾黎從未遠(yuǎn)去
- 2025-02-21【甘快看】秦嶺深山中的“青春答卷”
- 2025-02-20蘭州海關(guān):“萌寵出境”省心辦 旅客出行更便捷
- 2025-02-20甘肅文縣“白馬巧匠”的面具情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xué)習(xí)強(qiáng)國
學(xué)習(xí)強(qiáng)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